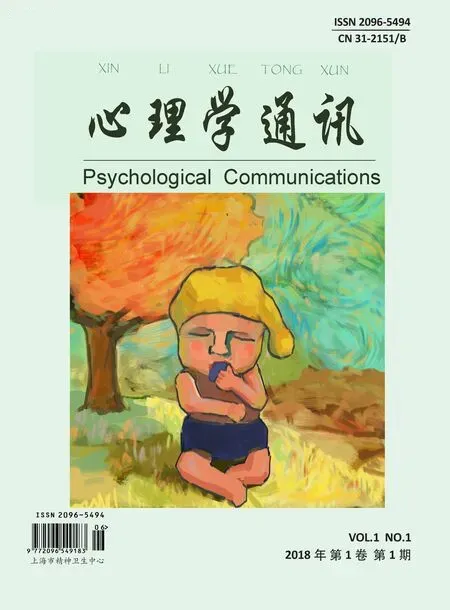幼儿情绪能力训练的理论构思与实证检验
严严,黄玲,华弥之,陈思佚,杨萌,周仁来*
1南京大学心理系,南京 210023
2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100875
1 引言
自1884年William James“情绪是什么”之问以来,情绪一直是心理学永恒的研究主题。目前学界并未对情绪的定义达成一致,但普遍认同情绪具有一套有限的组成成分和特性(Izard,2009)。关于情绪的组成,Izard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情绪是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三种成分的有机组合过程。他认为情绪可分为两种:在人类心理与适应行为中起到根本性作用的基础情绪,以及较为复杂的动态的情绪-认知互动过程,或称情绪图式(emotional schemas)(Izard,2009),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也是采用最多的四种基本情绪是愉快、悲伤、恐惧和愤怒。
1.1 情绪能力概述
情绪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由Saarni在1990年出版的《社会情绪发展》一书中借用Gordon(1989)的表述而提出。情绪能力概念基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强调幼儿通过社会互动能动地习得本文化的情绪行为、规范和符号。Saarni(1990)认为情绪能力是韧性和自我效能感在诱发情绪的社会情境中的体现,即如何自发地做出情绪化的反应、如何有策略地将情绪知识应用于人际交往和自身的情绪调节。Saarni(1999)将情绪能力划分为八种亚能力,包括觉察自身情绪、识别与理解他人情绪、使用情绪语言与表达、共情能力、区分内外部情绪体验、应对不良情绪和情境、情绪沟通意识以及情绪的自我效能感。Denham等(2002)进一步将情绪能力归纳为情绪表达、情绪知识和情绪调节三个主要方面。在逐渐意识到社会化与情绪能力互相交织以后(Denham et al.,2001;Denham et al.,2003;Rose-Krasnor,1997),社会情绪能力(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ies)的概念逐渐发展起来,Denham (2006)在原先三种情绪能力的基础上加入了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社会人际关系技巧,组成了社会情绪能力的主要方面。由此可见,人际交往对幼儿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三到六岁的学前期是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Brown &Dunn,1996;Harris et al.,1989;Lewis,2013;姚端维,陈英和,赵延芹,2004)。
1.2 情绪能力的作用
情绪能力对幼儿的终身发展有关键作用。它不仅与总体心理健康有关(Ciarrochi &Scott,2006;Ciarrochi et al.,2003),而且其各项指标能够预测认知、行为和成就等多方面表现(Blair,2002;Blair &Raver,2015;Denham,2006;Denham &Brown,2010;Voltmer &von Salisch,2017)。此外,情绪能力与注意水平(Trentacosta et al.,2006)、抑制控制和问题求解等认知功能相关(Blair,2002)。同时,情绪能力与学前期幼儿的社会行为发展和亲社会行为也存在紧密联系(Bailey et al.,2016;邓赐平,桑标,缪小春,2002;Denham,1986;Diaz et al.,2017;Garner &Estep,2001;Herndon et al.,2013;Hernandez et al.,2016;Ladd,1999;Lindsey,2017;Miller et al.,2006;Nakamichi,2017;Ornaghi et al.,2015)。
1.3 情绪能力的影响因素
情绪能力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除先天因素之外,也极大地受到环境因素的作用;这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融合。例如年龄(Brophy-Herb et al.,2011;Denham et al.,1997)、性别(Denham,Bassett,&Wyatt,2010;Root &Rubin,2010)和种族(Garner &Mahatmya,2015)这些生理和心理差异对情绪能力的影响也受到环境因素的调节。
环境因素又可以分为人际环境和社会环境(Pollak,2008)。对幼儿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场所是家庭和学校,相应地,父母(Denham et al.,1997;Telzer et al.,2014)、教师(Garner &Mahatmya,2015;Finlon et al.,2015;Lam &Wong,2017;Root &Rubin,2010;Stratton,1984;Zinsser et al.,2015;张婕,2009)和同伴间互动(Ladd,1999;万晶晶,周宗奎,2002)也是最关键的人际环境,幼儿在这种社会互动中习得和培养情绪能力(Dishion &Tipsord,2011)。有证据表明,社会环境在相当程度上也通过人际环境发挥作用,例如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可能通过父母的心理状况和教养方式(Brophy-Herb et al.,2011)、危险行为暴露量(Domitrovich,Cortes,&Greenberg,2007)起作用。由此可见,情绪能力和人际关系深刻地互相影响,培养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构建良好的家长-教师-同伴三元人际关系,对于幼儿综合的社会情绪能力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4 情绪能力的训练
鉴于情绪能力的重要作用以及学前期阶段的关键性,通过在学校引入情绪能力训练课程来促进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者的共识(Domitrovich et al.,2007;Durlak et al.,2011;张 婕,2009)。国外很早就关注幼儿情绪能力的培养,设计和实施了相应的课程。1994年成立于美国的非盈利组织“社交与情绪学习协作中心”(CASEL)是循证的(evidence-based)社交与情绪学习(Social-Emotional Learning,SEL)的发起和推广者。一项基于213个SEL项目的大型元分析研究表明,SEL项目参与者的社会情绪技能、行为态度都有了显著提升,尤其是学业表现平均增长了11%(Durlak et al.,2011)。截至2017年底,基于SEL的课程已经在全美五十个州的幼儿园普及,至少十六个州公布了相关指南(Dusenbury,Dermody,&Weissberg,2018)。英国也认识到培养情绪能力的重要性,将学校在增进情绪健康和幸福感中的作用提上了国家议程前沿(Ohl,Fox,&Mitchell,2013)。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都在探索和落实幼儿情绪教育,目前也有许多较为成熟的训练方案。对以往的研究稍加总结,我们可以将训练方案按照对象和目标的不同分为三类:(1)面向整个学校的一般性方案;(2)针对品行不良或有相应发展倾向儿童的矫正或预防方案;(3)针对有心理疾病的儿童的特殊干预训练。表1对三类训练方案做了更具体的说明。需要指出,三类课程的对象并无严格区分。
我国的情绪能力训练课程起步较晚。国内曾在2006年引入英国的系统化幼儿情绪健康教育课程“比比和朋友”(Zippy’s Friends)在上海进行试点教学,后来又推广到北京,研究结果证明课程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然而,这类引进课程的内容中不免带有许多文化差异性的情境和价值观念,例如兄弟姐妹间的妒忌、对禁止宠物带到学校的愤怒等,使得幼儿难以理解,因此也折损了课程效果(张婕,2009)。根据Hofstede(2011)的研究与回顾,中西方文化在情绪易感性、群体关系、集体或个人主义倾向等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人的情绪表达较为温和,有较高的自我监控能力;重视家庭,崇尚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开发一套适用于中国文化情境、强调人际关系处理的情绪训练课程,将有助于幼儿更好地在生活情境中运用情绪能力进行社会互动,从而健康地发展和成长。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北京某公立幼儿园两个中班的幼儿共58名。将被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并对性别进行了平衡。实验组依照《情绪能力培养与训练方案》进行干预,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各有一名幼儿因故退出,最终得到有效被试为56名。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幼儿各28名,实验组男孩20名、女孩8名;对照组男孩19名、女孩9名。

表1 三类情绪能力训练一览
2.2 测试工具与编码
根据华弥之等(2012)提出的由近两个月内与儿童有频繁日常接触的成人来评分的建议,本研究结合了教师评定法和家长评定法;两组幼儿的情绪能力均由自己家长和班级的三位教师(主班教师、助理教师和配班教师)进行评定,取三位教师打分的平均值作为教师评分。在课程进行之前,即中班上学期开学时进行了一次前测,第一学期结束时进行中期测查,第二学期期末进行后测。考虑到课程内容为模块化教学,中期测查的成绩不能很好地反映总体水平的提升,因此在数据分析时仅包括了前后测成绩。
2.2.1 学前情绪与行为评定量表(Preschool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Rating Scale,PreBERS)
PreBERS量表是专门用于评估学前期幼儿的情绪和行为优势的标准化常模参照量表,包括情绪调节、入学准备、社交自信和家庭融入4个分量表(Cress et al.,2012)。该量表的中文版被证明有较好的信效度,适用于中国儿童(华弥之,周仁来,2012)。中文版PreBERS量表由34个正面陈述的项目组成,其中情绪调节和入学准备分量表各包括11项,社交自信和家庭融入各包括6项。量表采用0~3分的Likert 4级计分(0代表完全不符合,1代表比较不符合,2代表比较符合,3代表非常符合),总分在0~102分之间。
2.2.2 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
SDQ量表用于评估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适应,它综合考虑了情绪行为功能和个人优势,应用面较广泛(Van,Veenstra,&Clench-Aas,2008)。该量表的中文版被证明有较好的信效度,适用于中国儿童(刘书君,2006)。中文版SDQ量表由25个项目组成,分为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多动问题、同伴问题和亲社会行为5个因子,每个因子包含5项。量表采用0~2分的Likert 3级计分(0代表不符合,1代表有点符合,2代表完全符合);其中前面四个因子为负面陈述,构成问题总分,在0~40分之间;亲社会行为为正面陈述,单独计分,在0~10分之间。
2.3 干预方案
2.3.1 方案设计
在上述理论构建的基础上,我们将抽象的理论发展成了实用的教学技术,研发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幼儿的情绪能力训练方案,包括课程教具、教材、幼儿培训课程和专业教师培训课程四个部分,涵盖了班级活动和日常行为。结构化课程一共30课时,每节课课时长度在25~30分钟,使用统一的教学大纲。训练方案由基本情绪和人际关系两部分组成,每部分有7个单元;课程主要关注快乐、悲伤、恐惧和愤怒四种基本情绪,以及合作、竞争和友爱关系三种人际互动。
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可以从情绪能力的三个方面以及人际关系来描述。(1)情绪知识:认识四种基本情绪,主要是识别面部表情和用语言描述;理解不同情绪产生的原因和情境。(2)情绪表达:知道情绪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但用语言表达是最好的方法。(3)情绪调节:掌握不同的情绪调节方法。(4)人际关系:体验并识别合作、竞争、友爱关系;知道建立这三种关系的方法。课程在整体主题的框架下层层推进,以3~5岁幼儿的认知和情绪能力的发展特点为依据,在不同的年龄设置了体验识别、表达评价、调节/建立与维持等不同的阶段目标,从引入概念到应用技巧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帮助幼儿逐步打好社会情绪能力的基础。以四岁阶段为例,具体的课程设置如表2所示。
为了更好地将方案应用于本土化教学,我们与不同城市的多位幼儿园教师讨论了容易引起幼儿情绪反应的认知情境,以及适合幼儿的教学活动组织形式。在经过多次实践和修改后,最终制定了包括游戏、绘画描述、语言描述、情境表演等形式在内的教学活动方案。此外,我们设计了一系列辅助教具,例如课程配套的卡通图片、印有面部表情图和情绪调节步骤等内容的卡通漫画集等等;每个单元最后的“拓展活动”可以作为本单元课程内容的补充,提供多样化的游戏方案。
基于对家长-教师-同伴的三元人际关系的强调,我们设计了与幼儿园教学活动相对应的家长联系卡,并在课程开始前对家长进行了培训,介绍了联系卡使用方法、与孩子的沟通技巧及情绪训练方案的大致情况。通过完成家长联系卡,家长可以了解孩子上课所学内容、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并进一步帮助孩子复习和巩固所学内容。
2.3.2 方案实施
每周五上午 8:30—9:00 之间为课程的教学时间。每周五下午幼儿离园时,将《家长联系卡》交给家长,以便他们利用周末时间与幼儿做课程的同步练习,并在周一将练习的结果返回给班级老师。分两个学期完成所有的教学活动。
2.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将家长和教师部分的前后测数据分别汇总,进行方差齐性Levene检验,Bonferroni校正,独立样本t检验,重复方差分析,功效估计通过偏eta方(ηp²)估计。
3 结果
两组的性别比例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对前测分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家长与教师共22项评分中仅3项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占全体评分的14%,因此认为该实验中性别基本不起作用,在数据分析时折叠了性别分组。
误差方差齐性的Levene检验结果表明,二组的各项分数没有明显违背方差齐性。为进一步确认实验组和对照组起始条件的一致性,分别对年龄和前测分数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实验组和对照组平均年龄分别为4.56(0.36)、4.56(0.29),没有显著性差异(t= 0.05,p= 0.96)。两组的家长评分在所有项目上都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社交问题p= 0.13,其余项p> 0.38);而教师评分上,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家庭融入(t= -2.58,p< 0.01)、情绪调节(t= -2.24,p< 0.05)、多动问题(t= 2.30,p< 0.05)和同伴问题(t= 2.18,p< 0.05)上差异有显著意义。总体而言,实验组在前测中体现的社会情绪能力水平比对照组低。

表2 具体课程设置(以四岁阶段为例,共30课时)
3.1 描述统计
表3,4分别是家长评分和教师评分部分的描述性统计。为确认差异的显著性,固定组别对施测时间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固定施测时间对组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经Bonferroni校正,由于对同一数据集提出两个独立假设,显著水平收紧为通常的1/2(Ornaghi et al.,2015)。

表3 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描述性统计(家长部分)

表4 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描述性统计(教师部分)
为进一步检验幼儿情绪能力是否得到了显著提升,我们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分数增量(后测分数-前测分数)作为幼儿情绪能力提升的指标,对该差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5。由下表可知,家长评分和教师评分中,实验组的问题与困难都有一定的下降,而情绪能力的各项都有一定的上升。
3.2 干预效果
以时间为组内变量,实验处理(实验组与对照组)为组间变量,情绪能力的11个项目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2×2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功效估计通过偏eta方(ηp²)估计。
结果表明时间(家长F= 2.92,p< 0.01,Wilks’λ=0.61;教师F= 15.12,p< 0.001,Wilks’λ= 0.25)、时间 ×组别的交互作用(家长F= 3.25,p< 0.01,Wilks’λ= 0.58;教师F= 15.84,p< 0.001,Wilks’λ= 0.24)对量表得分效果显著。部分分量表分数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可见时间与组别有显著交互作用。单变量检验进一步说明时间×组别的交互作用在家长评分中主要对优势总分、情绪调节、同伴问题、亲社会性、问题总分和家庭融入效果显著;在教师评分中对所有11个项目均效果显著(均p< 0.001)。

表5 幼儿情绪能力提升的比较

表6 干预后幼儿情绪能力提升的综合比较
根据ηp²> 0.14代表较高水平的效应量(Richardson,2011),家长评分中情绪调节、优势总分和同伴问题能够各自解释一个较高比例的组间变异;而教师评分中所有变量项目都可以各自解释一个较高比例的组间变异,其中优势总分、情绪调节和家庭融入为解释量最大的3项。通过两个评分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综合考虑家长和教师双方评价,本训练方案对情绪调节、家庭融入、优势总分、同伴问题、问题总分以及亲社会性有显著贡献,其中以情绪调节、优势总分和同伴问题的改善最为突出。

图1 部分情绪能力变化趋势图
4 讨论
经过将近一年的教学,实验组幼儿与对照组相比,行为与情绪优势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心理适应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尤其是在情绪调节、入学准备、社交自信、家庭融入、优势总分、同伴问题、品行问题、问题总分以及亲社会性方面的改善相对显著,证明了该训练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4.1 教师评分与家长评分
4.1.1 教师与家长的评分差异
家长和教师代表了幼儿发展的两个典型人际环境。从结果的比较中可知,家长评分和教师评分既存在共性,也有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教师评分普遍较高。对家长和教师评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评分差异较小,且主要体现在前测阶段;后测中家长和教师评分均有显著的相关,体现了量表的评分者信度(结果未呈现)。然而,配对样本t检验说明了两种评分的确存在差异。家长对幼儿的优势与长处的评定都一致显著高于教师评分,而困难与问题、尤其是情绪问题和品行问题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家长对幼儿各项情绪能力的评定在总体上表现出“偏爱”倾向,即对幼儿优势与长处的评分更高,困难与问题的评分更低。
这样的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首先,家长评分由幼儿家长独立进行,他们往往缺少客观参照对象,因此主观性和波动性较大;而教师接触的同龄幼儿较多,因此评分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客观性。其次,情绪能力作为一种内化机制,其跨情境的表现具有内部一致性;而幼儿与家长和教师进行社会互动的场所、时间和形式都存在不同,情绪能力的情境表现也有所不同,这也就解释了家长与教师评分的部分一致性与差异性。
4.1.2 家长在幼儿情绪能力训练中的作用
本训练方案强调幼儿园应脱离传统的“寄养”关系,帮助幼儿建立家长-教师-同伴的三元人际模式;人际关系课程的课堂教学主要关注同伴关系的部分,幼儿在老师的引导下形成与同伴的良好互动,而家长通过家庭联系卡实现与学校课程的对接。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家长在幼儿情绪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家长联系卡可以让家长参与到课程进度中,促使家长对幼儿的发展变化给予更多关注。在课后,亲子间可以开展基于课程内容的对话,例如讨论今天在幼儿园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是否可以运用学到的知识自我调节和解决问题。这种积极的表达与沟通不仅有效地巩固了课程所学的知识技能,更增进了亲子间的信任和情感交流,有助于幼儿形成对父母的安全依恋,转而对幼儿的情绪调节、自我—他人认知、亲社会行为和群体关系产生积极作用(李彩娜,石鑫欣,黄凤,马婧,2013)。
4.2 性别与年龄
4.2.1 性别
本研究中不同性别幼儿在量表前后测得分上表现出较少差异,故未呈现性别亚组分析的结果,但性别对幼儿情绪能力及其训练情况的影响仍不容小觑。学前期女孩的情绪理解能力较强(Brown &Dunn,1996),拥有更复杂的情绪知识,更倾向于自发地调控情绪反应,尤其对愤怒情绪的控制能力较强(Brody&Hall,1993)。在人际交往模式上,女孩的互动更加迂回和亲密,而男孩的互动行为更加广泛,也表现出更多外化问题,例如多动和攻击(Rose-Krasnor,1997)。
对实验组情绪能力增量的受试者性别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未呈现),男孩的优势提升以及问题减少的程度都有超过女孩的趋势。研究表明性别、语言能力和情绪能力三者存在关联,语言能力较弱的幼儿、尤其是男孩,在情绪能力上也表现较差(Na et al.,2016)。本方案中情绪表达部分的课程目标强调,应帮助幼儿认识到语言表达是良好的情绪表达方式,并设计了很多情境表演来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能力得到充分锻炼后,男孩相对女孩也就表现出情绪能力的显著提升。
4.2.2 年龄
虽然我们对实验组幼儿的初始年龄与情绪能力各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均无显著性(结果未呈现),但年龄因素不能忽视。幼儿在4岁左右逐渐进入第一反抗期,独立性和自我意识增强,显得“任性”和不受控制,容易表现出较大的情绪波动(邹进,1985)。因此,虽然经过训练后情绪调节能力有跨年龄的显著提升,但年龄稍长的幼儿最终训练效果不如低龄幼儿那么好。这提示我们抓住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对幼儿尽早开展情绪教育。
初始年龄可能与幼儿情绪能力中的入学准备有关。入学准备包括思维策略、自我调节、执行功能等诸多要素,很大程度上是随年龄而成熟的(Blair,2002;Blair&Raver,2015)。鉴于入学准备在认知、行为和情绪上的丰富内涵,为提高幼儿的入学准备程度,应在不同年龄阶段给予不同侧重点的情绪能力训练。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有方案设计、被试选取和研究实施三个方面。首先,在设计该课程时,国家还未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因此设计人际交往训练时主要考虑家长、教师和同伴,较少涉及与兄弟姐妹相处的情境。其次,被试的选取不够具有代表性。一方面,被试幼儿的家庭背景比较特殊,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为国家干警,文化素质较高,与幼儿互动的能力也相应较高,所以在参与幼儿情绪能力训练的过程中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被试的男女比例高达5:1,考虑到不同性别幼儿的情绪能力存在差异,研究结论不能很好地推广。最后,研究计划在实施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虽然方案囊括了3~5岁幼儿,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只开展了为期一年的4岁阶段的教学活动。可以想见,如果完整地实施教学计划,幼儿情绪能力的提升将更加理想。第二,国外的类似研究选取的样本量一般是100~200名幼儿,本研究选取了两个班级共56名幼儿,相比之下样本量较少。第三,实验只做了前中后测,验证了短期内训练方案的有效性,但未能对幼儿进行随访,训练效果的持续性有待证明。
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地扩大样本,系统地考虑经济文化水平、性别平衡、地缘等因素。在训练结束后一段时间内进行情绪能力的随访,验证训练方案的长期效果。教学方案可以与时俱进地进行一定的修改,例如增加多媒体教具,增添有关兄弟姐妹和睦相处、正确认识和处理妒忌情绪的内容,并且增加对家长、教师的评估指标,增强多方面的沟通反馈。
5 结论
本实验研究证明,无论根据家长或教师的评价,系统化、本土化的情绪能力训练方案都能够有效提高中国幼儿情绪和人际交往能力,其中总体的情绪与行为优势、情绪调节能力和与同伴交往中的问题这三者的改善最为显著,其它各个方面也有一定的提升。因此,我们推荐对学龄前幼儿开展系统化的情绪能力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