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课:“次生口语时代”的知识表达
文/徐坚 郭文革 乔博
《解密教育的技术变革史》是北大新上线的一门慕课。4月在华文慕课上线,已完成第一轮教学。5月在中国大学MOOC开始的第二轮教学,本文刊出时也已结束。这是一门教育技术学基础课程,介绍了从口头语言、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到数字媒介的教育的技术变革历史。这门偏重于历史、理论基础的课程,采用了朴素的“白板+PPT+教师讲授”的视频录制方式。为了保持口语感,视频中保留了一些口误,并为大家提供了“勘误表”。
在课程的综合讨论区,有同学给郭文革老师“打Call”,表示“从第一节课追到现在,有种追剧的感觉”。在“华文慕课”的讨论区,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徐坚老师提出困惑。徐坚目前的主要精力是放在面向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的相关研究,听了郭老师的课程后发现,郭老师的课程内容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引入,可以说进一步加大了来自不同领域、跨学科的思考碰撞,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框架。
然而,结合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复杂感受,徐坚发现,相互碰撞的过程既会带来获得新知识的新鲜和兴奋,也会带来由于自己原有知识结构的颠覆造成的反思和痛苦。为此,徐坚和郭文革两位老师进行了一番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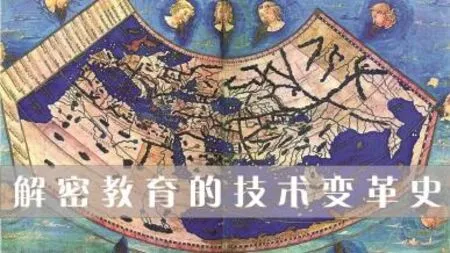
慕课制作者与学习者的动力
徐坚:我记得第一门慕课是美国一所大学计算机专业教授开的,当时通过邮件注册了,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之后这么多年,我从没完成过一门慕课的学习,每回一开头,然后很快就放弃了。您的这门课是我第一次坚持这么远的进度,我也有信心和动力必须要完成。我很好奇自己为什么这门课会坚持下来,想跟您探讨一下,您是如何录制慕课视频的呢?
郭文革:我之前一直在做线上小班制教学——班额一般在30人左右,比常见的SPOC规模还要小得多。这样的在线课程通常是以教学活动和高密度的交互为核心的。在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投入很多。在国外,线上小班课的收费和面授一样,少数还要高于面授。
我一直把慕课视频看作是一种和印刷技术时代的教科书对等的数字化阅读物,把师生交互松散的慕课,看作是一种可以和“作者对话”的“数字化阅读”行为。我不认为慕课完成率低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畅销书的“完成率”其实也很低,很多人跟风买回家之后,就塞在书架里,一页都不曾翻过。
作为一种知识的数字化表达样式,我们需要想一想,在互联网上应该怎样表达知识?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瓦尔特·翁提出的“次生口语时代”的观点值得思考。另外,我们还应该看一看,网上哪些内容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我本人比较喜欢“晓说”、“锵锵三人行”、“一千零一夜”,“圆桌派”、“吐槽大会”等,这些表达形态,还真的带有荷马史诗时代的口传色彩。
所以,我自己做慕课的时候,研究了很多样式,综合考虑了成本、时间、表达的自由度之后,选择了这种最朴素的、带有口语色彩的表达形式。那些达到广播级的视频,往往需要大团队大制作,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抠,我担心反而制约了教师的表达。
慕课制作过程中的勘误能否作为过程性教学资源
徐坚:您的慕课视频使用了口语、文字和互联网等多种媒介传播知识。口传很可能产生口误,PPT的文字也会有错漏,视频后期编辑时,修改口误的成本很高。所以,慕课中提供了“勘误表”。我还是第一次在慕课中看到勘误表!我很好奇,是谁来做的勘误?是您重看了一遍视频?还是您的学生?如果是您的学生,那么您的学生如何知道此处为错误呢?为何其他的慕课没有口误呢?
郭文革:我想绝大多数慕课都有口误,至少我认真看过的几门都有口误。没有勘误的原因,一是有很多慕课,是提前写好了文本,配合PPT做语音合成。这类慕课,没有口误,但也失去了口语的鲜活感。二是有的慕课由老师录的,但是老师自己都没有看,所以,没有发现口误和笔误的地方。
我的慕课,至少全部看过一遍以上,所以,很多勘误是我自己发现的。我愿意看我自己的慕课视频,这也许是现在你能看到勘误表的一个原因。
徐坚:慕课学习的学生能否加入勘误的队伍?理论上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我是来学习的,我如何发现慕课内容上的错误呢?错误本身也是一种教学资源,慕课内容的勘误过程是否也能设计为一种学生参与互动的教学资源呢?学生作为内容的消费者,是否同时也是内容的生产者?
郭文革:在慕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确帮我们识别出来好几处口误,以及测验题中的错误。但是,对于学生作为“内容生产者”的提法,我认为还是要谨慎对待。知识生产是一个长时间高脑力投入、还需要相关经济支持的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学生生产的“内容”跟专家生产的知识是不一样的,需要对知识生产的环节和流程有清晰的认知,才能想明白这两类知识的差别。笼统地这样说学生是内容生产者,很容易制造混乱的概念,产生“反智主义倾向”。
慕课制作者的经验总结
徐坚:尽管您的授课内容是经过多年的准备,但是最终呈现在慕课中的内容也许只有数个小时。同时,录制的时间估计也就是2-3天左右。你录制慕课的时候,主要做了哪些准备?
郭文革:我的慕课录制不是2~3天。去年一年,我几乎把以前涉猎过的资料,都重新梳理了一遍,包括我在慕课里提到过的书、纪录片,全过了一遍,还要做摘要,以保证出现在屏幕上的引用不会出错(笔误有,但所有的引用在工作文件中都是有索引的)。另外,还要注意理论内容、真实的故事、图片、视频材料的合理搭配,探索“次生口语表达”的叙事方式。这是我在准备慕课的时候,最头疼的任务。因为我需要在网上观看并分析大量的“次生口语时代”的优秀内容,揣摩表达的方式,以及合理的素材搭建结构、呈现方式。
即使这样,这门课还是录了两周时间,是专门为屏幕前的学习者录制的!我的3-4个学生,也花了很多时间,剪接成现在的样子。她们一遍遍看,还要减掉录制中的口误、打磕巴、重复的地方;甚至修改PPT中的文字。
我打招呼的用语、包括眼神,都是希望能和屏幕前的学习者有一种对话感。有几天,在白板前站着录了5-6个小时,录完真的觉得脚底板都要碎了。所以,看起来这么简单的形式,其实还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什么事情是轻易能做成的,背后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徐坚:慕课似乎并不能替代传统的课堂?您以前一直做线上SPOC教学,第一次开设慕课,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郭文革:慕课给我的第一个Shock,就是面对满屏的ID、QQ号、手机号的“学生”,有点茫然(掩口笑),无所适从,不知道对话的人是谁,然而,SPOC课程通常是实名,这也是慕课和SPOC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活动通常是“破冰”,做自我介绍,让后续的教学对话都能以名字、或者你互称,营造一种温馨的班级氛围。在慕课中,老师是实名,学习者都是匿名,感觉很不对等,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徐坚:您的课程,把跨学科的知识整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逻辑,我觉得这样跨领域真的很有趣,我一定要坚持完成这门课程,拿到我的第一份慕课证书。但是,我也担心您的课程可能很难得到各个领域的认可。比如技术领域的人,他们总是要看先进的技术,不太去回顾历史。教育领域的人,会认为您的课程不对头,怎么跑到新闻传播领域去了。新闻传播领域的人,可能又会认为您是做教育研究的。这两天,我在看您推荐的纪录片《书香》,发现原来书籍是最早奢侈品,为了豪华越做越大,真的很有趣。又看了《1984》的封面设计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我也觉得很有趣。《媒介史》对于理解当时的社会、阶层和人的心理状态,的确非常有启发。
郭文革:的确,大家都在提倡跨学科,但真正跨学科的研究,又会在成果认可方面遇到很多困难。当大家都身在“此处”的时候,很难看到“彼处”的风景。这也恰恰是在线教育、慕课面临的挑战。
徐坚和郭文革通过一番探讨得出一个结论,现阶段的慕课视频,还处于“新瓶装旧酒”的阶段,即把原来印在书上的知识,“装进”互联网。未来随着基于“大数据”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可视化、交互式、VR等新的知识表达形态的成熟,资源建设将进入“新瓶酿新酒”的阶段,大量新增“知识”,已经“生产”出来就是“原生数字化资源”。到那时候,在线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比重,将发生关键性逆转,人类教育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