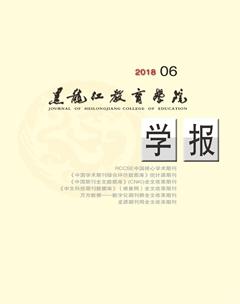消费文化视域下都市女性尊严感的获得、身份的认同及其反思
刘洋
摘要:2016年12月在亚马逊平台上热播的日剧《东京女子图鉴》引发了热烈讨论,该剧讲述了绫从20多岁到40多岁的成长过程,主要受众群体是都市中像绫一样的万千女性。基于此,从消费文化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女主人公在成长经历过程中由于受到消费文化的浸染,对其生活、尊严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系列影响,探讨消费文化下,炫耀性消费对于都市女性尊严的获得及身份认同。以反思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力求对于都市女性起到警醒与修正的作用。
关键词:消费文化;女性尊严;身份认同;尊严经济;炫耀性消费
中图分类号:I106.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8)06010404
引言
在消费文化情境中,城市女性消费是消费主义文化中的典型。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万花筒,各种刺激急剧增加。城市人为了显示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几乎都有一种从事怪异行为的冲动,标新立异的行为,这就变成了城市生活的常见现象。从这个视点去透视在这种场域中的女性消费,便有了明确的注解。另外,按齐美尔所描述的,大城市的特性是个人主义、个性、自由、非人性、理性和非情感化。在这个陌生人社会、喧闹的城市、络绎的人群中,个人被淹没了,同时也为个人私生活提供了广阔空间,消费也便成为“最自我”的行为。
城市女性由于其特殊的生活及发展环境,在全体女性群体中处于最先接触社会新动态的位置,这一特殊的境遇致其在都市及消费文化盛行之下产生了尊严获得及身份认同的诸多问题。
一、日剧《东京女子图鉴》故事背景
老家住在秋田县的绫,从小就跟其他安安稳稳的女孩子不太一样。当老师询问她人生的目标时,她的想法是,成为人人都羡慕的人。她一个人坐在秋田县的海边,静静地想着为什么自己没有出生在纽约、伦敦、堪培拉这样繁华的城市,而是秋田这样一个无名小城。她在心里埋怨原本生于东京,却因为爱情嫁来秋田县的母亲,以至于她也失去了成为东京人的权利。与周围以“平凡地过一辈子就可以了吧”的女孩子们不同,绫一直向往着东京的四衢八街与华灯璀璨。终于有了机会,在高中的一个暑假,绫背上行囊随母亲去东京旅行。人来人往,林立的楼宇之间,在秋田人人称之可爱的绫一心以为自己可以被街拍记者看到,故意在记者面前走了好几个来回。但是记者选择了打扮洋气的都市女孩,并在绫面前刻意对其冷嘲热讽、加以嗤笑。绫透过奢侈品商店的玻璃,落寞地看着自己没在高档理发店修饰过的头发,还有那一身没有一个名牌标识的不入流的装束。绫告诉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来东京努力工作,登上时尚杂志,真正成为人人羡慕的人。
以上的故事来自2016年日本亚马逊平台开播的网络剧,该剧改编自在《东京日历》上连载的同名四格漫画。讲述了绫从地方大学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东京从底层工作做起,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最终逐步踏入了时尚行业的管理层。她最早居住在三轩茶屋(位于世田谷的平民区,多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居住,市郊),后来逐步搬去惠比寿、银座、丰州、代代木上原、港区(商业设施丰富的市中心,房价处于日本最高水平,大学、媒体、使馆和高级别墅林立),最后在东京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不大却温馨的房子。绫一步一步走向了期待中光鲜亮丽的生活,衣柜里的衣服越来越昂贵,出入的餐厅越来越高级,品位越来越高,包括交往的男友也稳步升级。
该剧一开播,便受到大众尤其是都市女性的大力追捧。很多人表示,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有人是20岁的绫,还跟初恋男友站在高档餐厅门口感叹不知何时才能攒够进去吃一顿饭的钱;有人是30岁的绫,换过几任男朋友却依旧渴望稳定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有人是40岁的绫,离婚后时常跟几位“志同道合”的单身友人一起插花打发时间,其间也偶尔会有激进分子向大家阐述生养孩子的坏处。该剧绫的扮演者水川麻美表示:“绫因为憧憬华丽绚烂的东京而来到此地,每一天都在东京的生活中寻找人生的对与错,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整个剧组每天都在东京的中心城区拍摄,希望这个故事能让观众们找到共鸣。”[1]
当代都市女性的的确确在这部日剧中看到了一幕幕自己的影子。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里,总有许多像绫一样的女孩子,她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来到这里,一边像男人一样为生活抛头颅、洒热血,一边又要维系自己女人的形象来讨好男人,以得到一份真挚的爱情和富足的生活。但这个社会往往并不青睐这些女性,她们要么成为工作领域的铿锵玫瑰,但是孑然一身;要么放弃事业,回归家庭成为贤妻良母,很少有人能做到两者兼顾。诸如此类的现象不计其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貌”和“无能”这两个毫不相干、完全属于不同范畴的词语,在都市女性身上画上了等号呢?是什么,让都市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顾此失彼?又是什么,在人们心中烙下了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二元对立观念,使得都市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迷失了对于自己原本的身份认同?本文将着重于以消费文化视域来看待受到消费文化影响,像绫一样的都市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两难选择,并结合多领域对以上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
二、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最初起源于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政局趋于稳定,资本主义经济也在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发展,资本成倍累积,此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逐步趋于稳定。随着人民的恩格尔系数越来越低,人们不再为衣食温饱而发愁,转而关注自己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的非使用价值。这个时候,文化诉求和文化纬度就不断变高,消费文化也便应运而生。
葛兰西认为,文化消费实质上就是在社会实践中文化被更替和再创造的过程。消费者在消费时必定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把消费产品挪用成特定的文化符号,这时商品所表达的意义便不再是其使用价值[2]。在现代社会,消费文化的风生水起,使之开始重新建构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正如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所阐释的“炫耀性消费”,他认为,人们消费特定的物品是为了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地位,從而获得他人的艳羡或重视[3]。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女性消费趋向成熟,其消费观念与行为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在追逐流行时尚潮流中彰显个性魅力。在此特定情境下,都市女性对于个人尊严感和身份的认同的变迁便变得发人深省。
1消费文化下都市女性个人尊严获得
都市女性以高价商品、标志物商品,甚至是远远超出其消费能力的奢侈品消费来满足其非个体本身需求之外的欲望。期待被街拍时的绫因为衣着老土而被排斥,街拍记者、受拍的摩登女性,还有周围往来的时尚人群和沿街林立的奢侈品商店,无一不在无形中敲击着绫躁动的内心。在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态势之下,女性的身体、外貌和社会角色在消费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新构造,这使得女性身体走向商品化、客体化的消费时尚[4]。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并在心底推翻了对自己原有女性外形期待的认知,在不知不觉中试图以消费文化下的“炫耀性消费”来建筑起自己的社会归属感并获取他人认同。
地方大学毕业后的绫只身一人来到东京,租住在二十几岁的女性集中分布的三轩茶屋。在这里,绫遇见了她的初恋男友直树,两个人出身相同,连老家都挨得极近。恋爱后两个人便住在了一起,共同吃一份热气腾腾的泡面,也时常去路边直树喜欢的那家章鱼烧店沿街吞咽。这样的安稳的幸福虽然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却使一心上进的绫感到惶恐不安。终于在一个早晨,阳光透过窗子照进他们小小的爱巢,打在绫正要穿的内裤边上。绫盯着上面斑驳的毛球深思,这真正是她追求的一切吗?跟直树在一起很幸福,幸福到她开始迷茫,但是这样的幸福在秋田到处都是,那么她来东京又是为了什么呢?她要步母亲的后尘了吗?尔后,绫选择了“无论何时脱掉内衣都不会丢人”的生活。在一个无人的午后,绫打包了自己所有的行李,迅速逃离了直树和那种遍地都是的幸福生活。
步入新生活的绫迅速在同事组织的联谊会上认识了她的第二任男朋友,新男友毕业于一流大学,是一名年收入800万日元的商界精英。为了与精英男在生日那天去高档法餐厅Joёl Robuchon(米其林三星法餐厅,人均消费2 000元人民币以上)约会,绫不惜承担高额利息分期付款购买远超其经济能力的礼服,然而绫却万万没想到,精英男在她生日当天因为“工作繁忙”而未能赴约。普赫曾提出过一个“尊严经济”的概念,该概念强调消费者消费行为与消费者个体尊严和群体归属之间的重要关联,阐述时尚消费对都市白领女性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生活的形塑[5]。虽然绫本身并没有在Joёl Robuchon餐厅出入自如的能力,但绫寄托于通过消费价格高昂的晚礼服,来使自己看上去有这个能力,通过过度无脑消费来换取自己的尊严和上层社会的归属感。
消费社会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极大满足,在消费社会中,都市女性通过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意义与象征,来得到自己身份的建构、地位的确立和个性的展示。然而,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的社会里,真正拥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按照消费主义为主流的生活模式去消费的,仍然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少数人群体。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观念已经深深嵌入到许许多多像绫一样的都市女性心里,周围悄然四起的消费文化之风也使得她们不得不亦步亦趋地生活、消费。甚至,女性的消费已然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5]。
那么,都市女性消费的主要方面都有哪些呢?根据张慧玲的统计,女性消费主要集中于“三品一装”上,即化妆品、保健品(保养品)、食品和家庭装饰。早在2006年,仅在我国,美容化妆品行业每年的GDP便已经高达850亿元人民币,另外保健品(保养品)市场年销售额达到500亿元人民币,家庭装饰年消费能力则高达2 000亿—3 000亿元人民币。通过以上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女性尤其是都市女性的生活方式和关注比重。品牌消费对于女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女性投掷大量资金用于个人容颜的保持、身材的完善和气质的提升。克里斯·西林(Chiris Shilling)曾指出,在现代社会,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消费文化下派生出的身体消费也使得女性对于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的认同越来越模糊,女性需要通过对身体的良好建构、外在形象的高度关照,树立个人信心。在消费社会里,被异化了的女性身体和外在形象成为女性自我认同、获得尊严和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
2消费文化下都市女性的身份认同
跟第三任“男友”——已婚的高档和服店老板在一起后,绫的生活品质直线上升。当然,这时候的她也已经不再是那家小公司的底层人员,绫成功地跳槽到Gucci的管理层,过上了拿年薪的生活。和服店老板事业有成、深情款款并且品位不俗,带绫去约会时会送给她Mannolo Blahnik(意大利女鞋奢侈品牌,普通款高跟鞋价格在人民币10 000元以上)的高跟鞋。他认为鞋子体现人的品位,而绫脚上的鞋则会让他丢脸。和服店老板跟绫说,除了婚姻是不能给她的,其他一切都可以。作为补偿,他会带她享受这世间一切奢华而美好的事物。
因为和服店老板的出现,让原本就扎根在绫心中的消费文化观念愈演愈重,感受过美好而昂贵的事物后,绫更加坚信这一切的“意义”。此时的绫登上了杂志,当然,不是街拍而是采访,作为“人人羡慕的女人”,向广大女性诠释她秉承的幸福观。绫成为了一名成功女性,但她总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够完整,再去参加聚会时,她因为未婚、未育而无法和曾经的朋友交流,她开始被这个世界的普世价值观所引导,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从父权社会接替母权社会开始,社会衡量女性的尺度和标准便非常单一:嫁个好人家,相夫教子便是成功女性的模范。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需要依托于其丈夫和儿子才能得到实现,即便是在新时代的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在女权运动为女性争取合法权益的情势之下,女性价值的衡量体系却依然普遍停留在过去。
绫告别了和服店老板,绫开始注册婚介所,参加相亲。在快餐式的相亲会上,无论是容貌、气质,还是能力都鹤立鸡群的绫却无人问津。婚介所的工作人员建议她不要穿太名贵的套装,这会让男人感到有经济压力;不要留短发,男人喜欢温柔的长发;不要做看起來老气横秋的美甲,男人喜欢靓丽活泼的装扮。她努力挣来的名牌服饰曾经给她赢得了尊严,她践行着消费主义社会给她的认知和准则,可工作人员口中残酷的现实又让她非常迷茫,她的一切努力,仅仅因为性别是女,就失去了价值吗?
已经变得有些绝望的绫随便找了一个条件还算不错的男人结婚了,婚后又因为一直没有孩子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丈夫在两人分居后出轨并且女方怀孕,绫再次成为单身贵族的一员。女性的幸福在未婚时被别人定义为结婚,结婚后又被定义为声誉,关于女性幸福的定义却从来没有像这个社会对男性的期待那样,这个社会不会给女性以建功立业的期待,也不需要女性大展宏图。一旦有违背这一定义的女性出现,如女博士、女强人或剩女,偏见和诋毁足以击垮这些有抱负的女性。
绫决定不再盲目寻找另一半,她已经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有了深深的迷惘。女性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女性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就是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向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转变过程,这是个接受社会影响的过程。刚出生的女孩只是生物意义上的女性,随着女孩的成长,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逐步把她变成了“女人”这一社会角色。家庭是女性身份认同形成的主要场所,但社会对于女性身份认同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这个社会给了女性过多错误的信号,导致大部分女性在传统的性别二元对立环境的熏陶之下,逐渐接受了这种男强女弱的二元对立看法[6]。
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市女性虽然对于自己有正确的身份认同,她们也的确不断通过个人努力,甚至是迎合消费主义文化的方式来试图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不过斗争结果显然是差强人意的。
都市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消费来创造出一个美满的理想形象,从身体到心灵,这是对自我的一种认同,认为“女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与此同时,也是对自身素质提升和自我能力的实现[7]。消费文化使女性的个性得以张扬,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尊重,从而使自我身份得以认同。可社会固有的性别二元对立,却使其逐渐在这个过程中丢掉自己构筑的尊严,再度迷失。
剧情结束的最后一幕非常有趣,绫挽着一起相依为命的男闺蜜在小区散步,旁边一对衣着华丽、气质不凡的夫妇与他们擦肩而过。镜头扫过去,那个背着名牌包、身着皮草的贵妇人竟然是绫的面庞。消费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符号化建构导致了女性身体与自我的分离,这个符号化的身体和物品构成了一个同质的符号网络,承担起体现消费价值的符号性功能,具有“非我”和异化的特质[8]。
正如拉康的镜像理論,绫在自己希冀成为的上层女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绫将现实的自己与想象的自己混淆,纵然有着风霜雨雪的经历,但最终也没能真正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没能发掘出自我的真正价值,还是循照消费主义文化为这个社会构建的女性形象和女性价值观生活着。
三、树立正确价值观,正视女性自我身份以谋得尊严
自二战以来,消费文化在全球化之下大肆风行。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的“地球村”概念,西方消费文化在全世界迅速传播,我国也难以幸免。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认为,我们消费的并不是物品,而是各种符号。消费文化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充斥于都市女性的周围,是选择随波逐流寻求“尊严”,还是坚持本我获得尊严,使得无数人为之彷徨。在这样的过程中,都市女性的身份认同和尊严获取便变得进退两难。在当今社会,女性对自我形象的追求具有了较强的主体性,但决不能否定其未受到消费文化和传统性别文化的束缚与影响[9]。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我国而言,消费文化是妨碍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利于绿色、健康经济发展的壁垒。《“十三五”规划建议》提示,要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品,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由此可见,构建合理的消费方式包括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合理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促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科学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
艾玉波指出,我们要利用现代媒介传播绿色女性消费文化;提倡绿色消费,构建生态消费文化;多方位出击,营造绿色消费文化氛围。从反对攀比、“炫耀性消费”和过度消费入手,提倡绿色消费[10]。
曹文婕认为,我们要塑造女性表达自我主题意识与个人价值的消费观,培养多元化的女性审美标准,规范大众传媒和媒体文化。从女性本身到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以及舆论传播的多角度来树立女性自信和尊严[11]。
我们期待女性能够真正主宰自己的人生,不再对身份认同感到迷惘,塑造出真实、本我的女性形象,真正获得其所希冀的女性尊严。
结束语
在消费社会中,个人不再以拥有物品来相争,而是在每个人的消费中去到达自我实现。女性对于自我的追求和实现,在消费文化下被激活。可以理解女性的本意是希望通过此般消费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建构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但是受其主体地位的逐步丧失影响,使得女性越来越追求虚无缥缈的事物,从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诉求。出于尊严的获得和身份认同,女性消费在消费市场中愈加彰显。作为炎黄子孙,当代都市女性一定要看清西方消费文化对华夏大地民族个性、民族自信和民族前程的极大危害。女性尊严的获得及身份的认同在于自强自立,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母性的承载、阴柔与慈爱功能,在于女性通过其不懈努力为人类物质的丰富、心灵的成熟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远非在于物质资源的无原则浪费以及对虚荣的追求。另外,反思消费主义风行的负面影响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和都市女性的严重危害,打破原有的性别结构二元对立,积极正向引导女性消费,助其树立起正确的女性自我身份认同,从最广泛的层面上予以都市女性基本尊重,这一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水月麻美《东京女子图鉴》展现华丽真实的东京[Z/OL].腾讯娱乐,20161125.
[2]Antonio Gramsci.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M].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1929.
[3][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吴小英.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9(2).
[5]肖索未.“时尚的重要性”——消费文化、婚外包养与都市女性的“尊严经济”[J].文化研究,2016(2):82—91.
[6]张慧玲.女性消费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7]郭彩霞.女性身份认同浅析[J].工会论坛,2012,18(3):160—162.
[8]陈晓敏.消费主义文化中城市女性消费[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8,5(3):10—12.
[9]李庆,杨格新.身体消费与“灰姑娘”的童话梦[J].当代外国文学,2017(2):63—70.
[10]艾玉波,庞雅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女性消费文化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5(1):154—160.
[11]曹文婕.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女性消费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