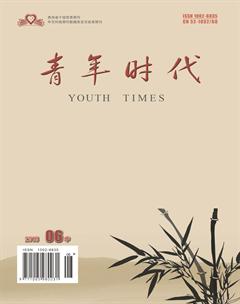尼采的“酒神精神”与中国“魏晋风度①”的比较
王璇
摘 要:尼采和魏晋士人都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悲剧性时代,为了追求美好生活、避免人生的悲剧性,尼采提出了强调个体自由、肯定生命价值的“酒神精神”,魏晋士人形成了任诞自然的“魏晋风度”。本文主要通过形成背景、具体内涵以及应从对悲剧现实的应对态度上比较尼采的“酒神精神”与中国“魏晋风度”来帮助我们建构心灵,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關键词:酒神精神;魏晋风度;生命;审美的人生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以强调个体自由、忘我超越的“酒神精神”作为整个悲剧艺术的内在核心。中国魏晋时期的士人虽与尼采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理环境中,但他们都清醒地看到了此在世界的永恒悲剧性,都注重人的内在精神气质之美的培养,都肯定生命价值,并提倡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追求自由幸福。
一、人何以承受悲苦人生
尼采生活在19世纪德国的战乱时代,他虽然出生于宗教世家,但他后来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徒”。未满五岁父亲就病死,于是在女人的周围与养育中长大,日后却成为顽强的反女性主义者。因为孤独,尼采的心灵旋即被两种艺术所充实: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罗斯的悲剧,以及瓦格纳的音乐。尼采在他探索人生问题的一开始,就遇到了叔本华,并且默默接受了他的悲观主义。在他看来,此在的生命只是强力意志的轮回世界中一个小小的轮回环节,此生的所有事物似乎在永恒的生命循环面前都变得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在他的世界中,上帝死了,不存在宗教所咏叹的生命彼岸。现实世界是悲剧性的,现实中的人最终都将走向死亡,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就是作为一场永无止境的悲剧在不断地上演。正如借着西勒尼的寓言:对于人绝好绝妙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乌有”[1],相对应次好的是——早死。他提出了一个沉重无比的生命哲学的问题:活着如此痛苦,人生是如此惨淡,我们何以承受此在?为了回答它赋予人生以意义提出“酒神精神”。
魏晋名士们同样生活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火纷飞的时代,政治腐朽,乱党专政,整个社会和人伦秩序都陷入混乱之中,人与社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正如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抨击当时社会“名利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驰,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2]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3]。因为太多死亡的刺激而产生的伤逝之情,一直弥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例如《世说新语》中《伤逝》篇有19条,全写魏晋名士对死者的哀悼和恸哭,集中而强烈地表征着魏晋人的悲情体验。在儒家礼教的监控下人们的正当欲望、审美需求、创造精神被遮蔽了,连最起码的生存需要都无法满足,更别说如何在这这充斥着悲剧色彩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了。加上中国古代文人仿佛天生的忧患意识,他们发出了与尼采同样的呼声:人何以承受悲苦人生?从而形成了“魏晋风度”。
二、酒神精神与魏晋风度的具体内涵
尼采在在研究希腊悲剧的起源和本质时相遇了狄奥尼索斯,发掘出了自由而慷慨的原始生命力量的“酒神精神”。它是一种原始本能的冲动,象征情绪的激动、亢奋,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迷狂,[4]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他在《悲剧的诞生》中第一次对“酒神精神”这个现象作了心理的分析[5]。悲剧是日神和酒神的结合,但本质上是酒神精神。“日神和酒神都植根于人的至深本能,前者是个体的人借外观的幻觉自我肯定的冲动,而后者是个体的人自我否定而复归世界本体的冲动。”[1]在悲剧中,个体毁灭了,但是它使人们回到了世界生命的本体,因为对于世界生命本体来说,个体的不断产生又不断毁灭正表现它生命力的丰盈充溢。“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1]“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制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1]例如尼采赞扬古希腊人而鄙弃古罗马人,因为古希腊人崇尚的是内在生命的伟岸力量,永恒的内在的生命力量才是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强大的真正标准。肯定生命就必须肯定生命的全体,包括肯定其中必定包含的个人的痛苦和毁灭,这是酒神精神的真髓。伟大的幸福正是战胜巨大痛苦所产生的生命的崇高感。[6]一个人在“直面惨淡人生”时要像海明威笔下的硬汉一样——可以被消灭,但绝不能被打败。尼采从根本上转变了传统生命价值观建立的基础,把生命的意义由基督教虚无缥缈的彼岸转换为立足现实的、活生生的此岸,以生命力是否强大作为评判生命价值的标准。
与“酒神精神”所崇尚的自由天性有着极大相似性的魏晋风度,体现在士人们任诞自然、清俊通脱的精神气质和饮酒、服药、清谈、纵情山水的生活理念。魏晋以其黑暗沉重著称于中国历史,同时也以其灿烂的思想文化深深地吸引后人。这个时代宗白华称“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3]鲁迅称是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冯友兰称其为“风流自赏”的时代。这个时代玄风大畅,道体自然,人们通过哲学、文学、绘画、音乐乃至书法抒发自己对宇宙、对人生的感悟与领会。[7]“魏晋风度”指一种遵循内心而不是迎合世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冯友兰先生曾归纳说“魏晋风流”有四个条件,即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有深情。[8]“玄心”说的是心灵的超越感;“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的真知灼见;“妙赏”指的是精妙的审美能力;而“深情”指那些真正风流的文人对于万事万物、宇宙人生都产生一种深厚的同情。魏晋风度的表现以人物品藻为核心,日月山川、风云雷电、林木禽鸟、珠玉宝石等自然界中的各种景观物象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美好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被魏晋士人广泛用来品题人物、描摹人格。例如《世说新语》里关于人物的评价“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谡谡如松下风”“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等等。
三、如何应对此在人生
现代社会中“上帝死了”,人是疏离的、孤独的存在于这世界上的,尼采把这种存在称作是“生活在险境中”。[9]他希望借助酒神精神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来挽救陷入精神危机的人类,让人们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和人生,这是一种悲剧乐观主义。在酒神的世界里,人们可以尽情挥洒自己蓬勃的生命力,展现人的本质力量,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进入一种审美的境界。“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2]他说“怯懦的眼睛不可能感受到美”,[6]美必须表现出生命和力。他呼吁人们“去生活在危险中……活在与你相匹敌的人物甚至在自己交战之状态中!”[6]生命的悲剧性并非给人类一个否定自我生命价值的借口,而是赋予人类挑战自我、在激流中逆流而上、尽情展现自己蓬勃生命力量和追寻自由尊严的机会。
同尼采“上帝死了”没有彼岸世界的观念相似,魏晋时代的士人们并没有把“人”之“在”安放在彼岸世界,在情感、语言、艺术、山水赏会中体验生命之“在”。他们看破生死、坦然面对此在世界的悲剧性,通过流觞曲水、吟诗弹琴尽情展现此在的生命价值,这便是生命意志的自觉,一种“游”的生活态度,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与尼采的酒神精神相比,士人们更重视的是肉体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逍遥,而尼采的酒神精神意不在酒,从根本上是鄙视酒、沉醉和感官享受的,他说“酒和沉醉与我何干!热情洋溢的人何须乎酒!他甚至心怀厌恶鄙视这药和药剂师”[2]。而士人们往往好酒服药来达到与宇宙合一,把握永恒的境界,表现出来的气质却是抑郁、沉重的。他们伴着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放浪形骸、流觞曲时畅叙的是一种幽情,缺乏一种力量之美。尼釆的思想虽然有些激进和偏执,个人主义和非理性倾向过重,夸大了酒神式的文化力量对社会的作用。但酒神精神中虽然面对人生悲剧性仍要奋发向上的刚性气质值得我们学习,同时魏晋士人们任诞自然尽情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气质风流,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吸取借鉴。
四、结语
现代社会较尼采与魏晋士人而言虽稳定安全,但信息爆炸、日新月异,人们面临着许多挑战,承担了更多的压力,精神世界必不可少染上更多的悲剧色彩。十九大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为了避免新时代矛盾所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有益于人类的身心发展,我们可以通过辩证吸取尼采的“酒神精神”与魏晋士人的“魏晋风度”中的积极思想,从而对比分析今天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帮助我们追求幸福生活。
注释:
①魏晋风度:因为学术上借用“魏晋风度”一词的较多,故本文借用“风度”而不用“风流”。
参考文献:
[1]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107/3/56/71/105/238.
[2]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
[4]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42.
[5]尼采.《瞧,这个人:尼采自传》[M].黄敏甫,李柳明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75.
[6]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73/265.
[7]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的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2:2(序第二页).
[8]冯友兰.《論风流》[J].载《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11.
[9]牛宏宝.《现代西方美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96.
[10]尼采.快乐的科学[M].于洪荣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