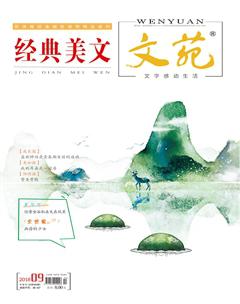教师节特辑:名家笔下的恩师
我旁听过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考证分析,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薄,又限于天賦,虽还不能论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也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的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有时候在校内林阴道上,会见到陈师去上课。他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在这一方面,他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真正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啊!
在课外的时候,她教我们跳舞,我现在还记得她把我打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在假日里,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家里和她朋友的家里。在她朋友的园子里,她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
她爱诗,也爱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教我们读诗的情景,还能背诵她教我们的诗:
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今天想来,她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像这样的老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她,怎么会不愿意和她接近呢?我们见了她就不由得围上去。即使她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她,连她握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什么。沈先生讲课非常谦抑,非常自制,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他最不喜欢刻板的生活,常要做些很憨的动作和说许多趣话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如果不了解他的学问,谁也看不出他是教授。他对自己从来不讲究,但却极认真地办理别人托他的事。我几次在学校碰见一些请教学问的和办私事的人,在一旁的人就说:“你去找蒙老师!”蒙老师在中文系是最忙的人。
毕业之后,我练习创作,他已经是知名的文艺批评家。作协陕西分会在太白开会,会上大家对我的创作说了许多鼓励的话。那一个晚上,他却叫我一块儿去散步,严肃地指出我创作中的许多不足,要我冷静头脑,扎实创作。我们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走过去又走过来,一直到深夜。
他喜欢喝酒,甚至有些贪杯,为了他的身体,师母曾严厉限制过他,我们在一起时也劝他少喝。一次他到我家,我拿了酒敬他,炒几盘小菜,因为他喜欢吃辣,我的小女儿也喜欢吃辣,两个人很快吃完了那盘辣豆腐。他说:“这孩子有个性,和我这个客人抢吃哩!”因为高兴,他喝得多了点,我和他到学校,偏巧遇到师母,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当时很尴尬。师母说:“你老师有胃病,以后不要让他喝酒。”从此和他在一起很少再敬他酒,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在酒桌上还提到他,说今后一定要多劝他少喝。
一个月前,我有事去找他,我们就蹲在校外的马路边上说话,他气色很不好。我说:“你近来身体不好吗?”他说:“是不好。”我说:“你要多保重才是。”他说:“我有个预感,可能随时就不行了。”我吃了一惊,劝他别这么想,不要太劳累。他又谈了许多他主管的作家班的一些事,还谈了他的小女儿,甚至谈到家里的那只猫。
现在蒙老师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做学生的一见面就提到他,眼里充满泪水,尘世真是好人难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