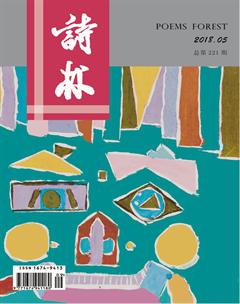乡村简史(组诗)
梁梓
晚 钟
黄昏是神给予我们的一个金币。
众鸟归林,好收成对它们来说也无所谓。
土拨鼠。它们大多数是隐于地平线以下,
眼含泪水的人是我们
很多时候有着相似的、被驱逐的孤独和命运,
只是它们很少说,很少向谁表达
它们从不想活着这件事儿
到底是不是一个谬误
小心地走过草地的人,不是怕露水打湿了鞋子。
使用铁镢头,也总是不敢过于用力。
我知道我这样做毫无意义。
有多少想起家乡,就要想起教堂的人?
有没有人说起教堂的尖屋顶是一把利器?
有没有谁说得清
晚祷的钟声是一把什么样的钥匙?
这是怎样事实?所有的黄昏都像同一个。
我们的人生就像站在金币的背面。
可是我终要耗费掉我的一生啊!
寻找远山般地寻找发光的钥匙。在此之前,
要种好田园里几垄土豆,几垄芝麻,
要喂饱院里的鸡鸭,要准备好一只削好的铅笔。
要等到夜空里的猎户蓄满力量,等到小熊和
大熊。
等到晚风吹来。刺玫瑰微亮的香气。
黄 昏
散步的空隙
夕阳已把金子涂在高大的树上
霜打过的叶子。闪烁着短暂的荣耀
稠密的手稿。发光的手稿
隐匿其间。麻雀部落的臣民在朗诵
它们说流利的语言,铁匠铺的语言
嘈杂的间隙——
获得巨大的安静
像河水停滞,打着小小的旋涡
黄昏总是弥漫着神秘的气息
多年后,异乡,一个破旧的朗木寺
几个沙弥大声诵《地藏经》
寺庙的犄角撑着一片金光
我想到——
如果不是有一种可以托住光的事物
天很快就会黑下来
刺 头
我说的是“刺头”,是植物中的异类
鸟雀不会吃掉它们,牛马也不啃食
刺头。这没有用的东西
它只对自己有用
它总是长得很茂盛
此刻它们粗大的枝秧,即使枯黄着
也并不影响我判断
它在夏日里曾经开过美丽的白花
而此刻荒芜、尚未有绿色的早春
站在沟边儿的刺头
手里攥着一粒粒种子,不忍放下
像是在犹豫
哦!刺头,这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家伙
它不得不活得比消失的同伴更用心
我不知道刺头面對它自己的明天
用喜悦,还是悲哀
松 针
枯黄,并没腐烂
保留着原来的形状。密密麻麻
遍地松针,我止住脚
松针或许并不是死掉?
树冠里有空出的间隙,明亮着
围拢着的是一些新生的松针
那些被松针围拢的明亮
它也是松树吗?它在松树的时间和秩序里呀
我的身体里,也有明亮的部分
被身体和类似松树的气息用心地围拢过
只是经历过后,现在如同虚无
我知道,记忆也会最终消逝
毋庸置疑,树上的松针
有一天也会枯黄、落下来,带着它的时间
麻 雀
我捏碎过有黑褐色花纹的蛋壳。
触摸到幼仔湿润,温热,光滑的身子。
用弹弓打下来过秋天的肥麻雀,
捏断过它的脖筋,吃它肉的时候叫它老家贼,
后来它们看见我,就吓得像子弹般射向天空。
这么多年,麻雀像钉子一样楔在乡野,
总有一只或几只代替消失的那些活下来,
在枝头叽叽喳喳,
在大地上跳着走路。
葵花田
执迷于种下葵花
在原本空旷虚无的田野里
如同执迷于做游戏的孩子。
除了葵花,我的眼睛里
看不见他物,这是为什么?
它们已深深地低下头来,
洒落花盘上虚浮的金黄颜料,
不再动摇。
它们已经记住了停下来的刻度
已完成肉身的信仰
我磨快镰刀,总是感动于它们
头颅尽失前的时刻,像是看到
有人摇晃着巨大的转经筒。
像是就要发生的
复杂的晚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