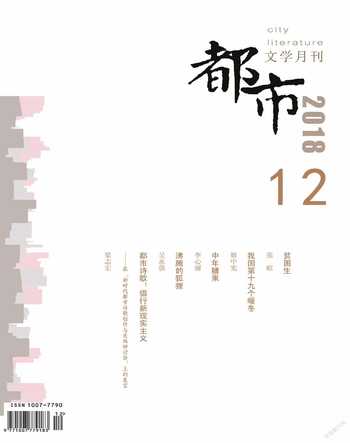坚持独立的诗歌写作
张红兵
近来,诗坛的“曹伊”之争甚嚣尘上,其中矛盾的焦点就是曹谁对伊沙诗歌的贬损,“伊沙是垃圾中的垃圾”,(这句话有语病,应该是,伊沙的诗是垃圾中的垃圾)当然这句话还有个前提,“中国新诗99%是垃圾”。曹谁的这句断语,不知道大家听后有什么感受,反正我是感到了一身的不爽,心想,我们的这位小老乡可真够狂妄,他打击了中国99%的诗歌写作者,(99%还不对,曹谁后来还将它修正为99.9%,打击面就更大了)让那些本来对自己的写作缺少自信的人更加失掉了自信。但我们的这位小老乡又有足够的智慧,他说99%,又没有点明,谁是这99%,谁是那1%,,它又让那些对自己的诗歌充满自信心的人,更加有了自信。其实,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些无聊。觉得我有点儿死脑筋,曹谁是谁?值得我如此劳神?慢不说就是年轻人玩“抖音”,即便是严肃认真的场合,那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完全不必放在心上。不过话既然说出来了,居然还有人接招,还有人帮腔。它至少说明,诗歌仍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话题。
这是题外话,但也是我打开今天话题的一个由头。我写诗二十年,一只处于不求甚解的状态。面对曹谁的99%论断,不管你是99%,还是1%。都有必要给自己降降温,清醒一下。看看诗坛,在反观一下自己,这或许是有益的。
我在诗歌写作中不提倡什么主义,也从来不去投靠山头,这是独立写作的前提。那么要保证诗歌写作的独立性,就要认清那些帮派诗歌的真面目,主动和他们划清界限,让自己在足够独立的空间里不断成长起来。
当前的诗歌写作有几种倾向必须引起注意,一种就是那种似是而非的诗,这类诗歌故弄玄虚,神神叨叨,姑且叫它晦涩派;第二种写法可以叫意象派,这种写法死守着那些所谓的意象不放,不敢越雷池半步,陈词滥调,不厌其烦;还有一种是民间写作,也就是曹谁所说的垃圾诗。这三种写法加在一起或许就是曹谁的那99%,也未可知。
那么,晦涩派诗歌到底是怎样一种面目呢?关于它的论断已经很多,而且许多诗人仍然在大行其道。说到底,这是一种油滑的、老练的、有策略的诗歌,它不仅未能让诗歌的独立性写作成为可能,反而成為诗歌独立写作的敌人。在晦涩派看来,诗歌的放弃独立恰恰是他们在为自己寻求独立。从本质上看,他们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因为世俗利益保证了他们的诗歌安适。已经不再顾及独立是诗歌的摇篮,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他们甚至认为诗的独立影响了他们正在享有的“独立”。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价值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当然会有着现实的利益关怀。已经认为诗歌无法承担什么独立,仅仅是一种语词的逻辑而已,至多是一种自言自语的抒情。有的只是对修辞的体贴、理解和矫情,甚至达到一种自我审美判断。其实,恰恰相反,他们思维和行动都罩在了主体性被异化的、独立精神被熄灭的牢笼之中。
如果说诗歌的晦涩派倡导了一种自由乌托邦的话,意象派就是在构筑诗的审美化倾向和宗教化虚幻。按意象派诗人的理由,诗歌只能以美的意蕴反映世界,诗歌秩序不再是批判理性,仅是一种美的感受。在他们看来,诗歌不再需要揭示人生的伤痛,也不需要对荒诞的世界进行提醒,甚至对世俗世界的本质性纷争也可以视而不见。他们认为唯美才是诗歌的正道。因此,意象派写作不仅宣布了自己的道德神话,还宣布了自己的正义立场。所以,在当下所谓的权威诗歌媒介中有大量的此类伪道德诗歌充斥就见怪不怪了。还有一类意象派写作者鼓吹诗歌的宗教化倾向。其实我们都知道,诗歌无法代替宗教,因为宗教不关心世俗利益,它只关怀彼岸世界,而诗歌是诗人与周围世界建立的一种隐秘联系的特殊呈现,除了尽情发挥生命的内蕴外,还要承担精神的独立。意象派写作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把“明天”看成了目的。殊不知,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过程,任何为了遥远的目的而牺牲过程的行为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而相对于晦涩派和意象派而言,“民间写作”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们想触摸当下的世界,但是由于理性的缺失,所以总是不得要领。“民间写作”将所有的传统全部解构和碎片化,结果是在这种诗歌里我们看到的只有从现实的场景偷取的符号,而没有任何独立可言。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反对意象派的虚假和晦涩派的麻木而进行有益尝试,然而,他们的写作只是对个人欲望的肯定和满足。完全沉溺于世俗场景的结果是并未对这些世俗场景构成抗争。比如“垃圾派口语诗人”,他们为了实现诗歌写作的目的,不仅拒绝了来自诗歌内部关于诗人对人格独立的要求,还回避了内在的生命深度,于是,大量复制产生的便是失去了生命温度的分行文字。再比如,近年来流行的“诗歌地理学写作”,因为跟风和泛滥,已经沦落到只有地理而没有诗歌的地步。写作只是为了罗列,不再是生命自身的表达,已经完全失掉了诗歌应有的灵魂力量。
当下诗歌中独立精神的丧失其实是一种诗人的自身丧失。不论是晦涩派诗人、意向派诗人还是所谓的“民间写作”者、诗人,一旦失去了自身,也便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能力和机会,也便失去了写作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主张诗歌写作的独立性。当然,诗歌写作的独立性也并不是要让诗歌全部承担所有的时代使命,也不是回到简单的政治诉求、道德欲望和宗教代理。而是说诗人必须要认识和参与时代并用诗歌来表达这种认识和参与,必须是抛弃功利主义的现实欲求,写作的目的是唤醒而不是占有。
坚持诗歌写作的独立,必须建立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不依附、不跟风。我手写我心,要写真实之诗、真诚之诗、真切之诗,正如我们行走在暗夜里,既要有手中的灯盏,还需要理想在远方召唤。如此,我们才能信心十足地走下去,这或许才是诗歌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