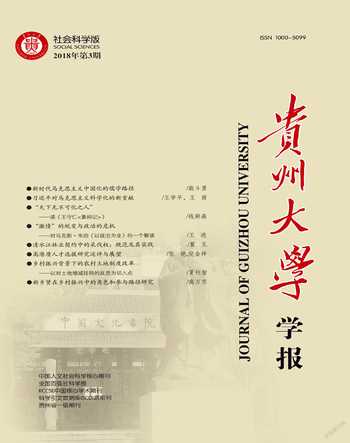同情、骄傲与社会性
苏光恩
摘 要:曼德维尔的道德体系在《道德情操论》中遭到了斯密的严厉批判,但斯密的这一批判很难说是真正成功的,他的“同情”并没有与曼德维尔的“骄傲”真正拉开距离,他的道德学说仍然带来鲜明的曼德维尔的印记。但他们在社会的自然性还是人为性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在曼德维尔那里,道德的产生、人之社会化离不开“政治家”的努力,他致力于探询的是一系列驯化激情的政治技艺;而斯密的道德心理学则没有了“政治家”的位置,他试图揭示的是道德的自然生成机制,在斯密那里,社会成了自然的一部分。
关键词:同情;骄傲;社会性;斯密;曼德维尔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3-0035-08
Abstract:Adam Smith's Criticizing severely on the moral system of Mandeville in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was not adequately successful, because his Sympathy was not greatly different from Mandeville's Pride, and his moral theory wa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Mandeville's. However, they we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 artificiality or nature of society: Mandeville upheld that the origin of morality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human beings could not be achieved without politician's efforts, and he endeavored to explore political skills in taming passions; but Smith left no space for politicians and tried to reveal the natural formulation system of morality, classifying society as part of nature.
Key words:sympathy; pride; sociality; Smith; Mandeville
伯納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作为18世纪思想史当中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在思想史中的位置很长时间里与亚当·斯密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蜜蜂的寓言》当中所宣扬的“私人的恶行,公众的利益”常被视为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一种预先表达,曼德维尔由此被界定为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先驱,换句话说,他成了一名斯密之前的斯密主义者。①
不过随着对斯密研究的深入,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对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日渐重视和深度发掘,曼德维尔开始更多地作为斯密的对立面出现,因为在《道德情操论》中,曼德维尔的“放荡不羁的体系”遭到了斯密的严厉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曼德维尔与斯密之关系的历史本身便构成了斯密研究史的一个侧面,不过斯密研究的这种《道德情操论》转向的直接后果便是曼德维尔的重要性遭到了贬低。这不仅在于曼德维尔的体系为斯密所明确拒斥,而且在一些研究者那里,曼德维尔也只是属于为斯密所拒斥的霍布斯传统(即把我们的一切道德感皆归于自爱)中的其中一员。[1]80
然而视曼德维尔为一名霍布斯主义者,并没有解释斯密为何要专辟一章讨论曼德维尔所代表的“放荡不羁的体系”,而曼德维尔作为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先驱与遭斯密最严厉拒斥的哲学体系的代表这两种形象之间的矛盾也并未得到解决。因此,重新考察斯密对曼德维尔的批判,有助于我们廓清曼德维尔与斯密之间的关系,确认斯密在哪些地方深受曼德维尔影响,又在哪些地方与曼德维尔分道扬镳,而这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18世纪的论争和斯密的贡献显然是有帮助的。
一、怜悯与自爱
我们先从斯密对自爱论传统的批判开始,一般认为,霍布斯、普芬道夫和曼德维尔均属于这一传统,而斯密的同情理论则以拒斥这一传统为己任。“同情”(sympathy)无疑是斯密道德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作为哈奇森道德情感主义的继承者,斯密试图跟其导师一样,呈现道德的自然之源,而这一自然的根据在他那里,便是人天生赋有的对他人的同情。不过尽管我们可以用同情理论来形容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但他的“同情”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狭义的同情,即我们对他人情感的同感(fellow ̄feeling),这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自然的能力;但单纯的对他人情感的同感不足以构成我们的道德情感或道德判断,我们还需要借助第二个层次,即合宜性(propriety),行为者与旁观者双方通过相互间的同情,调整各自情感的强度,以达到情感的一致性。正是这种合宜性构成了道德判断的依据,而个体的道德意识便产生自与其他个体或社会之间的这种持续性的互动。因此,要评价斯密对自爱学说的拒斥是否充分,我们必须对这两个层次分别予以考察。
第一层次的同情,即对他人情感的同感无疑是从怜悯(pity)演变而来,只不过斯密将对他人不幸遭遇的感同身受扩展为对他人“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2]I.i.1.1-5。对那些试图将一切激情皆归结为自爱的思想家来说,如何看待怜悯始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因为在直观上,怜悯是对他人不幸遭遇的同感,这似乎很难称之为自爱。事实上曼德维尔便承认,“在我们的所有弱点当中,怜悯是最友善,也与美德最为相似的”[3]I.56。对于这一问题,霍布斯的回答是,我们的怜悯是由“想象类似的苦难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而引起”,当我们对他人施以怜悯时,所关心的仍然是我们自己,所以“那些认为自己最少可能遭受这种灾难的人,对之也最少怜悯”。[4]42
《道德情操论》开篇第一句话便表明了斯密对这一自爱观的抗拒:“不管人被认为有多么自私,在其天性当中始终明显存在着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把他们的幸福当做自己的事情,尽管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原则便是怜悯或同情”[2]I.i.1.1。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曼德维尔,他们显然都不否认存在怜悯这样一种激情,因此斯密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人是的有怜悯心的,而是证明,在人对他人的同情或怜悯当中,他真切关心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斯密的观点是,同情作为一种感同身受,我们是将自己放在了他人的位置上,我们所同情的是被同情者的处境,而不是我们自己[2]VII.iii.1.4。白发人送黑发人总是令人心碎,但我们对那位老人的同情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象着这样的不幸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而是我们想象着自己如果是这位老人会承受何等痛苦,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是他。同情不仅仅是情境的交换,也是角色的交换[2]VII.iii.1.4。所以斯密说,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对一件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产生同情,比如一个男人对分娩中的女人的同情。
当然,因为男人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分娩的痛苦,他的同情显然要弱于有过分娩经验的女人。不过按斯密的说法,这是因为他并没有“well ̄informed”,而同情的强度与是否对境况充分了解密不可分,这一点我将在下一节再谈。在这一点上,斯密对同情机制的揭示比自爱论传统的解释要精细得多,而且他也似乎颇为可信地证明了同情或怜悯并不是自爱。
不过格里斯沃尔德认为,在对亡者的同情这一极端情形当中,同情似乎是自私的,参见Charles L. Griswold Jr.: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89。
但斯密对霍布斯怜悯观的拒斥并不等同于他拒斥了曼德维尔的怜悯观,在怜悯问题上,曼德维尔的解释要复杂得多。曼德维尔并没有像霍布斯那样,认为我们对他人的怜悯是由“想象类似的苦难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而引起”,相反,作为“对他人不幸或灾难的感同身受和慰问”,怜悯似乎是对他人真切的关心[3]I. 254。曼德维尔所否认的是怜悯是一种美德,因为按照他对美德的定义,唯有出于为善的目的和理性的抱负而对激情施以自我克制的行为才堪称美德,而怜悯作为一种自然的冲动,它既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譬如对一位法官来说,对罪犯的怜悯显然会毁掉他的公正[3]I. 56。
不过在曼德维尔这里,怜悯确实包含了自爱的因素,这是因为目睹他人的不幸却没有加以阻止,这会让我们产生痛苦或不适(uneasy),所以自我保存之心(self ̄preservation)驱使我们去避免这种不幸的发生;而当我们想到自己对宽慰被同情者,缓解他的悲伤有所帮助时,这会让我们如释重负[3]I. 56, 254-255, 258。简而言之,怜悯之为自爱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人的怜悯实为自怜,而是我们之所以怜悯他人是为了克服因他人痛苦而帶给我们的不适。如果这一点是对的话,那么斯密对自爱论的上述批判并不构成对曼德维尔的真正反驳。斯密毫无疑问也同意,目睹他人的不幸会让我们自己感到痛苦。当斯密举例说一个体质孱弱的人因见到乞丐暴露的脓疮而感到不适时,这跟曼德维尔说乞丐通过展示其身体的疾病和虚弱来唤起你的怜悯如出一辙[2]I.i.1.3。在有关怜悯或同情的看法上,斯密事实上与曼德维尔有着不少一致之处,比如曼德维尔同样认为,同情的强度与距离的远近密不可分[3]I. 254-255,而这一点恰恰构成了斯密同情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
有关斯密道德哲学中同情与距离的关系,Fonna作了十分深入的阐述,参见Fonna Forman ̄Barzilai: Adam Smith and the Circles of Sympat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不过在斯密那里,由于“同情”已由原初的“对他人悲伤的同感”扩展为“对任何激情的同感”,它是一种传递激情或情感的机制,而非一种激情。
这似乎也意味着“怜悯”在斯密这里已不再是一种激情。作为对他人情感的共鸣或传递,斯密的同情强调的是fellow ̄feeling;而曼德维尔的怜悯除了这种fellow ̄feeling(目睹他人不幸所引起的痛苦和不适)之外,还包含了为避免此种不适而采取的行为(action)。前者与斯密的狭义的同情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而斯密也并没有辩明,因此种感同身受而引发的行为不是自爱。
二、对一致性的渴望与骄傲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曼德维尔的指名道姓的批判是,曼德维尔将“任何出于某种合宜感、出于对何为值得表扬和值得称赞的考虑而做出来的行为”,都视为源于对称赞的热爱,或曰虚荣(vanity)。一切公共精神和人类美德皆不过是“逢迎骄傲的产物”(offspring of flattery begot upon pride),从而对美德和荣誉的热爱这两种“人类最高尚和最伟大的激情”与虚荣这种“人类最浅薄和最低级的激情”在曼德维尔这里被完全混为一谈[2]III.2.27, VII.ii.4.7-10。这一批判所涉及的正是斯密的同情的第二个层次,即合宜性问题。在斯密那里,同情之所以构成道德情感或道德判断的来源,是因为同情是相互的,由于行为者的情感与旁观者的同情之间在强度上总是存在着不一致,这种事实上的不一致,和对一致性的渴望,会驱使双方都调整各自的情感强度。而这种调整,这种借助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便在很大程度上克制了我们的自爱之心,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重要。换句话说,斯密试图证明,他的同情学说在两个层次上都克服了自爱,我们不仅会真切地同情他人的处境,而且会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审视自己。
不过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寻求一致性的背后动力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将我们从自爱当中拽离出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曼德维尔与斯密在明面上的核心分歧。在曼德维尔看来,这一动力便是骄傲(pride)或自尊(self ̄liking)
在《蜜蜂的寓言》第1卷中,“骄傲”尚属于“自爱”(self ̄love)之一种,到了第2卷,曼德维尔明确区分了“自爱”与“自尊”(self ̄liking),自爱被等同于自我保存(self ̄preservation),而自尊便是对自我的高估,即为骄傲。在《论荣誉之起源》中,曼德维尔对自尊与骄傲之关系作了进一步修正,他称自尊过度时的表现为骄傲。self ̄love与self ̄liking与后来卢梭所区分的amour de soi与amour ̄propre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对自我的高估。这是人身上最为强烈也最为根深蒂固的激情,它使人陶醉于他人的赞扬,而惧怕他人的蔑视。曼德维尔同意美德是对人自身激情的自我克制,但这种自我克制必须借助于另外一种激情,而在所有激情当中最能让人做到这一点的便是骄傲,所以他才说一切美德皆为逢迎骄傲的产物[3]I. 51。这样一种主张无疑是斯密要抗拒的,在他看来,将美德归结为骄傲实际上完全抹消了美德与恶习之间的区别[2]VII.ii.4.6。但斯密的这一指控显然有些夸张,尽管曼德维尔试图揭示美德的幽暗根源,但他并没有否认美德的真实性,因为美德要求真实的自我克制(self ̄denial)。因此当斯密指责曼德维尔将对美德和荣誉的热爱与虚荣这种“人类最浅薄和最低级的激情”混为一谈时,他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曼德维尔的本意,事实上在曼德维尔看来,只有“孩子和蠢蛋才会囫囵吞下所有的个人赞美”[3]I. 52。
为驳斥曼德维尔,斯密区分了对赞扬的喜爱和对值得赞扬的喜爱,后者乃是希望成为“自然而又合宜的热爱对象”,害怕成为“自然而又合宜的憎恨对象”。在斯密看来,尽管对赞扬的喜爱和对值得赞扬的喜爱互有联系且常常混为一体,但“对值得赞扬的喜爱并不完全来自对赞扬的喜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赞扬的喜爱似乎是来自对值得赞扬的喜爱”[2]III.ii.1-3。曼德维尔的问题显然在于将本应归于对值得赞扬的行为的喜爱也归结于对赞扬的喜爱,或曰虚荣心[2]III.ii.27。然而斯密的这一区分很难说真正驳倒了曼德维尔,因为根据这种情感主义的进路,我们仍然可以追问,我们为什么渴望成为值得赞扬的对象?斯密在对曼德维尔美德观的转译过程中,事实上将骄傲与虚荣作了完全的等同。在曼德维尔那里,骄傲从根本上说是人对自身的良好评价,而对他人赞扬的喜爱则仅仅是骄傲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由于对自身良好评价的不自信才需要他人的赞扬作为确证。因此,在曼德维尔看来,完全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仅仅“出于对自己的评价,……便能默默地做出值得称道的举动”,而这些举动得不到任何的赞赏。这一类人相较其他人而言无疑“通晓一种更高尚的美德观”,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当他们在思考自身的价值时,会怀有一种愉悦感,而这种愉悦感显然便是骄傲的确切标记[3]I. 57。当斯密说“虽然我们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赞同,但是想到自己已成为自然的赞同对象,还是感到愉快”时,我们看不出它与曼德维尔所说的“通晓一种更高尚的美德观”的那類人的心理有何实质的区别[2]III.ii.3-5。
斯密引入“对值得赞扬的喜爱”,无疑是想为道德行为的动因赋予一种客观性,是想说明在每一个道德情境中,我们都拥有一个恰当的尺度,尽管每一个道德评判都视具体情境而定,难以抽象和普遍化。由于在斯密那里,道德产生于行为者与旁观者之间持续的互动,因此,构成“何为值得赞扬”的评判者的便是社会本身,也即《道德情操论》中著名的“无偏私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强调“无偏私”,显然是为说明,并非所有的旁观者皆为合宜的旁观者,唯有与行为者利益无涉,不存偏私之心的人才有可能做出公正的判断。而我们在评判自己的情感或行为时,则会借助一位想象出来的“无偏私的旁观者”的眼光,唯有这位“内心的居民”有可能抵消我们最为强烈的自爱的冲动[2]III.3.5。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这位“想象中的无偏私旁观者”,我们才得以避免对赞扬的喜爱与对值得赞扬的喜爱的混同。[5]84但斯密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因为根据他对同情的分析,我们知道,判断公正与否除了旁观者必须无偏私以外,还必须对行为者的行为背景有充足的了解(well ̄informed),唯其如此,旁观者的同情才可能是充分的。然而问题的悖谬之处恰恰在于,唯有利益相关、关系密切者才有可能、也有意愿拥有关于行为者处境的充足知识;距离越远,越是利益无涉,我们的同情也便越为微弱。[6]71这也意味着,内心的那位“无偏私旁观者”所给予我们的同情显然要多过社会中实际的无偏私旁观者,这两者的判断之间必然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因为外在于我们的陌生人并无那样的热情和能力对我们的境况作充分的了解。因此,尽管想象出的这位无偏私旁观者能够让我们站在一定距离之外看待我们自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我们的自爱之心,但是他显然使我们有可能对自己做出比外人所能给予的更高的评价。而在曼德维尔那里,所谓骄傲指的便是我们对自己的高估。同情的机制并没有能力真正克服这种骄傲。
三、曼德维尔的“老练政治家的巧妙管理”
斯密的同情在克服骄傲上的失败似乎可以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便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仍然是一位隐匿的曼德维尔的追随者,他的同情机制不过是一种更为精致的自爱体系,由此,曼德维尔的两种形象之间的裂隙似乎得到了重新弥合。[7]32, 37; [8]219-233 但这样一种解释显然过于贬低了斯密的理论自觉,因为从斯密自身的抱负上来说,他恰恰是试图将道德从自爱体系中解救出来,尽管他的这一努力未必是成功的。不过不管道德的基础究竟是同情还是骄傲,也不管这两者之间是否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对斯密和曼德维尔二人的道德学说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毋宁在于,我们的道德感是如何形成的。他们都否认人具有自然的道德能力,无论这种能力是理性还是道德感官,相反,它是社会的产物。但在如何解释道德的社会性上,两人事实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而这一分歧恰恰构成了曼德维尔与斯密二人思想的核心区别。
在曼德维尔那里,虽然骄傲是一个人做出合乎美德的行为的根本动力,但仅凭骄傲本身并不足以形成美德,相反,美德是一项“政治的发明”,它源于“政治家”对人之骄傲之心的巧妙利用。在“论美德之起源”这篇文章当中,曼德维尔称,“政治家们”出于治理的方便,将人的行为分成了两类,将那种“出于某种为善的理性抱负而致力于惠益他人,或战胜自己的激情的行为”称为美德,而称那些只管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公共利益的行为为恶习[3]I. 48-49。据此他们将人也分为两类,践行美德者是高尚的,沉溺恶习者则是卑贱的。由于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他人的赞扬而害怕遭到他人的蔑视,美德便成了人们效仿的榜样。正是在这意义上,曼德维尔宣称“美德乃是逢迎骄傲的政治产物”(the Moral Virtues are the Political Offspring which Flattery begot upon Pride)[3]I. 51。
如何理解曼德维尔所谓的“政治家”,恐怕是曼德维尔研究当中的最大争议所在,因为它与我们通常赋予曼德维尔的自由放任或自生自发秩序思想先驱的形象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个常见的做法是称它为曼德维尔早期尚未克服的思想不成熟,持此论者常引曼德维尔的最后一部著作《论荣誉之起源》中的一段话作为佐证:
“我不加区别地用它们(即“道德家”和“政治家”)来称呼所有那些对 人性做过研究,或是为了统治者和官员的便利,或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的俗世幸福的目的,而致力于将人们文明化,变得越来越驯顺的人。……我把所有这一类的发明都看作是许多人共同的劳动成果。人类的智慧乃时间的产物。”[9]40-41
而《蜜蜂的寓言》第2卷中所表达的演进论更被认为是曼德维尔与第1卷中的理性主义立场的明显决裂。[3]I. cxxxiv-cxxxv, pp. cxl-cxli; [10]579-580但早在《蜜蜂的寓言》之前,曼德维尔在为《女闲谈报》(The Female Tatler)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就已经明确表露了演进立场:“(所有的科学与技艺)均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才臻至完善,而它们最初的萌芽也大多渺小得连它们的作者均不值一提”。[11]100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说曼德维尔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前后不一。曼德维尔在“论美德之起源”中对美德产生过程的勾勒,并不是要说明这是真确的历史,而是对美德如何驯化人之激情的一种抽象的演绎,它意在揭示美德的人为性。
终曼德维尔一生的著述,他始终关心的是人之社会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人这种极其自私、“本性上似乎最不适于社会的动物”,如何却成了“唯一具有社会性的动物”。[11]96这一关切本身表明了曼德维尔对霍布斯以来的这一论题的继承。和霍布斯一样,曼德维尔也认为人是受激情驱使的动物,而这些激情又都是自我中心的。因为这样一种人性特征,所以无论在霍布斯还是在曼德维尔那里,人都不是自然的社会动物。所以社会在他们那里与激情不受约束的自然状态是对立的,它是对激情的规制和约束。不过与霍布斯相比,曼德维尔赋予了人更多的可社会性(sociableness),虽然在自然状态之下,人是最不适于社会的,但一旦社会形成,却没有什么动物比人更适于社会,因为人在社会当中获得的舒适与安逸要远远胜过自然状态下的穷困无助[3]II. 180。但这种可社会性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形成是自然的,相反,它是政治技藝的产物。曼德维尔关于葡萄酿酒的比喻十分形象地表达了他的社会观:适于酿酒无疑是葡萄的本性(nature),但葡萄酒却是人类的发明。自然所提供给我们的仅仅是各种材料,“发现它们的用途并加以利用的,正是人的聪明才智”[3]II. 185-186, 188。
在曼德维尔那里,社会的演进与社会的人为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矛盾,变化和发展恰恰是人为之物的特征,而自然之物则是永恒的、不可变更的[3]II. 186-187。而曼德维尔对政治技艺的演进特质的承认也并不等同于他否认政治家在人的社会化和文明化过程中扮演的主导性角色,事实上《论荣誉之起源》本身便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路易十四、罗马天主教和克伦威尔的高明的政治手腕。在曼德维尔那里,一位理想的政治家好比一位调酒师,他能够从各种卑劣的人类品性中调配出于社会有益的味道来[3]I. 105。曼德维尔也正是在这意义上说从“私人的恶行”到“公众的利益”有赖于“老练政治家的巧妙管理”。所以与霍布斯视骄傲为无序的重要根源,从而关心如何借助一位至高的主权者来使人摆脱这一可悲境地不同的是,曼德维尔则视骄傲为于社会最为有用的激情,他更乐于呈现的是一系列引导和利用骄傲来驯化其余激情的政治技艺。美德、文雅和荣誉在曼德维尔那里皆属于这样的政治技艺,它们都源于对骄傲的不同利用。对曼德维尔而言,重要的不是事实上谁发明了美德或文雅,而是这些伦理原则背后的心理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四、斯密的自然社会
休谟的正义理论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曼德维尔那里道德的人为性。对于任何志在解释社会的自然性的人来说,他都必须回答正义的起源——即政府与法律的起源——问题。事实上曼德维尔批驳沙夫茨伯里的理由也正在于,如果社会的基础源于人们对同类所怀有的自然的情感,那么不仅社会的繁荣将不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本身也将变得毫无必要的了,因为政府从本质上来说便是对人之自然的激情施以约束,使之成为驯顺的动物[3]I. 323-325, 347。这一困难在休谟那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因为在处理正义(即政府和法律)的起源问题上,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正义并非人之自然的情感,而是对人性弱点的矫治,“我们的自然的、未受教化的道德观念,不但不能给我们的感情的偏私提供一种补救,反而投合于那种偏私,而给予它以一种附加的力量和影响。因此,补救的方法不是由自然得来,而是由人为措施得来的”。[12]529
哈孔森据此称休谟的人为正义观是其道德理论中的一个赘生物,见努德·哈孔森:《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赵立岩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休谟的这种人为正义观显然与曼德维尔思想是一致的,所区别的只是休谟反对将一切道德皆归之于人为的发明,在他看来,人身上还存在一些自然的美德,比如柔顺、慈善、博爱、仁厚、温和、公道等。[12]620 “某些哲学家”的错误正在于,他们“认为所有的道德区别都是人为和教育的结果,是由于老练的政治家(skilful politicians)通过荣辱的概念来努力约束人类狂暴的激情,使它们促进公共利益”。[12]621一般的研究者常认为这段引文所指向的是霍布斯,但一个略熟悉曼德维尔文本的人定会清楚,它是对“论美德之起源”一文主旨的准确概括,而“老练的政治家”显然是指向曼德维尔的确切标记。
所以不难想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休谟的批判,主要针对的便是后者的正义理论,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暴露了休谟道德哲学的不彻底性,而斯密的抱负显然是要为社会真正奠定自然的基础。斯密否认正义源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理性考量(从而是人为的),相反,它源于我们对受害者的愤怒的即刻的同情(从而是自然的)[2]II.ii.3.9-10。也就是说,即便正义这种通常被视为人为之物的美德也是同情机制的产物,旁观者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行为者的愤怒构成了我们对何为正义与不正义的感受,这种正义感先于法律的创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法律不过是对我们已然怀有的正义情感的顺应。不是立法者通过创制法律来约束人的自然的激情,相反,法律本身便是我们情感的自然结果。虽然斯密在转述曼德维尔的美德观——即人类的美德不过是“逢迎骄傲的产物”——时,隐去了“政治”一词,但他显然十分清楚曼德维尔那里美德的人为性,因为他称这种美德产生方式为“对人类的欺诈和哄骗”[2]VII.ii.4.8。斯密的确谈到在教育上对虚荣的利用[2] VI.iii.46,但他并不以探询这种驯化激情的技艺为己任,在斯密的道德心理学中,这种“欺诈和哄骗”并不是通则。
虽然在确立社会的自然性上,斯密自觉地继承了哈奇森的传统,但斯密与哈奇森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他否认在人身上存在着自然的道德感官,人的道德感是从社会中得来的,唯有借助社会这面镜子,一个人才能明了自己的情感是否合宜,才会习得孰是孰非[2]III.i.3-5。但斯密又没有陷入霍布斯、曼德维尔的人为社会观,毋宁说斯密学说真正的创见正在于,他打破了原有的自然与人为的二元对立。他试图说明,道德是在社会中生成的,但同时它仍然是自然的。在这一理解之下,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社会成了自然的一部分。休谟仍然模棱两可地为“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留有了位置,因为他还需要借助这样一个虚构的自然状态来观察哪些措施是对人之自然弱点的矫治。[12]533 而斯密则是从真正意义上抛弃了“The state of nature”的概念,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一個前社会的开端,从而需要一个力量来完成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的跃变,相反,人从一开始便是处于社会之中的。所以斯密从根本上取消了对道德起源问题的考量,而对某一伦理原则之起源的考察恰恰构成了曼德维尔持久性的关切。
按《论荣誉之起源》开篇所言,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第1、第2卷和《论荣誉之起源》中分别讨论了美德的起源、文雅的起源和荣誉的起源。见Bernard Mandeville: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Honour, and the Usefulness of Christianity in War. London, 1732, p.1。所以斯密在其《法理学讲义》中勾勒的文明四阶段的第一阶段渔猎社会绝不能被视为自然状态,而从渔猎社会向游牧社会、农业社会直至商业社会的演进也不过是人们顺应其处境的自然过程,文明社会的历史由此成了一部“人类的自然史”。[13]14-16
这种历史中生成的自然性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斯密究竟是不是一个习俗主义者。斯密毫无疑问同意,道德是社会的产物,它会因时因地而异,但斯密否认这种变化是任意的,它仍有其客观的尺度,而这一尺度便是他所谓的“合宜性”。在斯密那里,道德判断是情境性的,我们唯有将某一行为放到其具体情境之下,我们才能判断其是否合宜。情境千差万别,我们的道德判断也便随之而异,但缺少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从进行道德评判。在斯密那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职业、社会阶层,也会塑造出不同的性格和道德品行[2]V.2.4-6。但在每一个民族、每一种职业和每一个社会阶层当中,都存在着与该民族、职业或阶层相称的行为方式。习俗与风尚的差异并没有取消自然作为尺度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情境的合宜性使我们既能够对异文化进行道德评判,也能够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审视我们自身的社会。我们可以斯密对弃婴行为的讨论为例,他毫无疑问认为这种习俗是极其野蛮的,但“在最原始和最低级的社会”,因为野蛮人的极端贫困,他常常难以同时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命,所以这样的行为较能够得到原谅;而在富有教养和文明的希腊社会晚期,极端贫困的条件不复存在,再容许这样的行为便是不可原谅的[2]V.2.15。
所以在斯密这里,尽管传统的自然与人为(或习俗)之间的对立被打破,但自然并没有丧失其原有的重要性,相反,“自然”是斯密著作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
有关斯密的“自然”观,参见Charles L. Griswold Jr.: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p.311-329;吴红列:“亚当·斯密的自然观——对《道德情操论》中nature的解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8-26页。本文不打算对斯密著述中“自然”的意涵做一一探讨,仅就与“人为”相对这一层意思而言,自然与人为之分并没有彻底失去其有效性,只不过改换成了另一种形式。我们需要辨认,哪些做法是自然的,哪些做法是不自然的(unnatural),而这种不自然便是我们对事物自然进程的不当干预或扭曲。斯密彻底抛弃了“The state of nature”的概念,但在他那里又出现了另一种“自然状态”,即“Natural state”。譬如“与幸运能够将人的心绪拔高到超过其自然状态(Natural state)相比,厄运必然使其承受者的心绪消沉到远远低于其自然状态”[2]I.iii.1.5;又如“只在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处在普通状态,即所谓自然状态下时,这些用途的所有利害才会有这样的均等”。[14]I.108尽管“Natural state”也指事物依其本性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但它已不再有与社会相对的意涵,它是社会中依然存在的一种状态。如今重要的不是通过人为的努力来使人摆脱“The state of nature”,而是避免用人为的干预来扭曲事物的“Natural state”。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自然观,斯密导向了一种要求节制政府权力的政治学说,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道德领域,它都应避免造成对自然的背离。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不重要了,如我们前面所见,政府的必要性本身便是自然的产物。恰恰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自然与不自然之分,所以理解并顺应这种社会中的自然便变得尤为重要。但无论如何,斯密的“政治家”或“立法者”所应扮演的角色显然要弱于曼德维尔。在曼德维尔那里,“政治家”是十分积极主动的,他应当是社会的塑造者,应当能够将“私人的恶习”转变成“公众的利益”;而斯密的“政治家”或“立法者”所担当的更多是消极的角色,他确实也需要了解自然,但其目的不是要驾驭自然,而是遵从自然。尽管在斯密这里,我们尚未见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明确分离,但我们已经能够预见这种分离的到来,对斯密而言,不是国家创制了社会,而是社会塑造了国家。
五、结语
通过对斯密的曼德维尔批判进行再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道德情操论》中,曼德维尔仍然对斯密有着深远的影响,斯密并没有真正将他的“同情”与曼德维尔的“骄傲”区分开来。但这不足以使我们得出结论说,斯密是一位隐匿的曼德维尔的追随者。与我们惯常持有的曼德维尔是斯密自由放任思想先驱这一印象恰好相反,他们在社会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上有着根本性的分歧,曼德维尔仍然为“政治家”保留了更多的位置,而斯密则试图提供以社会的自然性来约制政治的力量。本文无意于判断这两种立场当中哪一者更为高明,但毫无疑问,它们之间的纷争仍在塑造着我们今天的生活。
參考文献:
[1]CHARLES L, GRISWOLD J R.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ADAM S.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M]. Liberty Fund, 1982.
[3]BERNARD M.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M]. Liberty Fund, 1989.
[4]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莫斯纳,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M].林国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FONNA F B. Adam Smith and the Circles of Sympath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7]ISTVAN H. 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 Jean ̄Jacques Rousseau and Adam Smith[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8]BERT K. A Fatal Attraction? Smiths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nd Mandevilles Fable[J].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995 (2).
[9]BERNARD M.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Honour, and the Usefulness of Christianity in War[M]. London, 1732.
[10]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1]BERNARD M. By a Society of Ladies: Essays in The Female Tatler(1709——1710)[M]. Edited by M. M. Goldsmith. Thoemmes Press, 1999.
[12]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3]ADAM S. Lectures on Judisprudence[M]. Liberty Fund, 1982.
[1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