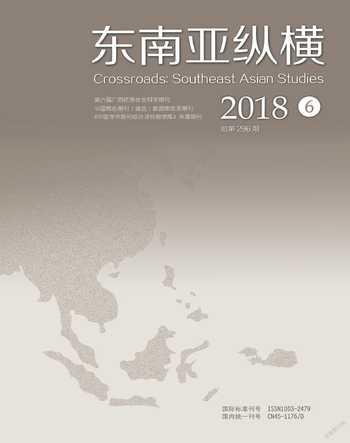加强东亚共同体社会—文化支柱建设
赵力涛 陈红升
摘要:本文提出从三个方面加强东亚共同体社会文化支柱的建设,即更为深入地理解社会文化支柱,超越功利主义的目的和考量,对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全面建设应采取更加务实的手段;更为注重相关各方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愿望,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以成为相关各方加强合作及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良好平台;智库和学术机构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扩大智库参与范围和目标范围,共同致力于东亚共同体的建成。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社会文化支柱;共同体建设
[中图分类号] D8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8)06-0011-04
近40年来,东盟内部合作以及东亚与东南亚区域伙伴关系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势头有所加强,从合作转向共同体建设,重点从经贸关系扩大到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关系。
建设东亚共同体需要“东盟+3”各国向前看,着眼长远并坚守承诺。对这些国家来说,政治价值观与经济发展差异巨大是一大挑战,意味着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培养共同感,促进人文交流由此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文化支柱,经济和政治支柱本身是不会产生强大的地区认同感和共同归属感的。
一、要更深入地理解社会—文化支柱
把社会—文化当作东亚共同体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一大进步。然而,目前对于社会—文化支柱的看法主要还是功利主义的。这种偏见在《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Master Plan on Connectivity 2025)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规划旨在通过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熟练工人的跨境流动以及增加留学生数量等方式加强社会—文化支柱的建设①。
中国与东盟在社会文化领域保持着一致的基调,这也解释了为何2016年被确定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年、2017年被确定为中国—东盟旅游年。双方互访游客人数不断增加,并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不断扩大的有力证据。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提到,2016年“中国赴东盟游客为1980万人次,增长了6.4%,而东盟赴中国的游客为1034万人次,显著增长了57.8%”。他还着重指出,“人文交流有助于增进对东盟与中国多元文化和历史经验的相互了解和鉴赏”②。同样地,2018年7月12日,在中国—东盟建立战略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招待会上,中国驻东盟大使黄溪连说道:“东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已经从2003年的387万人次增加到2018年的5000万人次,互派留学生总数超过20万人。”③
虽然游客和留学生数量反映了人文交流的某些方面,但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文化方面与旅游业发展及留学生人数的增加完全等同起来的做法是有严重缺陷的。仅仅关注跨境旅游和留学生的流动在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中国与东盟“消费阶层”的崛起推动了旅游的增长。鉴于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日益成为接受国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增加和创收的一大来源,中国与东盟促进旅游业发展更多地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关切而非社会文化方面的获益。同样地,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涌入中国,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中国软实力建设(通过政府资助的奖学金)的驱动。
在此背景下,游客或学生的流动与公共意识之间的联系可能很松散。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全面建设应采取更加务实的手段,超越功利主义的目的和考量。特别是有关社会—文化支柱的叙述应更多地集中于共同的挑战、愿景和愿望等方面,而不是采取当前固有的功利主义的做法。
二、要更为注重共同挑战和共同愿望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共同体意识是以长期存在的联系和互动为前提的。当前,在东盟与东亚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共同体的理念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愿望而非现实。如此来看,共同体的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相关各方的坚定承诺。
利用现有的承诺并协调参与国的优先事项有助于加强共同体建设正在进行的各项努力。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推动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2016年1月启动。联合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到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认可,为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致力于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和确保人民和平与繁荣提供了共同框架。
东盟把自身愿景和计划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对接。正如东盟负责社会文化共同体事务的副秘书长翁铁·阿萨卡瓦蒂(Vongthep Arthakaivalvatee)在2016年6月所说,“东盟认识到,在东盟与联合国合作框架内,在东盟成员国共同推动的《202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建立协同关系极为重要”④。
中国也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本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中。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还计划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⑤。
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两个特点, 使之成为中国与东盟加强合作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良好平台。首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使相关各国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愿景有所了解。随着相关各国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化并在这一全球性倡议与其国内优先事项之间建立协同关系,中国与东盟可以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换句话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个多边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共同议程,把中国与东盟等对话伙伴相互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是各国共同接纳的与本国优先事项和条件相一致的指导方针,也是一项包括具体目标和进度报告的行动计划,这将给参与国带来一些压力,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并尽可能地实现目标。
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的合作存在诸多优势,可持续发展目标使得中国—东盟伙伴关系的重点更加明确,应对共同挑战和达成共同愿望的意愿更加强烈,做出的承诺也更加坚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长期性,中国与东盟就该议程开展合作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社会文化项目,前提是双方都愿意且能够分享知识、开展交流、协调活动并开展各种合作项目。
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2016年,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成立,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课程以及各种短期培训课程。一年后,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成立,该中心“汇聚了中国和国际的资源, 推进发展研究,开展发展理论和实践研究,促进包括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内的国际发展问题研究及知识共享”①。
有了这样的发展势头,中国与东盟可以发展共同的叙事方式,将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的合作作为一项社会文化项目来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这种新的叙事方式可以为中国—东盟伙伴关系提供总体框架和共同核心,聚焦双方共同的挑战、愿景和渴望。
三、智库和学术机构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东盟内部合作及东亚与东南亚地区间的伙伴关系主要是由各国领导人通过“第一轨道”的活动来推动的。尽管宣告了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共同体的愿望、认同以社会—文化为支柱的共同体建设,东盟框架内及其与对话伙伴之间的人文交流网络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严格的审查或完全被边缘化。智库和学术机构在“东盟+3”各国支持的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东亚智库网络(NEAT)已经成为“第二轨道”平台,是对政府间(“第一轨道”)关系的补充。该网络是在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的支持下,由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n Vision Group)提议,于2003年成立的。在设计上, 东亚智库网络是一个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机制,也是区域合作“第二轨道” 外交的平台。由每个成员国任命1名国家协调员组成不同的工作小组, 制定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 并将建议和报告提供给“第一轨道”的相关会议。数年来, 东亚智库网络涉及的研究议题广泛, 如积极老龄化、 医疗保健和城市化等。与之类似的中国—东盟智库网络(NACT)也于2014年成立。
东亚智库网络或中国—东盟智库网络的模式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这两个网络的组成方式造成其成员固定且有限。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国家协调员有可能得以很好地发挥“桥梁”的作用;但对于幅员辽阔、多样性突出的国家来说,期望仅依靠1名国家协调员来做好这项工作是不现实的。这种“垄断”的联络方式导致这两个网络模式均有其局限性。
因此,问题不在于建立更多的与上述两个网络相类似的智库网络,而在于建立新型智库网络,扩大参与范围和目标范围。智库和知识机构网络应该更加包容,共同致力于东亚共同体建设,这意味着新型智库网络应该在幅员更大的国家设置更多的联络点,不仅应该包括国家政府层面的智库和知识机构,也应该包括地方政府层面的机构。这还意味着,这些网络不仅应该包括政府下属的智库,还应该包括非政府资助的智库②。为了保证更加广泛的参与,网络成员的构成应比东亚智库网络或中国—东盟智库网络的模式更加开放。
智库与学术机构的职能也应该得到扩大。如果东亚峰会“希望通过共同探讨政策问题,促进观点交流, 起草各方认可的方案”, 那么智库和学术机构在“第二轨道”外交之外还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智库和学术机构有条件把过去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地方观点和做法纳入主流,加强东亚共同体社会—文化支柱的建设。
对话伙伴之间及民众之间的知识共享远远超越了技术知识的相互转移。除了技术层面, 知识兼具制度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的涵义。知识还具有地方性特征, 不受任何简单典化的束缚。 智库和知识机构可以分享那些反映当地观点并包含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知识以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在这方面,现有的大学网络如东盟大学网络(AUN)和“东盟+3”大学网络(ASEAN+3 UNet)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中国智库和学者的步伐却远远滞后。中国投资项目在东南亚多个地区遭遇的一系列挫折表明了在当地社区如何看待中国投资项目及活動这一方面,中国智库严重缺乏完整的信息和到位的分析。笔者鼓励和支持中国智库和学术机构不仅要关注东盟国家的高层政治,同样还应关注东盟各国的基层,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就东盟智库而言,考虑到理解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这一趋势、过程及其结果的重要性,与中国同行建立网络也可能是有益的。
结语
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正在寻求塑造东亚共同体并不断加强这一方面的措施或实践,一直存在着争议。对于这一争议,最好是从适应规则、满足双方利益的双向社会化进程来理解。无论是哪派观点占上风,这一争论本身都表明,关于东亚地区共同体发展的核心问题尤其是中国在规则制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即将到来。
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三大支柱中,社会—文化支柱的重要性目前被政治—安全支柱和经济支柱所掩盖。这种不对称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政治安全及经济领域面临着更为紧迫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缘于对社会—文化支柱缺乏深入的理解,特别是社会—文化支柱对于共同体建设与规范制定的重要性的理解,这在以国际游客和留学生的数量来衡量社会—文化支柱的叙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社会—文化支柱作为薄弱环节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迎头赶上。加强社会—文化支柱建设,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何为“以人为本”的共同体,更清晰地聚焦共同面临的挑战及共同愿望。智库和学术机构应在架起国家、不同文化和社区之间沟通的桥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形成跨国网络,合作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相关知识的共享。
(责任编辑: 颜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