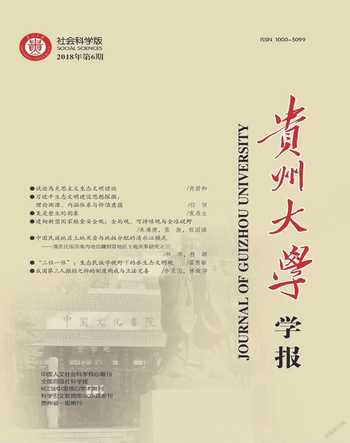法律研究与实践经验
理查德·A.波斯纳 胡德胜 张艳
摘 要:法律研究应对联邦司法机构的改善有所裨益。本底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充斥于顶尖法学院队伍。联邦最高法院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裁决提交给《美国案例报告》到其刊登出来之间的漫长耗时,拒绝披露那些不签发调卷令的案件的表决情况,拒绝给出回避和不回避的理由,不适当地将审理意见书的截止日期定在每年6月底,审理意见书过分冗长,异议意见容易被遗忘,裁决书的脚注时有前后冲突,过分依赖法官秘书等。基于访谈调查发现,需要由学术本底是富有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官运用不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专门技术知识的方法,开展学术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改进联邦司法机构。
中图分类号:D9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6-0114-05
我有一个座右铭,摘自丁尼生的《尤利西斯》一诗:
[做一个闲散的国王,无所事事。
安居于家中,统治着这个嶙峋的岛国。]
我与年迈的妻子相依为伴,分配食物,赐奖施罚。
用不平等的法律统治着野蛮的种族。
他们收存、他们睡觉、他们吃喝,
却不知道我的存在。①
在我对丁尼生诗句的感悟中,那位年迈的妻子不是我孩子们的母亲,而是需要加以诸多改进的联邦司法机构。本文的主题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学术研究,能够帮助改进联邦司法机构。
从高高在上的最高法院到位于最低层的移民法院和社会保障残疾人办公室,司法机构可以采用相当多的改进措施,跨学科法律领域(诸如法律、心理学和法律经济学)在改进计划的设计和评估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不过,我在本文中强调的研究方法,是那些不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专门技术知识的方法。因而,这些方法可以被那些没有交叉学科背景的法学学者使用。顶尖法学院的队伍越来越多地被来自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避难者所占据
在波斯纳看来,法学既不属于人文科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而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或者技艺。——译者注。,我因这一事实而烦恼 J. McCrary, J. Milligan and J. Phillips, The Ph.D. Rises in American Law Schools, 1960-2011: What Does It Mean for Legal Education?. 65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2016, pp. 545~546.他们注意到,法学院队伍中获得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领域博士学位的成员比例有所上升。。实践经验对于理解和改进法律至关重要,这表明所需求的法学教授是那些学术本底是富有法律实践经验的教授,而非本底是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教授。
我担任法官已经35年之久。在那期间,我对法律研究的兴趣逐渐集中于具体的领域,同时这样可以改善司法行为。那些基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反垄断及其监管的法律研究,往往对法官们解释、适用法律和那些支配或者至少应当支配这些领域的原则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猥亵儿童及其他强迫性的性犯罪者的刑罚及其恢复正常生活的可能等方面的法律研究,正在取得一些进步。这些进步表现为法律关于这些罪犯待遇方面的改革,虽然进步缓慢C. Mancini, D. P. Mears, 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and Sex Offender Legislation: Evidence of Evidence ̄Based Policy? 103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ogy, 2013, p. 1115.。心理學在法律研究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在打破“举止暗示”(指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可从其在法庭证人席上的外表及举止观察出来)的神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阅读证人的证言笔录能够更好地推断其真实性,因为“举止暗示”并非线索,而且容易使人分心
M. Minzner, Detecting Lies Using Demeanor, Bias, and Context, 29 Cardozo Law Review, 2008, pp. 2559~2566.。
我将会特别重视统计学研究。这些研究阐释了司法行为的诸多方面;从法官秘书记录法官意见的作用
T. C. Peppers, M. W. Giles, B. Tainer ̄Parkins, Surgeons or Scribes? The Role of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Law Clerks in ‘Appellate Triage. 98 Marquette Law Review, 2014, p. 313.,到对渴望晋升的低层法院法官行为的影响。比如,对于美国最高法院
L. Epstein, W. M. Landes, R. A. Posner, The Behavior of Federal Judg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Rational Choice,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37~379.,整个巡回审判中政治敏感案件判决推翻率的差异
K. M. Scott, Understanding Judicial Hierarchy: Reversals and the Behavior of Intermediate Appellate Judges, 40 Law & Society Review, 2006, p. 163.,地区判决差异
C. S. Yang, Have Interjudge Sentencing Disparities Increased in an Advisory Guidelines Regime? Evidence from Booker, 89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4, p. 1268.,以及诸多其他因素。政治学明显有助于司法投票中对政务,广义上的政治形态
C. R. Sunstein, D. Schkade, L. M. Ellman, Ideological Voting on Federal Courts of Appeal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90 Virginia Law Review, 2004, p. 301.、宗教
G. C. Sisk, M. Heise, A. P. Morriss, Searching for the Soul of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Religious Freedom Decisions, 65 Ohio State Law Journal, 2004, pp. 576~584.、性别
J. L. Peresie, Female Judges Matter: Gender and Collegi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Federal Appellate Courts, 114 Yale Law Journal, 2005, p.1759.、种族
P. K. Chew, R. E. Kelley, Myth of the Color ̄Blind Judg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acial Harassment Cases, 86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8, p. 1117. (原文标注年份为2009年,是错误的,故予以改正),以及其他类似的远离“法律”(法律教义)的影响因素的理解。政治学和心理学能够共同阐释司法心理的一些方面,比如有些法官具有个性权威且该权威影响着刑事判决
R. A. Posner, How Judges Think,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98~103. 我在该书中提出了法官心理中权威倾向的概要图。。
不过在本文中,我强调那些不取决于社会科学的司法行为的研究形式。甚至包括我遗漏的一些狭窄的领域,比如法官传记——它是审判知识的宝贵资源且其创作无需额外的法律训练。但是也存在许多不涉及额外法律训练的前瞻性研究,比如采访联邦法官。在我和米图·古拉提(Mitu Gulati)教授所做的关于联邦上诉法官秘书管理的一项研究中
M. Gulati, R. A. Posner, The Management of Staff by Federal Court of Appeals Judges, 69 Vanderbilt Law Review, 2016, p. 479.,有一项调查或多或少地随机选取了75位这样的法官,对他们进行电话访谈。我们发现:只有3.5位受访法官(占4.7%)说他们的秘书直呼其名;而且该3.5位法官中只有一位允许其秘书在法院外直呼其名,因为她坚信若自己的同事发现她给予秘书这样的称呼自由时将会很生气
虽然我关于法官秘书是否应该对其法官直呼其名这一问题的觀点是源于同古拉提的共同研究,但本文并不讨论这一内容。有关讨论详见:R. A. Posner, Divergent Paths: The Academy and the Judiciary, pp. 372~273.。
这种司法礼节奇怪的一点是,现代企业倾向于要求其所有职工彼此直呼其名,甚至公司的员工以姓名称呼其首席执行官
J. Glickman, Whats in a (First) Nam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 1, 2011), archived at http://perma.cc/U4AE-Q933.。这么做并非出于偏爱,而是意在营造这样一种氛围:相信能够激发极大的忠诚、承诺以及低层职工的努力。在此氛围中,低层职工发现自己的想法受到了重视。50年前,或许20年前,在商人和法官看来这种不拘礼节是不可思议的。商人已然改变,为什么法官没有呢?正如我贯穿全文始终所阐述的那样,因为包括司法部门在内的法律职业是古板的、向后看的、保守的甚至是缺乏信心的。
近期,我和阿贝·格拉克(Abbe Gluck)教授一起对联邦上诉法官进行了访谈调查。该访谈涉及法官们对法律解释的信心和实践。受访者可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我们称之为“讨厌鬼”,因为在处理立法存在瑕疵的一些案件时他们冷酷无情。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一项法令规定:“禁止车辆入园(公园)。”公园内的一位游客掉进了池塘,一位旁观者打电话叫警察,一辆救护车呼啸入园去抢救这位失足游客,但是警察以救护车司机违反法令为由处以罚款。大部分法官会认为警察做错了,因为法令的制定者本无意使“禁止车辆”等同于“禁止车辆,甚至救护车”。然而这些“讨厌鬼”却会说:救护车是车辆,因此法令内容包含救护车;即使结果很愚蠢,这是法令制定者把事情弄糟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清除混乱。
[第二类是进行一般折衷的法官。]
原文并没有明确指出第二类受访法官, 译者根据上下文含义加以鉴别,认为此段所讨论的法官是作者所称的第二类。——译者注。 我们所采访的法官中有一些拥有参与立法的经历。他们或是立法者,或是立法组成员,亦或司法部门法律顾问办公室等机构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他们对自己解释法律的能力很有把握,认为自己既知道何种立法历史能为立法者意图提供可靠的指引,也知道何种不能。这些“立法者”在运用多种法律解释时倾向于一般折衷性的选择。
第三類法官则更为折衷。他们依赖于各类解释援引,比如词典、各类立法历史,包括语言学和政策准则的结构、先例、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律师和法官们称之为“平义”)、隐含的法律目的、相关法律的含义。
第四类法官数量很少,他们依据常识对法律进行解释。其中又有几位法官完全怀疑立法解释。他们指出,制定法律的立法机构没有预见到诉讼中所涉及法律的含义及其运用所产生的问题。在这些案件中,法律并不存在预期的含义,而是让法官扮演立法者的角色。持此观点的法官不仅是普通法上的立法者,而且是制定法漏洞的造法者。
另外,对于接受访谈的每一起案件,都有一位参与审理的法官成为受访谈的成员。联邦法官之间有一个特定的交际圈,如果他们的采访者中包含法官就会使他们感到更自在。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一种完全未经研究的法官解读渊源。这种渊源就是经验和智慧中或予以运用、或没有运用的常识。我们不应该要求科学或者研究来证实以下问题:应该允许向陪审员提问,否则他们将会陷入这样的风险,即,他们在尚未知晓作出理智的裁判所需足够案情和知识的情况下,被迫对案件作出决定;应该允许陪审员于休庭期间随时在陪审团休息室内讨论案件(即使是不决定裁决结果的讨论),否则在应该仔细考虑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关键证据;也不应该给陪审团提供模式化的陪审指南,因为这种指南是拘泥于法律条文的。
不科学的、不系统的常识往往被视为法律惯例评论的基础,而且容易被法学教授、法官及律师等人嘲弄;其中许多惯例可以追溯到若干世纪之前,用于阐释隐含于无趣的法律文化中的枯燥乏味。法律界人士喜欢将自身视为行业协会内学识渊博的专家,或是掌握行业语言所隐含的行业教义的大师。许多律师、法官、教授以及法官秘书在没有如下行话标题下的原则和教义时会感觉赤裸裸的:“实质无罪”“清晰且有说服力”“专断和任性”“同样独特”“可疑类”“理性基础”“严格”“高度的(盖然性)”“中立性的”仔细检查,“狭义解释”“反向解释合同草拟人利益规则”“法律不涉及鸡毛蒜皮的小事”等(例如,维基百科列举了大约四百多个美国法律适用的拉丁术语)
List of Latin Legal Terms (Wikipedia), archived at http://perma.cc/MHC9-598L.。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术语都是不必要的。
联邦司法其他亟待研究的是关于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审判。对地区法官(包括破产法官和治安法官)的访谈是一项基本尚未涉足的技艺。其他技艺包括简易审判观察、法庭记录研究、模拟法庭、审判模式的运用、对国家审判辩护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Trial Advocacy)高度逼真审判文件的运用,以及安排法学院证据课程(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授证据时的任务)。
我尤其对我所提及的“地区法院研究”感兴趣。因为自从在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任职后,我在巡回区法院以志愿者的身份审理过一些案件。至今,我只审理过民事案件,进行陪审团审理、法官审理以及监督发现(supervising discovery)、协商和解、民事案件的审前阶段。随后,我开始审理刑事陪审案件。
入职地区法院以来,我学到了很多审判程序的知识。我了解到,所有像我这样成为法官前不是初审法官或者律师的上诉法官应该从事审判工作,因为我从自身的审判经验得知:从事审判工作与对初审法院判决的上诉审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历。但是像真正的审判法官那样,我在审判工作中都是凭直觉、猜想、推测而不是可靠的判断。
我最后要提及联邦最高法院——一个混乱的机构。该法院管理不善,尽管这不足为奇。请忘记法庭上法官座旁的痰盂(痰盂是“一个其上方通常为漏斗形的金属或者陶制容器,用作吐痰”
Define: Spittoon (Google), archived at http://perma.cc/NH84-DQ4D.):那纯粹是古文物研究的愚蠢
作者在《各行其是:法学与司法》(Divergent Paths: The Academy and the Judiciary, 2016)一书中提到:“自最高法院大法官向他们审判席后椅子旁边的痰盂吐痰以来,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但痰盂还在那儿,显然还在使用——作为垃圾桶。他们可能有点历史价值,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该被展览而不是隐藏。”〔美〕理查德·A·波斯纳:《各行其是:法学与司法》,苏力、邱遥堃译,第28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本文译者认为,文中所表达的意思应该与该书中同义。——译者注。
想想最高法院存在的下列问题吧:(1)在裁决被提交与其被《美国案例报告》(U.S. Reports)刊登之间的五年耗时。(2)对那些不签发调卷令的案件,拒绝披露投票表决情况(不是指投票人信息)。然而,披露将会表明最高法院对于所寻求解决问题的重要性的看法,从而鼓励或者不鼓励那些劝说最高法院来审理能够体现该问题的案件的未来努力。(3)当法官对审理某一案件予以回避时,拒绝给出回避的理由;或者,在回避提议是有道理的情形下,拒绝给出不回避的理由。(4)许多审理意见书的截止日期是6月底而不是9月底,然而,定在9月底会使案件在次年4月开始的开庭期可以得到正当合理的考虑,而不是定在6月底导致的为了暑期休庭的匆匆结案。(5)审理意见书过分冗长。(6)异议意见容易被遗忘。(7)前后冲突的脚注以及因偶然疏忽写入的无礼词句。(8)对法官秘书的过分依赖。上述问题可以由一位激进的首席法官予以改变。然而,改变不了的是法官们不制定法律而仅仅适用法律的这一司法假象
R. A. Posner, What Is Obviously Wrong with the Federal Judiciary, Yet Eminently Curable: Part II, 19 Green Bag 2D, 2016, P. 266.。
我还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从20世纪60年代的“沃伦法院”的兴盛时期开始走向衰落
后面几段的内容,我基本上编写自《各行其是:法学与司法》一书的第249-251页。。回想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在联邦最高法院做了一整年(1962年)法官秘书。随后在1965年至1967年,我任职司法部副部长的助理。让我震惊的是,虽然最高法院过去的资源相较于今天而言相对匮乏,但是今天的诸多优质资源并没有让最高法院的工作得到改进。现在每位法官都有4名法官秘书;而1962年这一年每位法官只有两名法官秘书(不过,首席大法官还有第三个法官秘书来负责审查调卷令的申请状)。这一时期,很少有从未给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当过秘书的人被聘为最高法官秘书。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最高法院以不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了不聘用给其他法院法官做过秘书的人为最高法官秘书。这些最高法院法官秘书都很能干——其中一些还很优秀,不过平均水平比今天的要差一些;最高法院法官秘书这个职位如今不再被垂涎了,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奖金。而且,最高法院法官对法官秘书任职程序更加随意,通常将这一职位给了法学教授、私人朋友或者业内的熟知,而不对候选人进行面试,甚至不接收其他人的职位申请。当然,那时还没有电子数据检索。同时,也没有人才数据库;没有有组织的最高法院律师协会。尤其完全不同于今天的是,那时候法官在口头辩论时的提问寥寥无几——尽管当时分配给每一方辩论的标准时间是45分钟,而不是现在的30分钟。即使如此,最高法院那时对许多案件听审次数是现在的两次之多。或许,那时候的法官们工作更加努力,因为名人文化当时还没有接纳他们。事实上,除了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法官,其他人都是“墙角花”。例如,雨果·布莱克法官(Hugo Black)像道格拉斯法官一样有魅力,不过没有赢得大众的欢心。
那时候最高法院的法官,依任职时间顺序依次是:雨果·布莱克、威廉·道格拉斯、汤姆·克拉克(Tom Clark)、厄尔·沃伦(Earl Warren)、约翰·马歇尔·哈兰二世(John Marshall HarlanⅡ)、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拜伦·怀特(Byron White)以及亚瑟·高德伯格(Arthur Goldberg)。其中有些人不喜欢表现自己,但是布莱克法官、道格拉斯法官和怀特法官都是极其聪明的(即便道格拉斯法官缺乏责任心),而且哈兰法官、斯图尔特法官以及布伦南法官可能没有那么聪明但却非常称职。他们的职业背景比最高法院现任法官的职业背景更为多元化。布莱克法官曾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出庭律师,有影响力的参议员。道格拉斯法官是耶鲁大学著名的现实主义派法学教授,曾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负责人。沃伦法官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州三届州长,且其第一届任期正值二战期间。克拉克在杜鲁门政府时期曾任美国司法部部长。布伦南有着私人律师业务方面的杰出职业生涯,曾是二战期间的军事管理员、新泽西州初审法官,且一度是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法官——那时,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在首席大法官亚瑟·范德比尔特(Arthur Vanderbilt)的领导之下,工作极其出色。高德伯格曾在肯尼迪政府担任过劳工部部长。怀特在同一时期担任司法部副部长。此外,他们的教育背景也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两位法官毕业于耶鲁大学,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一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其余的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阿拉巴马大学、西北大学、纽约法学院以及伯克利大学。与此不同的是,最高法院现任法官中,只有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法官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年(且毕业于此),其他法官要么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要么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现任法官都没有显著的政治经历(没有人曾任政治性官职)。只有索妮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法官拥有大量的庭审经验,她也是其中唯一曾经担任过审判法官的。
正是在1962年这一年,查尔斯·惠特克(Charles Whittaker)和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法官被怀特和高德伯格法官接任,从而强化了沃伦法院。直到1969年厄尔·沃伦法官退休和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法官接任首席法官,最高法院在成员组成方面只有两次变化:高德伯格于1965年被亚伯·弗塔斯(Abe Fortas)法官接任,克拉克于1967年被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法官接任,不过,它们都不构成显著的意识形态变化。沃伦法院在一些领域问题的处理上有些过分,然而它的大多数里程碑式的判决影响至今。例如,关于立法席位的重新分配、辩护权、宪法第四修正案在各州的适用、米兰达警告规则、性权利问题等方面的判决。现在的最高法院似乎不太可能留下类似的遗产,尽管可能会留下极其丰富的资源和极其优越的工作条件。
我坚信,那时候最高法院法官的平均水平高于现在的。现任法官的人员配备(法院秘书)太多,口头辩论时讲得太多,并且在审判之外的活动中投入了过多时间。然而,先前的最高法院能力更强的原因(尽管根据现在的标准来讲,它很缺资源)主要是当时法官职业背景的多元化。如今,从教育和职业背景的角度来看,虽然存在着显著的意识形态差异,但法官们却“本是同根生”
R. A. Posner, Divergent Paths: The Academy and the Judiciary, pp. 249~251.(我这里没有考虑与最高法院相关的种族、性别或者信仰形式方面的多样化)。
在对最高法院的有益改革中,我要强调的是:减少法官秘书,取消无序的优先秘书任职资格;听审更多的案件;给口头辩论分配更多时间;未经法院考虑并获得允许,不得提交“法庭之友”诉讼摘要;法官职业多元化;《美国案例报告》应及时出版;取消审理意见书的脚注;限制审理意见书长度;任命经证实具有高水平管理技能而且享有举国声望的人担任首席法官(这样的法官,比如威廉·霍华德·塔夫特(William Howard Taft)、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以及厄尔·沃伦);对口头辩论进行实况电视直播;取消6月底的审理意见书截止日期和暑期休庭;在宣布前一天就向媒体提供审理意见书,使媒体在审理意见书宣布当天能够发表可靠的文章;不要求最高法院法官在华盛顿定居或者工作;消除这一假象,即,法官是在“解释”18世纪的宪法,而不是在随时间地发展而编造宪法性法律。另外,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扔掉那些痰盂吧!
当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改革可能无一能够得到采纳和实施;若有的话,将确实非常难得。然而,我并不担忧这篇短文是否提出了可行的改革措施;我更关心的是,告诉读者法律改革无需取决于社会科学、其他科学或者严格的学术研究。联邦司法是我最了解的美国法律制度,事实上也是我了解的唯一一个。美国法律总体上以及联邦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大多数要么显而易见,要么无需经过科学研究(例如,《蓝皮书》的荒谬以及对斜体句号的恐惧
美国的法学院要求学生按照《蓝皮书》(The Blue Book of Grammar and Punctuation)完成其法律写作备忘录。如果学生的备忘录包含了斜体句号,他们就可能受到惩罚。作者在此批评《蓝皮书》式的形式主义,强调简洁和便利。——译者注。),都是凭洞察力和实践经验就可以辨别的。不过,也有一些问题(例如现行陪审团审判的多个方面的缺陷)需要经过更多研究才能够发现。
(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