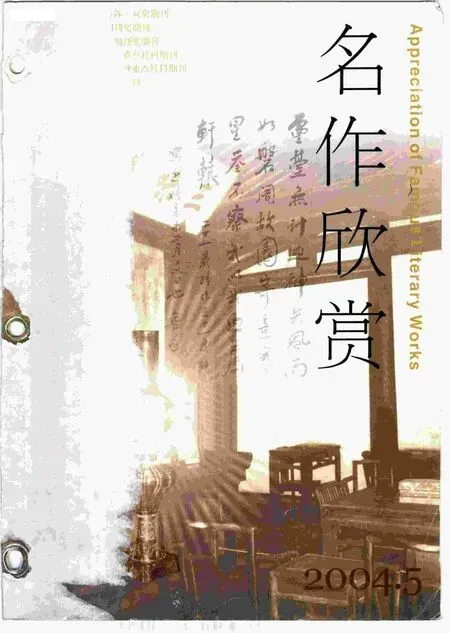周作人与日本人的“心中”及“情死”
魏丽敏
1926年,周作人写了一篇题为《心中》的散文,较为集中地论述了他所理解的日本人的生死观和爱情观,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当时的报纸,报道了日本人在西山旅馆的自杀事件:一对青年男女,大概是因为恋情受制于现实的压迫而不能实现,就双双自杀了。据说他们的遗言是请求合葬在朝阳门外。女的写信留给家人,自叹命薄,并请求父母无论如何不要再把妹妹卖为艺妓。而男的则写了一首绝命诗如下:
交情愈深,便觉得这世界愈窄了。虽说是死了不会开花结实,反正活着也不能配合,还有什么可惜的这两条的生命。
这在中国,大概自古以来就称之为“殉情”,而在日本则叫“情死”——也可以叫作“心中”。不过,据周作人说,情死之事日本古已有之,但“心中”这个说法却是日本德川时代的产物。
大凡青年男女之相爱,差不多只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和一见钟情、擦肩而过两种模式,自然还有日久生情或友情转为爱情等,但追溯其开端,其实还是可以归于前面两种。“心中”之最初意思,差不多就是字面意義——我开始把你放在心上了。然后为了表白心迹,就有了互赠信物、男子刺字与女子割发为誓等。再进一步那就是以一死表白相爱之深等。西鹤,这位日本江户时代的小说家就称之为“心中死”,后来这“心中”差不多就等于是专门用来指男女二人的“情死”了。
至于那些男女做出共同赴死的决定何以如此坚定,大概和他们对来世的期盼有一些关系,更是出于对现实的绝望:
幽暗的独木桥,郎若同行就同过去罢,掉了下去一同漂流着,来世也是在一起。
我很奇怪的是,1926年的周作人,早已娶妻生子,作为日本女婿的他,婚姻也算幸福,至少还算正常,如何会对这样的“心中死”产生兴趣呢?不知周作人的心中,是否也曾有过“心中”的念想。再想到周作人曾经写过《初恋》这样的文字,发现要真正了解他确实很难。
因为周作人这样的作家是不愿意在其作品中袒露任何心中奥秘的,接下来他为读者考证的,是此类情死在日本历史上源远流长——据那部很有名的《日本情史》,日本早在公元十四世纪,就有侍女与男主人有了私情,事情暴露后无路可走,终于双双走入深山,共同伏剑而死的记录,其情景可谓惨烈之极。他们临终前所希冀的,也还是那句:“今生既而不幸,但愿得来世永远相聚。”——这大概是日本后世情死的先驱罢。
周作人曾在另一篇散文《唁辞》中这样说:“死总是很可悲的事,特别是青年男女的死,虽然死的悲伤不属于死者而在于生人。照常识看来,死是还了自然的债,与生产同样的严肃而平凡,我们对于死者所应表示的是一种敬意,犹如我们对于走到标杆下的竞走者,无论他是第一着或是中途跌过几跤而最终走到。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死之赞美者’的话未必全无意义,那么‘年华虽短而忧患亦少’也可以说是好事,即使尚未能及未见日光者的幸福。”这里,明显可以看到他受日本文化中生死观的影响。
对于日本伟大的剧作家近松(近松门左卫门),周作人更是从讴歌死亡的角度出发,认为近松的剧作在表现死亡方面格外出色。这近松本是日本江户时代净琉璃(木偶戏)和歌舞伎剧作家,原名杉森信盛,别号巢林子,近松门左卫门是他的笔名。他出身于没落武士家庭,青年时代做过王公侍臣。后来有感于仕途多艰,毅然投身于被人鄙视的演戏艺人行列,从事演剧和剧本创作。他从25岁左右开始写作,直到72岁去世,共创作净琉璃剧本110余部、歌舞伎剧本28部。按照周作人的说法,这近松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写“心中”的,而且对这痴情男女给予了最大的同情。据说近松的净琉璃剧盛行以后,日本民间的男女心中事件大为增加,让我们不禁想到当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民间也是有很多人模仿维特而自杀的情形。此外,与近松差不多同时代,还有也属于净琉璃一个分支的《新内节》,按周作人的说法,这《新内节》对于“心中”的狂热向往已经到了病态程度,所以不管怎样,最后都是以死作为唯一的归宿。而当时一些青年女性听了这些流行的悲歌,就无端引发很多悲剧,以致最后日本政府不得不禁止《新内节》,直到明治维新才得解禁。
日本人这种对于死亡的格外敏感和近于病态的追求,周作人认为我们中国人是不大能够理解的。无论是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还是老子的“归根日静,静日复命”,抑或庄子为妻子之死的“鼓盆而歌”,其实中国人所看重的无非是现实人生以及死后的回归自然而已,整体上总是给人以虽无奈却看破之后,只能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而很少会有日本文化中那些狂热追求死亡以及对死亡行为的病态性赞美。至于原因,周作人认为可能和我们处于大陆而日本是海岛有关,生存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生死观以及美学观。
对此,蒋百里在他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见解,认为日本人热情而又性急,而岛国特有的地理气候条件,又容易使得日本人形成悲观性格:“地震、火山喷火,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予日本人一种阴影。”对于日本人何以会有“心中”或“情死”情结,戴季陶在其《日本论》中也有这样精彩的分析:“情死的事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很多情死的人,不是为达自己的目的而且不是为达共同的目的,是为达所爱的对方的目的很勇猛地积极地做所爱者的牺牲。他们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有相对的两个人间的绝对的恋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为了这个世界能够舍去一切世界。”
不过,周作人和鲁迅一样,却是能够从日本文化中看出其表面悲观之下还有达观之底子的少数人。在另一篇名为《老年》的散文中,他就根据松尾芭蕉的俳句,对芭蕉的人生观有这样的评价:“芭蕉本为武士后来出家,但他毕竟还是诗人,所以他的态度(对于色欲和老年这两件事——引者注)很是温厚,他尊重老年的纯净,却又宽恕恋爱的错误,以为比较老不安分的要好得多,这是很难得的高见达识。”请看芭蕉的俳句:“朝颜花呀,白昼还是下锁的门的围墙。”——意思是早晨可以出来看到初开的花儿,平时就还是要关起门来。我们总是说周作人散文有味道,其实就是在这些看似淡淡的文字中,透出他对人生的淡淡忧伤,其实也不是忧伤,而是自然而然的快乐。所以周作人非常喜欢陶渊明的“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至于这思想属于儒家还是道家,其实不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日本文化怎样受着地域或气候的影响,但对于人生不过是一个舞台而每个人都有出场也都有谢幕这一点,与中国文化还是有着内在的一致,如果说这一致到底是什么?那大概就是所谓的“普遍的人性”罢。
写到这里,不由想到所谓中国人的“大团圆”情结,鲁迅曾对此有所批判,并在《阿Q正传》中给予辛辣的讽刺。从批判国民劣根性角度,鲁迅自然非常深刻,且此种心态今天亦然根深蒂固。但如从另一角度看,这“大团圆”情结正反映了中国人内心深处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所以渴望在艺术中发见美丽与诗意,以及凡事追求美好与圆满的审美情趣,则也还不错。对此,周作人也有相似见解。他在《赞成大团圆》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民不爱悲剧,需要大团圆的这件事,无论在艺术专门家如何批判,我们外行的看法,只就中国前途着眼,觉得这是对于人生很好的态度,大家应该拥护的。”兄弟二人看似有分歧,其实只因视角不同。鲁迅注重的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所以反对大团圆。而周作人是从普通民众的简单的世俗愿望出发,所以理解他们的大团圆情结。的确,大团圆思想固然幼稚可笑,因为人世间万事当然是以悲剧收场更多,但作为世人应该有的理想或者说幻想,不是很自然而然么?人们走进剧场或者捧起一册小说,固然可以希冀看到生活的真实与残酷,但也希望借此让自己从严酷的人生中暂时解脱出来,从艺术欣赏中获得轻松与喜悦,给他一些美丽却虚幻的肥皂泡又有何不可?至于这欣赏者是否能识破这些美丽的泡沫,就不是艺术家的责任了罢。当然,那些故意画蛇添足,要让宝玉和黛玉结合的人,才是真正不懂得普通民众的悲哀与幸福,他们无论怎么试图续《红楼梦》,都只能暴露他们根本不懂人生的真谛,也不懂文学的真正价值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