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生戒烟
○陈四益
梁实秋和林语堂相似之处太多。梁林二位开始吸烟的时代,纸烟已渐渐统一“烟坛”。他们都留过洋,带些洋派,所以烟斗、雪茄都是领略过的。吸烟在那时尚属时尚,两人染上烟习不足为奇,既不算领风气之先,也不算对科学的蔑视。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中叶,也就是二位先生都先后实行戒烟之际,吸烟对健康的严重危害,已经不断为科学界披露。
林先生的戒烟是失败的。他大约戒了三个星期就“悔悟前非”了,反过来称自己的戒烟是“昏迷”,是“懦弱”,甚至是一种“下流的念头”。二十天中的这种反复,若以现代认知来说,烟草中尼古丁的致瘾性,会使吸烟者难以摆脱对烟草的依赖。近年,这种对烟草的依赖,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一种慢性疾病。吸烟者的复吸,并非一定关系于意志力的强弱或人品,尤其是林先生吸烟的友人们“吞云吐雾”的诱惑,使他“嗒然若有所失”,终又重操“旧业”,此后再也不曾戒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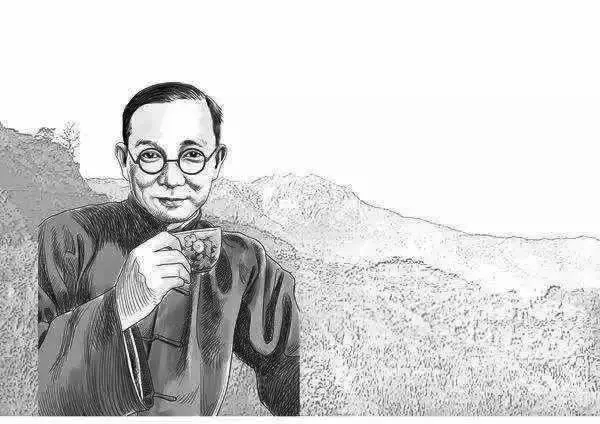
林语堂
作为烟草依赖患者,戒而复吸,就应当找医生咨询,寻求戒烟帮助。然而林先生的为人,是不肯这样做的。他主张以自我为中心,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当初他立意戒烟,大概觉悟于吸烟的危害,并觉得戒烟不难。等到熬不过烟瘾时,他又替自己找一番说辞,把复吸说成是自己新的觉悟与复归。为了证明这新的复归的合理性,他故意找出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强为之辞。
他说,“试问读稼轩之词、摩诘之诗而不吸烟,可乎?不可乎?”又说,“谁都知道,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这样的强词夺理,颇令人发噱,就像一个顽童东拉西扯地找出些不成理由的“理由”为自己“碎了花瓶”辩护。

梁实秋夫妇
试想,唐宋之世是并无烟草的,但当摩诘吟诗、稼轩填词之际,难道不曾意到神飞,锋发韵流?庄周、司马迁之文,屈原、宋玉之赋,李白、杜甫之诗,东坡、稼轩之词,王实甫、马致远之曲,哪一样是靠着吸烟写出来的?写尚无须,何况乎读。但是,林先生偏偏就这样为他的复吸辩护。你要真以为吸烟同写作、阅读有如此重大关系,不免上当。
梁先生的为人,似乎更拘谨、认真,不像林先生更多受老庄的影响,就像林的文章天马行空、恣肆不拘,而梁的文章细密严谨、流畅委婉一样,虽然他们都欣赏幽默。
梁先生一生只戒过一次烟,从此再未吸过。他并非烟瘾不大,当其戒烟之时,已有几十年吸烟的历史,吸烟量已从一日一包进而两包,再进而一听一五十支,烟瘾可谓大矣。但是,他没有选“黄道吉日”,也没有“诹访室人”,只是闷声不响,一股脑儿把剩余的纸烟丢在垃圾堆里,烟嘴、烟斗、烟包、打火机则分赠别人。后来也曾因烟瘾而六神无主、手足失措,但终于没有再吸,一次成功。
若论文章,我更喜欢林语堂先生,若论戒烟,我更欣赏梁先生这样的态度:“我吸了几十年烟,最后才改吸不花钱的新鲜空气。如果在公共场所遇到有人口里冒烟,甚或直向我的面前喷射毒雾,我便退避三舍,心里暗自咒诅:‘我过去就是这副讨厌的样子。’”
中国的烟草业喜欢讲名人吸烟的故事,但从不见他们提到梁先生这种更符合现代观念的认知与态度。这也不怪,他们巴不得所有想戒烟的人都向林语堂看齐,以保证财源滚滚。
一切爱惜自己同时也爱惜家人、爱惜他人生命的朋友,在戒烟问题上当弃林而取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