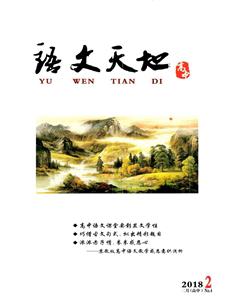记叙文写作中主题揭示方式探究
丁雪霞
记叙文以写人记事为主,但是必须表达一定的主题才有意义,而主题的揭示必须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体现出别样的匠心才能被深刻、巧妙地传达。高中生往往懂得叙述,却窘于主题揭示的艺术能力。为此,我们应当积极探究揭示主题的艺术途径。
一、精准议论,凸显主题
高中学生往往具备借助议论揭示主题的能力,但是也常常出现议论泛滥,甚至喧宾夺主的弊病。这就要求教师指导他们准确把握议论性内容的设置时机和容量。有的高中生喜欢在行文之初即展开一段哲理式的议论,使得主题过早地暴露出来,削弱了引人入胜的力量。所以,我们有必要提醒他们开端的议论最好点到为止,甚至不采用议论的方式。
不少高中生在记叙时生发许多感慨,往往以议论为最为主要的表达方式。一方面,这样做淡化了记叙的色彩;一方面也使主题过多地暴露,无法带给人以想象的力量,使文章少了艺术性、趣味性,同样不可取。
如果放在结尾,高中生似乎有很多可以议论的话,但是却于记叙文而言最令人反感,恰如狗尾续貂,拖泥带水。如果非得以议论收结,就必须言简意赅,点到为止,以便于给读者以思考的空间和时间。比如冯骥才写《珍珠鸟》,只一句“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便使主题赫然呈现。这可概括为“珍珠鸟式”议论。
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仅仅以一句关于希望的议论含蓄地揭示了为梦想而探索的思想,给读者留有无限的思考余地,恰如空中响鞭,久久回响。《祝福》一文里,在写到祥林嫂询问“我”关于人死后的魂灵的问题时,有一段议论,但是作者通过心理描写的方式呈现出来,当然区别于中规中矩的论说文中的議论,相当巧妙。这可概括为《祝福》式议论。
二、创设情境,寄寓主题
情境是物象、情感、思想共同交融的综合体,记叙文也可以营造典型情境,寄寓主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小说中获得启示。因为小说的主题往往依靠特定的情境传达出来,比如《祝福》最后一段:
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样的描写创生了特定的情境,具有了特定的意义,似乎暗示着题目“祝福”的含义。其实,在这祝福声中祥林嫂寂然死去,这一喜一悲的映衬就具有了讽刺和批判的力量,暗示了封建礼教和封建社会对人的戕害,对祥林嫂这样的弱势人群给予了无限的同情。这种揭示主题的力量震撼人心。同样,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写法迁移到记叙文的写作之中,使得主题的表达耐人寻味而又深刻有力。
诗歌本身就具有画面美、含蓄美、情感美和意境美。如果高中生以诗歌的形式做结表达主题,那么同样就具有了特别的艺术魅力。这也符合高中生喜欢独具一格、追求自我的特点。海子有一句著名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诗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该句营造了特定的情境,使人产生许多遐想,作者的思想情感、人生理想便寄寓其中,也就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性。我们也不妨将这种形式化用过来,通过创生特定的情境完成主题的表达,可称之为“海子式”。
当然,高中生写记叙文还必须考虑到“应试”之需,在主题表达上要适当注意高考中写就的作文的主题必须是明确地说出来的,让阅卷教师一看就懂。不能像某些文学创作一样去追求含蓄蕴藉,需要读者慢慢品味欣赏。
三、巧借人物,体现主题
写人记事中的人物形象设计往往事关主题的表达,主人公的角色定位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往往寄托着作者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反映作者的社会理想。所以,主人公的言谈举止正是主题表达的载体,主人公的情感、态度和思想认知其实也就是作者自身的写照,也就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代言人。从这个认知看,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也就是作者的喜怒哀乐,主人公的精彩台词也就是作者的宣言,即主题集中体现所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保尔其实就是写他自己,高尔基写《童年》《我的大学》《母亲》也就是自传体三部曲。这一点,很多高中生并没有意识到,教师必须点拨到位。
所以,凡出现在作品中的人物,要么是主人公的同类,要么是对立者,要么是“以我观物”者,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都为塑造主人公服务,为揭示小说的主题服务。
当然,所谓的次要人物其实也是作品中必不可少的角色,除了作为主要人物的陪衬之外,还可以充当作者的代言人,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个次要人物也就是作者自己。比如《孔乙己》中的“小伙计”、《祝福》中的“我”等。
所以,写人记事的一般性记叙文和小说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引导学生将小说写作的方式方法迁移到记叙文写作之中来。小说主题表达的手段艺术性很强,我们从小说主题表达的视角来关照记叙文主题的呈现往往会带来意外的惊喜。以上所述,还显浮浅,我们应当引导学生不断地研读、发现、迁移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