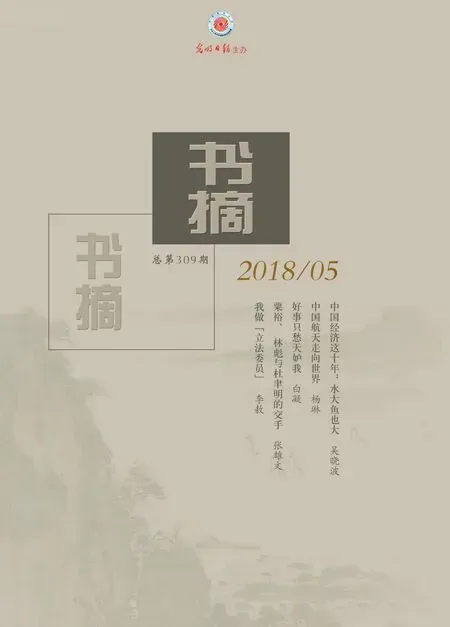人道
☉冯友兰

君子小人
一社会之分子,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即是依照一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以行动者,其行动是道德底。小人即不依照此基本规律以行动者,其行动是不道德底。若一社会内所有之人,均不依照其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以行动,则此社会即不能存在。所以照旧说,对于一社会说,君子为其阳,为建设底成分;小人为其阴,为破坏底成分。如一社会之内,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此社会之依照其理,可达于最大底限度。如此,此社会即安定;此即所谓治。如一社会之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此社会即不能依照其理。如此,则此社会即不安定,或竟不能存在;此即所谓乱。在乱时,社会之理或某种社会之理,依然是有,不过此社会之人,不依照之而已。此即朱子所说:“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道是亘古亘今,常存不灭之物”,即在幽厉之时,道亦不灭,不过幽厉不由之而已。
智,良知
我们说,我们有知,能知所谓至当或“天然之中”,不过可有错误,且事实上常有错误。对于道德之知识,所依照之理,即是智。孟子说:“智者,知此者也。”又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合乎所谓至当或“天然之中”者为是;不合乎此者为非。人对于所谓至当或天然之中,愈能知之无错误,其智即愈大。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即我们的知之智者;我们的知愈良,即我们的知愈智。
信
有以为信者,诚也。孟子说四端,不及信。朱子说:“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诚心为四端,则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犹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而水火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故土于四行无不在,于四时则寄王焉。其理亦犹是也。”(《〈孟子·公孙丑上〉注》)如此说,则所谓信者即以诚行仁义礼智也。此说亦可通,但不必如此说。我们尽可取普通所谓信之意义,即此意义,即可见信之所以为常。一社会之所以能成立,靠其中之分子之互助。于互助时,此分子与别一分子所说之话必须可靠。此分子所说之话,必须使别一分子信之而无疑。我于此写文而不忧虑午饭之有无,因我信我的厨子必已为我预备也。我的厨子为我预备午饭,因信我到月终必与之工资也。此互信若不立,则互助即不可能,即此小事,即不能成。若在一社会之内,其各分子所说之话,均不可靠,则其社会之不能存在,可以说是“无待蓍龟”。人必有信,不是某种社会之理所规定之规律,而是社会之理所规定之规律。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