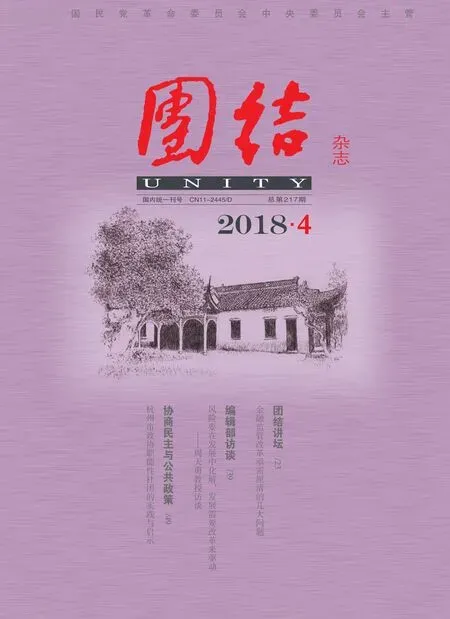风险要在发展中化解,发展需要改革来驱动
——周天勇教授访谈
◎张 栋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这显示中共中央对金融风险已经高度重视,非常警惕,也说明我国确实已经积累起了严峻的金融风险。如何理解、应对我国当前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个值得探讨、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以飨读者。
记者:当前我国面对的金融风险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周天勇: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经济总体负债率太高。尽管90年代末也出现过坏账问题,但那时国民经济整体负债率不高。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整体负债率,一般共识是270%左右,负债率的快速提升基本是近十年来的情况。
第二,是经济增长处于下行周期。自改革开放到2012年,中国经济以平均9.8%的速度增长了33年,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14.23%,2012年跌破8%,2017年是6.9%,2018年上半年为6.8%,近十年总体处于增速下行周期。
第三,是目前的资产泡沫太大,主要是房地产。一般认为,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应该在5倍左右,当前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大多都在10倍以上,一线城市大多在25倍以上,显著过高。
第四,是贸易环境恶化。中美贸易摩擦,这是我国面对的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带来了顺差减少、资本外流的压力,给人民币汇率造成冲击和不确定性,加大经济下行压力。不论美国的目的是缩小逆差、抑制中国发展还是促使制造业回流,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达成的,贸易摩擦可能会走向长期化。
所以我们当前面对的金融风险比以往要严峻得多。
记者:地方债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风险领域,其形成自地方政府的投资建设行为,您如何判断地方债的规模及其对应的资产质量?
周天勇:政府投资大多是投向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公共品,比如公园、城市道路、政府大楼,都没有收入,没有现金流。准公共品,公共交通、水电基础设施,有收入,但不会有很多利润,甚至是亏损的。政府投资主要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长期看会助益经济增长,但依靠这些投资产生的现金流去偿还债务是不现实的。
目前,地方政府债券余额约17万亿,这是显性的部分,此外还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对此有不同的评估,有的评估是约30万亿,有的评估是约47万亿,有的评估更高,此外还有以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形成的债务。地方债在不同口径下,估算的结果不同,尤其隐性债务难以准确评估。债务规模模糊、不透明,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是潜在的风险因素;同时不同的地方,债务规模和地方财力的匹配程度也不相同,有地方债务水平健康,但肯定也有地方债务水平过高,兑付困难。
地方债在总体规模上可控,局部出现违约也是难以避免的。中央政府已经明确了不兜底的态度,这是很必要的,中央财政和央行再贷款兜底会让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更无忌惮,形成希腊向欧盟转嫁债务一样的道德风险,风险将会继续恶性累积。中央财政和央行再贷款不兜底情况下,地方债违约,那该清算就清算,该处理资产就处理资产。
记者:房地产是我国信贷的主要担保品,信用创造也依赖于此。房地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可能会对商业银行资产安全、货币流动性产生冲击。在您看来,房地产价格脱离控制、剧烈波动的风险有多大?
周天勇:第一,房价明显是过高了。第二,房价过高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房价会不会落。从供需两个角度看,供的方面,如果地方土地财政制度不变,政府保持对城镇建设用地垄断供给;需的方面,如果居民的资产配置渠道狭窄的情况不变,股市继续低迷,实体经济投资风险大,利润率低,外汇管制,资金向外转移受到限制,那么居民财产保值增值的配置渠道,就还是只有一个出路,就是房产。这样房价应该会保持既有的格局,继续上涨。房价继续上涨,对投资房产的人来说是利好,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利好,但泡沫会越来越大。
2017年我国城镇住房存量大概在3.7亿套左右,其中由农民购买持有的大约3000万套,城镇居民拥有的住宅约3.4亿套,我国城镇居民户数大约在1.7亿左右,其中无房租住的约13%,一套住房自住的约66%,多套房的大约21%,计算下来,大多数的城镇住宅的拥有者是多房户,多房户户均约6.3套住宅。3.7亿套住宅,粗略计算,按每套3人计,可以容纳约11.1亿人口,显然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没这么多,空置数量肯定比较大。
政策方面,政府当前也面对一个两难,房产税要不要开征。不开征,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巨大,难以缓解;开征,房产的持有成本上升,多房户肯定是要抛售出货,房价可能会下降。
记者:前不久,有新闻报道由于监管规则的变化,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飙升。这虽是个例,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确实也是一大隐忧,您如何观察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
周天勇:我国银行业的结构,要分成四大行、股份制银行、地区性的城商行、农商行,或者广义地再包括小贷公司和网络信贷平台。其中资产质量比较稳定首先是四大行,首先是贷款的审慎性,风险控制的严格程度,四大行90年代初不良资产剥离之后,有很大的提升;全国性的大银行,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或者受干预较少;资产规模大,储户信任度高,流动性好,抗风险能力强。次之是股份制银行,也不受地方政府影响,但规模上弱于四大行,抗风险能力上差一些。风险比较高的是地区性的城商行和农商行,一般是由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转制而来,本身规模小、底子差,很多原有的不良资产在转制中并没有得到处理。转制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是受地方政府干预太多,本身就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目的也在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即使是明显没有现金流的贷款项目比如修路,这种区域性银行很难抗拒地方政府的要求,有些城商行60%的贷款投向地方政府相关的项目。除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或是已经上市,资本结构相对健康,大部分城商行可能风险比较高,农商行的问题可能更甚。城商行和农商行的问题,也不仅限于其自身,这些银行本身资本少、存款少,大量的资金来自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如果风险发生,可能会在银行体系中传导,甚至放大。
至于小贷公司,如果是私人企业,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一般问题不大。互联网借贷平台,如果排除那些违法违规的平台,最大的问题是杠杆率太高,抗风险能力低。
银行体系的风险点还有一个是银行的表外业务。很多银行正常信贷流程难以操作的业务被挪到了表外,通过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渠道操作,这部分业务整体情况不明朗、风险比较高,但这些风险的承担者并非银行本身,而是投资者。如果风险出现短期、集中释放,不会对银行体系造成直接冲击,但会造成社会风险。
记者:90年代末,我国曾经对银行业不良资产进行剥离,成立四大资产处理公司。今天回看,不良资产在发展中被消化,并没有形成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当前我国面对的金融风险能否像以前一样在发展中被消化?
周天勇:不良资产的消化主要是看经济增长处于上行周期还是下行周期。1998年、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不到8%,但从接下来2000年后,经济增长率就超过8%,之后一路上行,2007年最高达到14%。在经济增长上行周期,第一困难企业可能会复苏脱困,或者资产重组后产能重新得以发挥,不良资产可能在运行中转化成良性资产;第二是经济扩张期,新产生的不良资产会比较少;第三是随着经济的扩张,不良资产的相对规模会逐渐变小。2007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2012年掉到8%以下,至今增长速度一直是下行趋势。在经济增长的下行周期中,产能利用率下降,破产企业增多,良性资产规模增长放缓,消化不良资产会更难。即使在下行周期,也需要一定的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速不断下滑,那么不良资产的规模可能还会不断累积。这如同一辆自行车,有些故障,但有速度就不会倒,速度太慢一定会倒。
记者:防范金融风险的最终落脚点还是维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我国当下经济增长放缓。您怎样看待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
周天勇:我国的高速增长期比应有的时间短,比如中国台湾的GDP增速在跌破8%以前,经济增长从1950年保持至1997年,长达48年,跌破8%时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14048美元,韩国则是从1960年保持到2002年,长达43年,跌破8%时,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12094美元。而我国1978年,按官方汇率人均GDP为244美元,黑市汇率为39美元,按购买力平价约为120美元左右,城市化水平仅17.9%,从1979年到2011年,8%以上的高速增长期只有33年,跌破8%时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5447美元。
我国高速增长阶段缩短存在多方面因素。首先是老龄化因计划生育而提前,人口红利提前消失,低生育水平、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需要抚养消费的人口在减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持续收缩,老年人口消费率较低,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需求增长持续放缓,甚至萎缩。
第二是,城乡二元结构对于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限制,使中国城市化水平相对工业化水平滞后很多,应当城市化的人口滞留在农村,农业劳动力过多,既压低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也减少了城市化带来的收入增长和消费需求。
第三是,同样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土地不能交易,宅基地、林地、耕地处于僵尸资产状态,生产要素无法再配置,农民无法获得财产性收入,也无法抵押贷款,资本无法下乡。这不但压低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也造成城市土地供给不足,政府饥饿卖地,推高了房价,进一步遏制了城市化的进程。
第四是,企业面对的税负、融资,运输、水电等非劳动力成本过高,造成制造业过高的成本压力,原来向内的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已经转变成向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外向产业转移。
问题之外,我们优势也很多。我们拥有工作勤奋、节俭储蓄、向往创业的国民。我们的国民教育水平已经不低,还有很大的海外留学群体,人口也没有老龄化到难以复振的程度。我国的科学研究、产业技术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后发优势仍然存在,在很多前沿领域,我们已经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而且我们还拥有大国经济的规模优势,每一个细分产业都能规模化生产经营,可以支撑起完整齐全的产业门类;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因庞大的人口基数易于发生,也因巨大的市场空间而易于成功;交通、通讯等各类基础设施因庞大的消费规模而获得小型国家难以企及的利用效率和规模优势;巨大的经济纵深,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上有更大回旋空间,劳动力、土地和资金都拥有更大的转移和再配置的空间,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记者:发展依靠改革,当前形势下应有哪些改革要点?
周天勇:如果没有特别的改革举措,我国经济增长率应该会继续延续现有的趋势,继续下行。但问题也是机遇,窒碍也是潜力,通过改革解决发展的窒碍,就会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首先是切实地减税、清费、降成本,让企业缓上一口气,得以休养生息,也避免制造业过早、过多向东南亚、向美国转移。第二是产权改革,激活各种僵尸资产。比如用永佃权把农村土地产权落实,把交易放开,把农村僵尸资产盘活,让资本可以下乡,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比如知识产权,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 50%、60%的股份归发明人,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向社会开放等等。第三是,改革户籍制度,城市的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降低房地产价格,让滞留在农村的人口得以城市化。第四是放开生育,鼓励生育。不仅是放开生育限制,还要采取有措施,把子女抚养以及各级教育的费用降下来,对冲生育意愿的下滑。
技术性的政策能够延迟,能够缓释风险,但不能化解风险,化解风险只能依靠发展,而且发展需要相当的速度,发展速度不足,风险还将继续累积。要重新提振经济发展速度,扭转经济增长下行趋势,只有依靠改革。
在当前的策略上,要保持金融形势的稳定,在防风险、降杠杆和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之间保持平衡。杠杆不降不行,用力过猛也不行,不能一刀切,在降杠杆的同时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相机决策,不断进行压力测试和政策推演,密切关注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大力推进改革。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在人口老龄化之前,我们就需要通过改革把经济增长速度推动起来,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