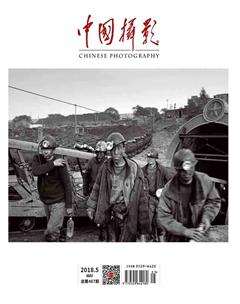三影堂,在时代的交叉口
本刊记者:你曾说,三影堂活到今天是一个奇迹。这当然是指作为民间摄影机构的三影堂这些年经历过许多困难。过去的访谈里,你对三影堂这些遇到的困难基本上都是一些抽象的、诗意的描述。但是,我想很多人与我一样很好奇,请问具体是什么样的困难能够让三影堂的存在成为“奇迹”呢?
荣荣:其实最困难的就是三影堂2007年刚开馆的那段时期,做什么事都没有什么经验。我和映里创办了三影堂。我们来自不同国家,因为摄影而结缘,三影堂最初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梦想。但是我和映里的身份是摄影家,并不是房地产商,虽然有一个情怀,但完全是感性的。我们做这样一个空间,其实超出我们个人能力。
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了,有很多艺术空间关了。在2007年,还有很多空间都是新开的;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金融危机这么猛烈,成立三影堂初期还觉得未来蛮有希望的。因为那时候中国开奥运会,国际人士来往很多,都热火朝天的。突然2008年就变得非常萧条,我们那时候随时都觉得,明天可能也面临着关门。
开馆的时候,我跟映里两个人,把我们90%以上的费用都放在这个空间里头了,包括这个空间的修建、硬件设施、第一个展览的费用,还有最初团队的搭建。我可以这么说,我们开馆后,很快资金耗空了。看起来三影堂建筑修好,只是一次性的投入,但是团队的管理、运营,包括后来每一个展览完了,还有接下来的展览,这种持续性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碰到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一直都需要资金养着。这些应该是三影堂很大的困难所在。
当时很多个晚上都在说,明天怎么办?如果熬过今夜,明天还是有阳光的,那我们就熬过今天晚上。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夜就是那么难熬,黎明也迟迟没有到来。不过还是熬过去了。就是坚持信念,这样做下来。
本刊记者:你经常把三影堂简称为“空间”。这个“空间”从北京扩展到厦门,有持续了11年的摄影奖,近几年还主办了摄影季“集美-阿尔勒”。可以说三影堂已经不是一家简单的摄影空间了。在中国的摄影生态链上,你把三影堂定位在哪一个环节上?
荣荣:这也是说为什么三影堂到今天还能存在。我觉得是它的建立好像是在中国摄影发展的时代交叉口,有无形的力量推着我们往前。其实这十几年的现状,对三影堂这种民间机构是有需求的,刚好中国摄影整个生态这个方面也是很缺失的。
我们当时对三影堂的定位不是画廊,我们是艺术中心,不以盈利为目的。首先,我作为艺术家,经营一个画廊,这不是我想要发出的声音。
其实三影堂还背负了另外一个职责:它要在中国跟国际摄影产生交流、对话。因为国际上有很多人士,包括策展人、专家、美术馆负责人到中国来,他们真的想看中国摄影当前发展的样子,三影堂无形中就扮演了联络人这个角色,我这么多年是这样感觉的。
本刊记者:为什么三影堂這十一年这么重视对外交流?
荣荣: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不是我们本土圈子里面玩的机构,而是开放的、国际性的平台。三影堂设在北京,但不能局限于北京这个圈子和国内圈子,我们一定要打破这个圈到外界去发声。但那个时候不可能马上把三影堂空间开到美国去,开到日本去,不可能空降过去,需要一步一步来。所以当下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就是让国外摄影相关的人员、国际评委到中国来。
比如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首位摄影策展人西蒙·贝克(Simon Baker),我连续三年邀请他来当三影堂摄影奖的评委,他拒绝了两年,理由就是对中国摄影不了解。到第三年他终于来了。因为我每一年都会在日本看到他,他在研究日本摄影方面非常厉害。我问他:亚洲摄影里,为什么对日本这么偏爱?他说没有办法,因为日本摄影的信息非常多。首先他了解日本摄影家,是因为日本的写真集和画册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英国传播得很好,都可以随时买到,他从摄影集了解日本的摄影生态。恰恰在中国,摄影集就很少了。比如,日本摄影师有大量的摄影集在他们国内外的图书馆,但中国摄影师的作品集在国外图书馆的情况根本比不上。作为泰特美术馆很重要的策展人,西蒙为什么对中国不了解,这样看不能怪他,怪我们自身,我们应该多做些努力。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当然没有放弃邀请他。我说,你要到中国本土来看,你想了解中国的生态,就要亲自来到中国。去年我邀请他来的,他非常高兴,他第二次来了,我给他介绍中国摄影家,不仅仅是年轻人,还有过去的摄影家,比如骆伯年。今年骆伯年的作品会在泰特展出,对我来说目的就达到了。
摄影是外来的,摄影确实在西方世界里走得比我们远,比我们快,而且得到的重视更多,我们应该有不少东西需要向人家请教和借鉴,所以像西蒙这类很有水平的策展人,我们邀请他来参与,也是很荣幸的。西蒙他们之前不了解,我请他来,来了以后我相信他自有判断。他们来到这边跟大家交流、碰撞,在心中对中国摄影有一个初步概念,未来是否再度合作,就要看他了。
本刊记者:对外合作也在经济支持上有体现吧?一个具体的案例是跟资生堂的合作,从第一届三影堂摄影奖就开始了。合作缘起是什么?资生堂作为一个商业品牌为什么选择一直和三影堂合作?
荣荣:资生堂,大家都认为它是化妆品品牌,但是它的第二代经营者福原信三就是摄影家,他办了东京写真摄影协会,很厉害的。资生堂创办后,在银座做西药,后来才慢慢有了一个实业。资生堂一直在支持艺术家,我很早有幸参与资生堂的展览,跟他们认识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资生堂第三代经营者福原义春,这个人在1980年代把资生堂引进了中国,他后面去了东京都当摄影美术馆馆长,现在退休了。2008年的时候他来了,当时看到我们的方向跟定位的时候,非常感兴趣,说:“你们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支持,但支持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每一年都支持。”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太高兴了。他们支持的费用不是很多,但是人家真的承诺的支持已经十年了,每一年他们总部的人都来。我们真的很欣慰的。关键是人家没有要求任何回报,就是有支持艺术和文化的这样一个理念。
资生堂在日本也支持很多艺术项目和展览。在日本,企业对文化机构的支持跟自己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态度对中国的企业和文化机构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个借鉴。
本刊记者:三影堂作为民间摄影艺术机构,除了像资生堂这类商业机构的支持外,有来自政府直接的资金支持吗?
荣荣:北京的三影堂以前是没有的。但是这一两年,草场地崔各庄乡文化产业的一些项目,政府开始有一些支持了。以前包括我们做的“草场地摄影季:阿尔勒在北京”这些,政府的经济支持可以说是没有的。不过我们有些项目有来自领事馆单独的支持,现在我们也在努力申请国家基金。
2015年,三影堂建立第8年的时候,实现了第一次跟政府的真正合作。当时收到我的家乡厦门集美区政府的邀请,请三影堂入驻并举办“集美-阿尔勒”摄影季。集美区有一个新城,盖了很多非常好的房子,但政府也想在城区的定位上多体现文化侧重,希望三影堂能为当地带去更多的文化内涵。到今年,“集美-阿尔勒”摄影季将要举办第四届了,这几年这个摄影季也为当地吸引了很多国际上的关注,收获了比较好的反响。
其实中国有很多城市,经济发展都很好,但是文化机构和公共空间还是非常稀缺,力量弱小,所以多一些这样的民间机构来参与城市的文化建设,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的事情。
本刊记者:具体的项目会有具体支持?
荣荣:对,单独的项目。比如说我现在要做法国的项目展览,请法国的艺术家来,我们可能就会找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处,问能不能支持这个艺术家来中国的机票,或者他在国内的住宿。
本刊记者:除了这样一些具体项目去找资金以外,平时自己自发做的涉及中国摄影的展览,这些资金怎么办?
荣荣:我们基本上快耗空了。可以说这么几年的运营,很多时候是靠我们的作品去销售,销售的收入几乎全部放到空间里来运营。有时候我自己也很难,这是自己做艺术家的收入,但因为这个空间要活,不可能给员工欠工资,团队里十几个人,人家也要租房子,也要生存,年轻人哪那么容易。对我来说,费用真是巨大的责任和压力。
本刊记者:从这些角度来说,我们注意到2016年之前三影堂是免费开放的,从2017年开始收费了,还有办会员卡之类的,是不是也需要从这方面补贴日常的运作?
荣荣:我当时开个玩笑,因为之前国家很多美术馆都要收费,我们不收费,现在国家美术馆不收费了,作为民间美术馆的我们要开始收费了。
其实最开始不收费,我的态度是让不同人群没有门槛,随时来三影堂欣赏摄影作品。因为中国摄影被更多人接纳需要引导,需要让更多人来看,我们希望做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来传播。还有我们的图书馆都是免费的,讓很多人来阅读。
但是,我们的空间一直在产生费用的,本身我们的租金也不便宜,虽然房子是我们自己盖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交租金。这个空间运营蛮贵的,而且越来越贵。三影堂很不容易到了十年,其实是值得庆幸的事情,要继续为这个空间更有计划地存活下去,就应该找到更有利的方式,包括运营和管理,都要跟市场去对接,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空间更好地存活。
本刊记者:三影堂这十一年来基本上都是做艺术摄影的展览,办三影堂摄影奖,也还是侧重于艺术方面,后面会不会有一些与商业相关的展览活动?
荣荣:我们需要,我们现在这一方面很弱。要多条腿走路,只有单条腿走路是走不远的。三影堂第五年的时候,我们开辟了另外一个空间“+3画廊”,以前三影堂从来不参加博览会的,现在“+3画廊”会代理其他艺术家进入商业博览会市场作推广。还有我们线下开设的各种课程,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了我们运营,都为了我们空间,有资本可以继续保留我们的学术品质。因为坚持学术定位,没有资金你是养不起的,你要出版一本书,你要邀请专家做论坛,你要开研讨会,你要巡展,这些东西都有巨大的费用。怎么建立良性的循环,这是我们未来应该去做的。
本刊记者:说到变化,三影堂关于作品呈现和展览本身的倾向似乎也在变化。三影堂在创立之初,表现出推动实验性摄影的鲜明姿态。最近几年,三影堂也在逐渐增加对摄影史的关注,比如2017年“中国当代摄影40年(1976-2017):三影堂10周年特展”,是在把三影堂的历程置于中国当代摄影背景下来梳理。再比如2016年三影堂编辑出版了《骆伯年》和《杨福东》的摄影集,作为中国摄影书典藏系列的前两本,似乎也是在这种并置中寻找和提示中国最当代的摄影与传统摄影之间的关联。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荣荣:从做三影堂的那一刻起,我就了解到,这么多年中国摄影有很多需要补的课,我们其实有非常好的摄影家,但我也经常说中国摄影家没有“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目前的公立博物馆、美术馆、大学、图书馆还有其他机构,对摄影艺术的关注和研究太少了。从清末、民国一直到现在,都应该得到重视。现在三影堂十一周年了,我们回头不仅仅是看十年前,还要回到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去看中国摄影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所以梳理中国摄影的脉络非常重要,我们这几年就请了比较专业的专家,比如说巫鸿老师、王璜生老师,来一起参与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有责任去做这样的梳理,不仅仅推出年轻的摄影家,还要挖掘很多被埋没的摄影家,有的摄影家,本土的公众都不知道,不要说国外的来了解了。如果自己的摄影文化都整理不清楚,你怪国外不来关注我们,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自己应该要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保护、传播。
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做,我们只是抓住了一个点,作为民间机构能力也有限,只是发出很微小的声音而已。我们所收集、整理的,会给一些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这对于未来的研究个案或者一个群体都是有利的。
本刊记者:如果今后民间摄影机构越来越多,各有各的特色,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像现在做的当代摄影发掘和推广、摄影史研究、展览、出书、论坛这些事,你觉得民间机构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荣荣:很多时候,民间的机构孤掌难鸣,中国像三影堂这样的空间有十家我都觉得不够多。现在中国真正专业的摄影机构还是太少了,上海有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今年北京又成立了光社,未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但是到最后,真正需要的还是中国专门的摄影博物馆。这不是个人能做的,需要国家的力量来做,或者北京市来做,或者其他省份来做,有市的摄影博物馆、省的摄影博物馆、国家级的摄影博物馆,这样的未来,中国摄影才能到一个新高度。
另外,当代艺术空间现在越来越多,它们把摄影纳入进去,它不会觉得这是摄影,主要觉得它们是艺术作品,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未来里头如果没有真正的摄影博物馆出现,中国摄影还是让人很尴尬的,跟国际对话,话语权还是别人定的。
这就说到了在中国,摄影春天怎么来得那么慢。从做三影堂空间到现在,国内十年盖了很多博物馆,但是摄影依然是边缘。拿画廊来说,中国的摄影画廊活得很费劲。纽约的摄影画廊为什么能活?他们画廊的作品会卖到MoMA去,卖到盖蒂去,卖到旧金山博物馆……美国有多少博物馆都有摄影的收藏,所以美国这些画廊太容易活了。但中国不管是博物馆,还是大学,都没建立起对摄影的收藏。再比如东京,早我们20年就有了摄影美术馆。现在中国经济方面不是问题,主要问题还是摄影收藏的定位和方向。
现在中国的收藏还是零散的,过去有展览,我去借作品。比如说骆伯年的作品,我都从收藏家手里面找,其实这些作品都应该是到博物馆去找。民国时期很多作品的原作都还有,但是有一个现象,1980年代、1990年代的很多作品却没有原作。我去陕西,找胡武功他们要原作,他们说没有,之前做完展览,作品都不知道哪里去了,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有的老摄影家出书,把底片给出版社了,出版社扫描完,底片不知所踪,没有还给摄影师,这也是问题。我们没有尊重底片或者相片这个物件。
我策划的展览全部要求是原作,你没有原作我没有办法纳入进来,因为我给人家看的是真品,不是复制品,是当时制作的,不是现在制作的。我希望尊重作品。中国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意识你怪不了他们,问题是我们的博物馆没有这个体系,到现在还没有。
要是今天,骆伯年的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了五张,而你手里有一张,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就像齐白石的画,博物馆里收了五幅,你有一幅,自然摄影的身价、地位就会上升了。现在中国摄影看起来繁荣,很热闹,但是其实摄影家没有“家”。他的家在哪里?就应该在博物馆。其实现在中国很多摄影家的作品在国外有被收藏,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去保护它、尊重它,这挺可惜的。
本刊记者:国外有很多大学里面都有专门的收藏室、图书馆,里面都有这些资料。
荣荣:大学里面很多,我曾经考察日本东京工艺大学,他们想请细江英公去当教授,然后细江他就提出来,我去当教授可以,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建立一个摄影的收藏部。东京工艺大学就建了,现在那个收藏部很不得了,里头有细江英公、森山大道的东西,有大量1960到1970年代的原作,都变成了学校的资产了。学生上课的时候,给他们原作看。
现在学摄影,全部在电脑上搞,看不到真东西,看到的都是復制的东西。之前鲁美的刘立宏老师带研究生来我库房,说要看一下蛋白纸工艺做的照片,我说你们鲁美没有收藏一些作品吗?他说很可惜,没有。
本刊记者:现在摄影画册多了,学校、图书馆都有。但是原作、档案资料、底片这些还是很少有人考虑捐给学校、图书馆,或者一些专门的收藏机构。
荣荣: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这个要呼吁,有的人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做一些提案往上报。我了解日本的摄影美术馆怎么形成的。一开始也不是地方政府直接说做摄影美术馆,全部是摄影家和摄影批评家发起,开会,每一次会都有记录,开了十几二十次,市里面才真正地说,可以建立一个摄影美术馆。我觉得中国有这么多的专家,他们能不能做这样的工作?必须要有一群有远见、有责任、有担当、有共识的人,才能做成。
摄影节、摄影季也是。不能像逛庙会那样,狂欢,然后完了,没有东西沉淀下来。需要留下来的是什么?是后来的人能够以此梳理摄影发展来龙去脉的东西。没有原作、没有素材,哪有中国摄影史可以写。没有这个材料,怎么下一道好菜?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摄影节,但是摄影收藏这方面还没有眉目。现在连州有一个摄影博物馆,他们每一年会有一些收藏,也很有参考意义。从零开始做,不怕晚。建立一个制度,一个规则,就是好开头。
本刊记者:你强调收藏对摄影生态的推动。2007年三影堂就做过一个名为“对流”的收藏作品展,后来“+3画廊”建起来了,现在三影堂收藏作品的状态大概怎样?
荣荣: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多收藏。建三影堂之前,我们当时也有一些收藏。后面所有资金都放到运营空间来了,我们这几年有一点点有条件的时候,会去零零星星收藏一点点,但不会很多。
本刊记者:今年是“三影堂摄影奖”第十年,这十年来,投稿的作品有哪些变与未变?是否可以反映国内当下青年一代摄影发展的某种状态?
荣荣:三影堂这个空间有点实验的性质,设立的奖项跟建立三影堂这个平台的立场是一致的。
对参赛作品的质量,最开始我们也是未知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感觉作品来的时候,质量非常参差不齐。不要说作品的内容了,单纯在作品投稿的样式和制作上就水平不一,有的特别大,有的是卷着来的,有的邮了一个小样片,作品的品质也相差十万八千里。当时我们也担心,这样做到第二年、第三年,哪有那么多新人出来?做作品哪有那么快?甚至在考虑是不是两年做一次。从第四年、第五年起,感觉作品越来越有水平了,后来就没再担心了。每年基本上保留着五六百份、六七百份的投稿量,包括去年也是。虽然没有特别多,到上千或者八九百,但这五百多份投稿的品质都更高了,有时候你要挑出20组,就很纠结,因为有一些作品确实相差不是很远。但是我们空间有限,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十年的过程中,优秀、年轻的创作者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创造力,越来越有活力。现在投稿的大部分是“80后”“90后”,还有一些海外回来的人,他们在国外学习视觉和摄影相关专业,也把稿件投到国内来了。可能你入围三影堂摄影奖时还蛮年轻的,很多人是20多岁到35岁之间,这时候他并不是很成熟,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风格后是不是还能突破自己,这是很多艺术家都在努力做的尝试。
我曾说过,三影堂摄影奖不存在的话,三影堂也就不存在了。“三影堂摄影奖”是我们最重要的品牌,或者说是我们主打的声音。很多人从三影堂摄影奖走出来了,这也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其实这个工作没有白费。对我们来说,每一个艺术家有新的成绩,他们的作品被认可,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在成长。他们成长也意味着我们在成长。
(所有图片由三影堂摄影艺术中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