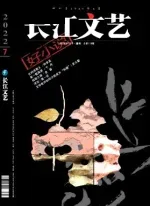四季日料
□赵 依
原刊编辑荐语
正如著名作家阿来所说,赵依这篇小说,从切身的经验出发,不躲闪,敢直面,自然就真切透彻。这样的出发点,才更正确,更为洒脱。
小说语言有着年轻知识女性特有的锐气,不拘泥,没有自我标榜和道德洗白,没有炫技和掉书袋习气,故事来自切身的痛感经验,书写笔调准确自如,人物刻画、氛围营造具有当代性,叙述节奏有着难能可贵的诚恳和分寸感,基本实现了苏东坡所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书写境界。
本篇是作家的小说处女作,得天独厚的教育背景和文学资源,以及愈挫愈奋、生机勃勃的创作态势,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是文坛一颗耀眼新星。
王秀云
一
愤怒有时无边无际。
何颜勉勉强强撑到了下班。她早早约了黄怡。但从中午开始,她就一直跟黄怡微信热络着。她跟黄怡的要好,基于一个共同的认识。当黄怡初去新职场,有同事扒底裤式地打探黄怡的一系列信息,哪一年生、毕业自哪个学校、婚否、北京买房了没、以前在哪个公司、父母在哪个城市、职业为何……最后还不忘补问一句,哦未婚,那有男朋友了吧?黄怡感到了深深的冒犯。
何颜对此的评价是,一切所谓的教育无外乎外化为两点,一是善良,二是尊重,否则可以绝交。
何颜当然也遭遇过类似情况,曾经,出版社的同事收到一封投稿信,作者是一名婚内出轨者,并在信里直陈其事,投稿一篇以此为原型的小说,这事被这名没什么职业操守的同事发在了微信朋友圈,何颜也是没事找事,向这同事提起来,意欲说明某种不妥,没料到被反问“莫不是这个作者是你?”当时,何颜正处于离婚诉讼剑拔弩张的要命状态,这么被反问,一时被激怒到不知道该如何发作,等到组织好语言想破口大骂时,那同事已经颠儿回自己的办公室了。
黄怡对此事的态度简单粗暴——恶心。
从此,两人在为人处世上便达成一致,而后又在吃喝玩乐上达成了一致。
离婚的早前,何颜被骂“泼妇”。何颜觉得“泼妇”这个词天理不容,它竟敢暗示一种将没有锋芒的性格作为女性美德的价值体系,更可恶的是,它使何颜在跟刘男的对骂中败下阵来。应当用什么词语来对刘男造成同等的杀伤力?何颜百思不得其解。
娘炮?气势不足诙谐有余。
小鸡巴?好像有些过分,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损自己的修养。以至于当战争中断,何颜企图从刚刚结束的争吵中汲取斗争经验时,她着重反思的是“泼妇”的词源问题,这使她确认了自己的变态。
黄怡认为更变态的是,她生活在北京,离她想要的生活永远可以直杠杠地量化为大于等于500万货币价值的距离,这种直接的数字化的单刀直入,确认了她比泰戈尔更能准确掌握当代一线城市异乡高知文青关于距离的通感表达。可惜,黄怡无缘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空有的户口和房票无处施展,只好把攒的钱全部在高点投到了股市,输个七七八八买房难上加难,因此就不得不固化着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半径。
何颜和黄怡都追求一些情怀和感觉,这也是她们爱吃日料的原因,居酒屋里的隔断和穿透隔断的絮叨,所有人都共享此刻的喜怒哀乐。她们不知不觉经营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想,于是在择业的时候,双双英勇就义般地选择了体面的工作和没有尊严的收入,诗和远方也就逼仄得只剩下想象。黄怡的男朋友其实可以给她一个家,这意味着黄怡的文艺生活不再动荡,她的文青气也可以安居乐业,但这使她不完全快乐。当然,何颜更是没有全然的快乐,她和刘男的这种不完全快乐,何颜觉得是她和刘男共有的变态。
“泼妇”,是刘男酒后吐的真言,这让何颜无法释怀,并且下决心永不释怀。
这一天,何颜的隐形眼镜又该换了。因为跟刘男大吵一架。在被刘男推倒在地的瞬间,何颜不争气地哭了,这一哭,花了妆,也毁了眼睛里的美瞳,好在是两周抛,也该换了,何颜心想。自打何颜跟刘男结婚,何颜更换隐形眼镜的周期开始规律起来,以前她要么是记不起来换,一戴就是一个多月;要么就是想再凑合戴戴,一戴还是一个多月。有了刘男,何颜的日子就不一样了,三天一小吵,何颜还刚烈得很,绝不低头,也不哭,到了两周必现的一次大吵,何颜大哭一场就是大概率事件,隐形眼镜也就跟着辞旧迎新。
何颜坐在奔向黄怡的出租车里,满眼飞絮,不管是杨树毛子还是柳树条子,何颜只觉得是一地鸡毛,这夹杂着沙尘的乱糟糟,跟自己的心情遥契。
平日里好的时候,何颜跟刘男浓情蜜意,彼此都觉得找到了人生的真爱、知己、灵魂伴侣。不好的时候,你说一句我怼一串,话赶话赶出了个没啥意思的功能性婚姻。
你无法告诉一个把“他妈他妈”当助词使的男人“管你妈的逼”有多伤人。
你也无法告诉一个没有生存压力的女人在外装孙子挣钱有多伟大和撮火。
这种无法诉说是何颜和刘男共同浇灌的水泥墙,不知不觉参了天。
有时候何颜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分子的牛头不对马嘴,转念一想又觉得是象牙塔的白和武士巾的红,有那么点互相厌弃又相互需要的意思,无助的时候干脆归结于命理,星座血型属相,总有一处是不大合适。
二
黄怡已经早早等在了门口,见面立刻给了何颜一个大大的拥抱。何颜知道,自己年纪还略浅几岁,但却实实在在地被当下的逼仄抹杀了二十来岁的热情活泼,尽管周围人也会安慰自己驻颜有术,美,何颜觉得更多是凄美,但愿有一天能找回有趣的灵魂,何颜暗暗许愿。
两人的聚会向来是吃什么都行,关键是聊得好。这天,何颜和黄怡点了日本锅。
黄怡说,虽然自己也是刚去,但毕竟是有资历的老人,凭什么被一个还在试用期的小年轻吆五喝六,她心底里厌恶一切不懂得尊重之道的人、事、物。
何颜开解她,至少表明你也被定义为了很年轻的新同事,往往是,自己觉得有区别,别人不一定觉得这种区别足够大。
黄怡说,要命的是,当你心里对一件事有想法,这种想法就会难以抑制地蔓延,先是到这个人,再到跟这个人有关的一切。比如,现在这个人从黄怡电脑前面的纸巾盒里默不作声地抽一张卫生纸出来,黄怡都觉得难以忍受,嗞啦的一声,扬起的白色纸巾并不如白旗,不是投降,甚至是宣战。黄怡感到每天都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峙,她的思路被打断,手指打破敲打键盘的连续性状态。
何颜说,放过自己最重要。
何颜现在每天都期待法院的开庭通知,祈求放过。然而刘男就是不放她。上一次的诉讼,刘男坚决不同意离婚,何颜只觉得何必。
何颜接过黄怡的话把儿,“当心被气出癌症”。何颜想吓吓黄怡,好让她看开点,比起自己,黄怡的情况好太多,再这么暗自生气下去,乳腺、脾、胃、肝都会受影响。
黄怡是个很惜命的姑娘,这一点何颜觉得值得敬佩。人生苦旅,仍觉珍重,其实是很坚强的。
何颜就不一样了,她热爱冒险,比如去芭堤雅高空跳伞、去蟹岛开卡丁车、去张家口夜滑,比如闪婚嫁给不甚了解的刘男……黄怡还夸她勇敢,尤其是,汶川地震那年,何颜高考,考完就进了四川重灾区映秀镇做志愿者,然后把高考志愿表填上了务虚的专业,说是要究天人之际。
黄怡呢,那段时间确实在纠结于做胃镜检查,一来是怕死,总该是要去查一查;二来还是怕死,总不敢去查上一查。
其实谁能真的健康呢?何颜坚信绝对的亚健康,身心说到底是消耗品,寿命早晚要上消费税。
突然,黄怡伸长双臂,举起手机镜头对准何颜,何颜自离婚大战打响以后就不大想拍照,害怕高清照片放大后眼底出现的细纹、害怕那两道略微加深的法令纹、害怕嘴角和苹果肌下垂……何颜不想见到自己的憔悴。
黄怡说:“我在扫脸支付,埋单了。”
分别前,何颜老实交代了,自己最近睡眠很浅,半夜里老妈去趟厕所,她就再也睡不着,想起过往从前,免不了被气得从乳腺到腋下淋巴一水的胀痛。
何颜出事以后,老妈就从杭州过来陪她住,既是安慰更是保护,何颜内心是内疚的,她还写过一首诗,有几句是:
那天晚上我哭了
于是母亲没有睡
黑夜里
她可能时不时在看
二十七岁的小女人了
还踢不踢被子
那天和那天之后的第二三天
一个母亲要捍卫她的女儿
她没有心情
梳头、泡茶、穿衣打扮
持续地思考——
黄怡也曾担心过何颜。那会儿,满是关于何颜的八卦,八卦一经发酵,有绕着弯子转了好几手打探何颜最新消息的,有甚至没见过何颜本人却开始执着于对何颜下着各种判断的,有曾经在何颜朋友圈每条必点赞的人突然不再回应她的任何发布的,有何颜认为肯定会给予自己几句鼓励问候却从头到尾装作一无所知的……何颜不哭、不说话,不真的崩溃,也不强颜欢笑,就那么照常上下班,这就是她的全部回答。后来,何颜对黄怡说,我必须坚强,我坚强了,爸妈也就心定了,只要爸妈觉得我还行,那我就真的行了。
三
北京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是农历二月初一。
何颜是先从电视上看见记者播报时的飞雪,再跑到自家窗前看见雪花飞舞的。今天正好被陈雅约去看电影,票是提前买好的,只能硬着头皮起床化妆穿衣出门。去电影院之前,何颜想先去趟银行,把这个月的按揭存了。房子是刘男住着,何颜早就搬出来租住在望京,但是房子和月供在她名下,刘男不理会,何颜也就只好扛起来。刘男知道何颜每个月也就万把块钱的收入,想用经济压力逼她就范。何颜更加看不起这男人,离婚的决心是日月可鉴。
何颜问爸妈借了钱,每月三万,何颜爸妈动了老本,卖掉了杭州的一套老房。
那套房里,住着何颜的童年和青少年,还有父母小半辈子的青春。
何颜咬紧牙根地恨着,再难,何颜也要夺回自己的生活。她要诉讼离婚,绝不协议。
何颜没想到,今天电影院会有这么多人,虽说是个周末,但是北京向来是刮风下雨生意全完,怎么今天的人会这么多,莫不是都提前买好了票?何颜开始想念小时候杭州老旧的电影院,那时候的电影票都要提前到市区唯二的剧院售票处统一排队购买,有时甚至得提前好几天去买好,只要买到票,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满满的仪式,加持着看电影当天的幸福感。
今天跟陈雅看的这部电影属于新春贺岁档,算得上精彩,何颜和陈雅全程笑个不停,水果茶热饮除了太甜以外没毛病,蛮好喝。只是何颜还会多出一些联想,这部电影的导演前段时间婚内出轨被爆料,主演更是跟自己一样经历离婚诉讼。何颜打心底里希望一切陷入婚姻泥潭的可怜虫都能力挽自己生活的狂澜,泥潭里的人就不是人了吗?
何颜喜欢电影里的一句话:杀人的不是兽,是兽性。何颜举一反三:能寒心的不是人,是人性。让人愤怒的也不是人,是人性……
陈雅很久没有恋爱了,她想找个人恋爱、结婚、过寻常日子。最近有个男的似乎有点在追她的意思,但是陈雅举棋不定尚未给出任何信号,说到底还是害怕受伤害。
何颜不发表意见,因为这个男的跟刘男同年同月生,何颜心里犯怵。
最近这个男的行动更加积极,不知道是不是跟陈雅买了房有关。
何颜觉得自己变得肤浅庸俗,这就是刘男带给她的,心里有屎,看一切都是屎,去他妈的。
这次换到电影院楼上新开的日料店吃饭,新店开张,大概是有什么员工奖励制度,递来菜单的服务员小妹一个劲儿地推销,光是姜丝可乐,何颜跟陈雅就点了四杯,初雪天喝这款没什么奇怪,但是在日料店喝就有点奇葩了。
曾经,何颜也是一个发明用紫菜包新鲜海胆吃的小姑娘,也是一个既喝得出大吟酿顺滑度,又讲究杯子制造的小文青,现在喝着滚烫的姜丝可乐,何颜怀疑自己曾经的行为是不是在装逼。
何颜先把陈雅送回家,再自己打车回家,车上,何颜给陈雅的朋友圈点了赞,照片是何颜拍的。
不知道为什么,何颜总是愿意多照顾陈雅一些,没准儿,是陈雅遇到的这个跟刘男八字有些相似的男人激起了何颜的过度保护欲。
四
北京暖冬,无雪,甚至上了新闻和微博热搜。
吃了日本海鲜泡饭出来,何颜忍不住大吸几口东三环上空灰黄色的雾霾,跟饭后烟似的过瘾。
身边挽着自己的姑娘戴着防霾口罩,口罩的边缘跟脸严丝合缝,鼻梁两侧的肉被硬是夹得凹陷下去两块,稍作合理推演,口罩下面应当是一团糊掉的粉底、腮红和唇釉,这样可怕的口罩何颜是不会戴的。
从团结湖到望京,两个人酒后偏偏倒倒地沿着东三环走,何颜以为路是笔直的。走过农展馆、走过燕莎,何颜跟这个姑娘就这么走着,也不是真的就打算这么走回望京。只是此刻,一切光源的光晕都和雾霾扭作一团,也不是能见度受了什么大的影响,就是觉得魔幻,好似行走在别处。姑娘是路痴,却喜欢拽着人走,何颜以为她认得路,也就甘愿被带着,直到在某个辅路口被带歪了方向,偏离了环路,跟她的生活一模一样。
“要不……打车吧?”姑娘轻轻地、有些提心吊胆地向灰黄里发问。“好。”何颜掏出手机开始定位打车,她并不是不能接受跑偏,为什么要把她想成那样,至于么,胆战心惊地发问,我又不是什么母夜叉。
第二天,何颜已经不记得自己跟谁吃了饭,她唯有的印象是自己在上车的几分钟之后就到了家门口,或许真的是沿着东三环走了很远,可惜自己退出了微信运动,具体步数也就不得而知。
何颜想起老妈的一个习惯,没啥事的时候,老妈喜欢摇几分钟手机,说是增加点微信运动的步数,何颜说,“妈,这排行榜没啥用,别费劲了。”老妈回何颜说,“我得让人知道,我在北京也是每天出门溜达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要不然我那些同学总问,北京气候不好的啦,生活又不如杭州舒服,还要讲正宗普通话的,你待在北京是为什么呢?”这让何颜感到万箭穿心,五味杂陈得说不出一个字。
何颜从枕头下抽出手机,今天是“三一五”,不知道又有哪些牌子让人以后都不敢再买了,晚点关注一下新闻。突然,何颜想起来,这么说来,昨天还是白色情人节……那么昨天自己到底跟谁在东三环上谈了一场恋爱?那个姑娘是谁?是黄怡?又或许,那个姑娘不存在,又或者,自己跟黄怡其实是同一个人。
五
何颜觉得,这顿饭可能不是她跟黄怡一起吃的。
最初接到章辛的邀约时,何颜有点意外,似熟非熟的前同事,莫非有什么业务要谈?何颜一直觉得章辛像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喜剧演员,因为章辛的生活一切都好,可在一切都好的时候,章辛依然悲伤。三里屯的日料店很多,这一家的门帘很隐蔽。当章辛在微信里把店面的链接甩给何颜时,只问了一句,“要打一个野招呼吗?”何颜有点惊喜,呵,这不熟装熟的本事……为什么不呢?
盛夏酷晒,章辛提前等在三里屯著名的优衣库旗舰店前面,何颜对自己的迟到感到抱歉,但她不想早到。
何颜注意到一个细节,章辛喝酒的时候,含混一口,闭眼,慢咽,像享受,也像受了什么刺激。
章辛出生那一年,父亲在街上被拍到给大学生送水,回单位立刻受了处分,当时章辛的母亲怀着章辛,差点躲回老家所在的地级市生产,好在,不是什么大错误,章辛一家的生活很快复归平静。只不过,章辛的父亲一辈子郁郁不得志,母亲则出于各种原因对父亲报以不满,其中也恨父亲的无能。
章辛恨透了告密者,曾经章辛也看过一张照片,四合院里,一群年轻人,有自行车也有布幅,告密者围坐中间,仿佛是这幼稚理想中的一员。
始料未及的是,二十多年后的章辛又因为一顿饭被告了密。
章辛属于典型的自命不凡又活得循规蹈矩的那一类人,考公务员进了部委,业余也炒比特币挖矿,北京一限购就买了房摇了车号,但可能雄心壮志敌不过时运不济,房子买了昌平的商住loft,空有环境没有涨幅。比特币一跌再跌,加上矿机迅速更新换代,折旧贬值的成本损耗加上放置机器的这套近郊三居室的月供,章辛不得不动用女友的存款。车倒是买了,车号也是女友摇上的,借了人家的钱和运气就得对人家负责,本来打算结婚了,但是部委按资排辈,迟迟不给这个年轻人分一套市区的小房子,就连配租房也得按工龄排下来登记,章辛索性转考到文化单位做行政,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何颜。但马上,章辛就发现自己无法对接这里的复杂关系,一狠心辞去公职去企业干了,也不知道是想得明白还是想不明白。
不管怎样,从大面上来看,何颜觉得章辛的日子在北京已经是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于这样的章辛的突然邀约,何颜觉得他只不过是需要生活里随便别的什么元素陪他待上一会儿,无非是心中生出一些人皆有之的倦怠,何颜之所以出现在此情此景,大概是章辛在划拉通讯录的时候,何颜比较靠前。
何颜至今记得,当初章辛辞职的时候,发了一条微言大义的朋友圈,图文并茂,得罪了不少人,何颜一如既往地点了赞。
这顿饭过后不久,就有朋友圈的索引派发现何颜跟章辛一起吃了饭,各色消息随后不胫而走,先是传到了章辛的公司社交圈,又不知怎地传到了刘男那里,刘男一举打到何颜单位,说这女人出了轨,他不离婚,要离婚就要给他房。
何颜觉得可笑,自己跟刘男是秋天才认识的,即便这场婚姻是对赌,结果双输,赔得也该公平。
只要是公平的,何颜都认,这也是何颜坚决要诉讼刘男的原因,尊严无价,傻逼。
但是文化单位的人都具备虚构的能力,有说章辛跟何颜在以前单位就一直相好;有说何颜怀过章辛的孩子,后来流了;有说何颜一直刷章辛的信用卡,后来章辛还不上,被女友发现了……小说作者不计其数,何颜也就完全不在乎,权当自己是当代的萧红,虽然的确是自视过高了,可如今唯有虚妄能陪自己度日,何颜少不了也在心里咒骂:原地爆炸吧,不善良的人类。
之所以说原生家庭重要呢,章辛最后还是跟他那个爸一样认,干脆辞职逃离,以为这样就获得了重生,有人说这叫默认。
何颜鄙视章辛,呸,孬种。
何颜觉得以讹传讹的人都是智障,自己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货。
何颜对周遭的愤怒来自他们对自己眼光的怀疑,这让何颜觉得被矮化,刚烈的何颜爱上的只会是枭雄,尽管她也遇人不淑。
六
当何颜怒气冲冲地替黄怡给那个小年轻一个耳光的时候,何颜就料到这件事会传回到出版社。
何颜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处处设法周全别人的何颜了,她不想再刻意地关心别人,反正别人也从来没有为她设身处地去想过,她只想守住自己生活里仅存的美好。
何颜替黄怡出气,实际上也捎带手地为自己杀鸡儆猴了一把,她也给自己做足了心理建设,出版社的同事再出言不逊,她也扇他们。
何颜想不明白,黄怡单位的这个小年轻,是出于什么心理和目的给黄怡微信发送了那样一个粉红色的生殖器插嘴的表情,这是不尊重女性、是侮辱、是性骚扰,令人作呕,何颜表态此事不能放任不管,得让他知道底线。
何颜拿着黄怡的手机质问这个小年轻时,小年轻小眼一斜,揶揄她:“呵,你们这些更年期老阿姨看得懂这个表情是什么吗?”
何颜回了一句:“看得懂,是你没有的东西。”然后何颜当众赏给他一记响亮的教训。
这天回家路上,何颜重新做了指甲,是干干净净的裸色。
何颜的义举似乎吓坏了黄怡。
事后,黄怡在微信上简单跟何颜打哈哈了几句,一直到春天快要结束,也没再主动约过何颜见面吃日料。
何颜开始觉得黄怡跟自己一点也不像,忍不住开始做全盘式的否定,然后在心里一点点切割、疗愈……
何颜想过自己的结局,要么刘男坚决不同意离婚,她一诉再诉再再诉,拖到人老珠黄离掉这个婚,成为小年轻口中的老阿姨单过一辈子;要么下次开庭刘男同意离婚,但前提是何颜得做出退让,把房子让给他。
何颜很想解脱,但她是不会放弃财产的,放弃财产就等于放弃尊严,她没做错任何事,受伤的尊严应当得到赔偿,并且怎么赔偿都不为过。
何颜也想过干脆把刘男杀了,她不是做不出来。只是转念又想,这样一来跟章辛有什么区别,胆小懦弱太不入流,连为沉冤昭雪付出的勇气都没有。
想来想去,只有一种结局,何颜是不能接受的,就是刘男把自己杀了。毕竟,何颜还想学习如何把无边无际的愤怒归于虚空,还有好多家新开的日料店没有吃到。
何颜以前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得出的不可被接受的结局有二,一是被杀,二是被破相。破相之所以变得可以被接受,是某天下班何颜按开电梯时碰见一个熟人,熟人刚刚遭遇分手,眼底有厚重的黑眼圈,手里抱了一大沓刚出的杂志,挤给何颜的笑容实在是过于僵硬,何颜其实觉得他不用冲自己笑的。
出了大楼何颜上车前,熟人说了句:特殊时期,你可面容略显憔悴了啊,注意休息。
何颜开始佩服起像黄怡一样惜命的自己,在手机备忘录上写下一句:愤怒有时无边无际,然,不亦快哉。
同时,给熟人发了条微信:下周二,去吃日料吧。
选自《北京文学》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