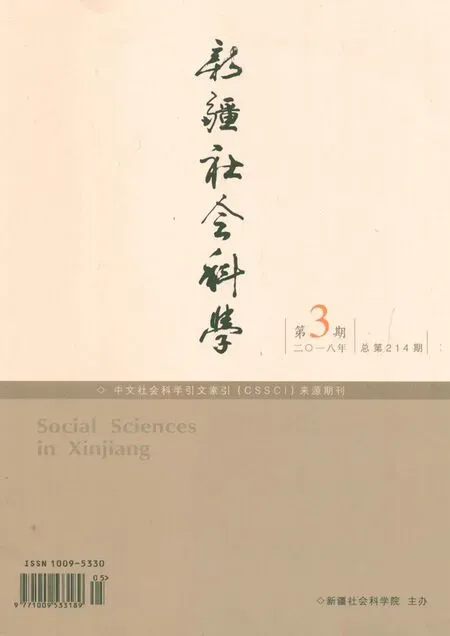Nation及“国族一体”论
潘志平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Nation,经常译作“民族”,它却表现有 “国家”或“国民”之义,如联合国是Nation的联合。在讨论问题和表述观点、立场时,应将Nation与ethnos(族裔)、ethnic group(族群)认真区分开来。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是包罗了各种历史形态和各种层次的人们共同体,实际上主要有两个概念:“国族”(Nation)和作为族裔的“少数民族”,在国际交流时不妨写作MINZU。问题是,如果将“族裔”为内涵的少数民族与“国族”为内涵的Nation,混为一谈,那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分裂的严重挑战。“一族一国”,如强调一个族裔(或族群)一个国,那就有对拥有多族裔(或多族群)国家的分裂企图。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国族”(Nation),理所当然;反之,一个国家弄出多个“国族”,那就有可能因此走向国家的分裂,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如苏联搞出15个“国族”( Нация),最终在合适时机就分裂成15个国家。在中国,中华民族就是“中华nation”,将中华民族与汉族、中国人与汉人划等号,不是大汉族情节、就是小中国观念,不足以训。我们现在说的“五个认同”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就是中华国族的“一体论”、就是对多元一体的“中华nation”的高度认同。须再三强调,这里的“中华nation”不是汉族,而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全中国“国民”。作为“族裔”(ethnic)成员对自己“民族”的热爱,无可厚非,但对它的认同不能高于对“中华nation”的认同,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意义重大。
Nation是近代出现的政治术语。法国大学者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著名学术讲演《Nation是什么?》*Ernest Renan,Qu'est-ce qu'une nation?Le mot et les reste,Marseille,2007,pp.17-36.非常精彩,震动欧洲学术界,1929年即被介绍到中国,近年又有两个新版译文问世:一是袁剑先生译自英文的,译题为《民族是什么?》;*袁剑:《民族是什么?》,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丛书》第10辑——《何种文明?中国崛起的再思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7~152页。一是陈玉瑶先生译自法文的,译题为:《国族是什么?》。*〔法〕厄内斯特·勒南:《国族是什么?》,陈玉瑶,译,《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Nation在这里分别对译成“民族”“国族”,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这真还不是新问题。尽管勒南的《Nation是什么?》最初发表于1882年,许纪霖先生主编《何种文明?中国崛起的再思考》时却将此文列入“西学前沿”栏。
近年,关于Nation是国族还是民族的讨论、特别是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树立国家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后,学术界就“国族”和“国族一体论”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朱维群:《更多强调中华民族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凤凰网》第25期,2014年4月2日;马戎:《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问答与讨论》,《民族社会学通讯》第152期,2014年1月31日;范可:《信任、认同与“他者”——关于族群、民族的一些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熊芳亮:《“国族—宗族”论》,《中国民族报》2012年12月14日;郝时远、朱伦、常士訚、彭萍萍:《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国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政治发展理论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陈建樾:《国族观念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基于近代中国的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高翠莲:《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意识与国族主义的互动》,《原道》2010年第00期;胡鞍钢、胡联合:《中国梦的基石是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4期;张健:《国族与国族构建研究述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邸永君:《加强对“中华国族”的核心认同》,《理论视野》2010年第6期;张永红、刘德一:《试论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fication)和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纳日碧力戈:《以名辅实和以实证名》,《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3期;林炜等:《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建设》,《红旗文稿》2015年第11期;明浩:《国族和民族的区别》http://blog.sina.com.cn/s/ blog_5ed4dbd70102vk4z.html,2015-07-22,等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现自己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Nation是什么?
众所周知,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实际上,当年在欧洲徘徊的还有另一个幽灵——民族主义的幽灵。如伯里(J.P.T.Bury)所论:nationalism事业在1815年还很少为人注意,但在1830~1870年,有人一再鼓吹和散播这些基本概念和特征,其效果之大,使得欧洲的政治思想起了变化,欧洲的地图也大为改观。nationality已经获得巨大成功,尽管人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许因为他们并不明白它的含意。这个词的含意并不仅指nation,还指一个nation即使在失去自由之后仍能藉以继续存在的某种东西。从那以后,政治学家们一直试图阐明这个词的具体定义。正因为它含糊不清,所以nationality才这样受欢迎:每一位理论家、每一个政党、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任意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塞进去,以证明自己的某些愿望是合理的。不论强调的是什么,反正nationality出现了,且很快就充满了感情的内容;而且和它的姐妹词nation和nationalism都包含着一种具有无限潜能的推动力。这个统治阶层在1815年大都不能接受的原则,到了1860年已为多数统治阶层所支持或不得不予以考虑了。英国一位重要的政论家约翰·斯坦图尔特·穆勒就声称:一般地说,各国政府统治的界限大致应与各个nationality居住界限一致,这是自由的必要条件。*《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陈厚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7~289页。
那么Nation究竟是什么?勒南坚决认为,Nation不是种族、语言、宗教、地理,洋洋洒洒一大篇,很有见地。但他把Nation定义为: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 ,一个思想健康、古道热肠的大型人类聚合体,这有点让人不知所云。然而,自此以后,世界各国开始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Nation一词。*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页。Nation意味着与全新的现代国家相联系,它是在一个现代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下的全体“国民”,在这里“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如同钱币的正反两面,是一体的,在这个意义上,Nation 就是“国族”,而不是血缘文化相联系的族裔。现代国家Nation-State取代了古典的王朝帝国、部族汗国,这不能不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此,我希望重温一下恩格斯当年的看法。1866年,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一文中说:
“每一个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自由主义呢?不过,请注意,——现在说的已经不是Nations,而是Nationalities了。”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peoples的残余叫做nation,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nation。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nationalites的自然分界线,即与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许多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法语;同样,德国境外也有许多人,他们说的是德语,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nation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nation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people的民族生活,已经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es)同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关于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的旧论点之间,是有差别的。‘民族原则’完全不触及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民族(peoples)的民族生存权利这个大问题,如果说它也触及的话,那也只是为了混淆问题。”
恩格斯认定的是:
(1)nation与nationality、 people不容混淆。
(2)所谓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es)与Nation有分离的独立生存权利的旧论点,不容混淆。
在当代nationality常作“国籍”之意,但须特别注意恩格斯的语境,即恩格斯所谓的nationality ,具体指的是苏格兰山区和法国布列塔尼亚的克尔特人,操芬兰语的马扎尔人,威尔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犹太人,以及近一打的斯拉夫部落。只要认真考察一下,恩格斯所谓的nationality与nation(国族)不同义,也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籍、国民身份、国民素质等含义,而大体上是以血缘文化为内涵的“族裔”或“族群”。作为政治家的恩格斯虽不是民族人类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如马戎先生指出的:“恩格斯一如既往明确地把民族分为‘有生命力的’和‘缺乏生命力的’两组,后者不应当享有与前者同样的‘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那种认为两者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和同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的‘民族原则’,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那些‘没有生命力’、竞争失败并沦为‘反动民族’的群体,应当‘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恩格斯,1849b:342)。到了1913年,列宁在讨论俄国国内的民族问题时才明确提出‘民族平等’的提法,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转折。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的立场和观点与后来斯大林奠定的苏联民族理论之间具有原则性的差别。今天的人们完全可以不同意恩格斯的观点,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斥之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宣传以及对弱势民族文明传统和生存权利的漠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在讨论民族问题时绝对不应当回避恩格斯的这些观点,而且应当认真地思考他所坚持的这些观点背后的道理。”参见马戎:《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中国学术》第32辑(2012年12月)、《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128期(2013年1月31日)。但他这里特别强调的,以国族为内涵的nation、与以血缘文化为内涵的族裔,必须严格区分,虽然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言句句为“真理”,但我认为恩格斯的这一认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Nation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也就是斯大林认真做过回答,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斯大林定义。俄语中的Нация大体相当于英语中的Nation。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定义排除了“血缘”联系,正如,宁骚先生指出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把血缘联系排除在民族特征之外,是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大进展”*宁骚:《民族与国家》,第17页。。我认为,宁骚先生这一认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据此,可以认为,斯大林关于Нация的定义明显带有政治实体的含义,表达的是现代政治范畴的“国族”之意。斯大林的定义言之凿凿地强调:它“是一个在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第34页。。如此说来,近代中国之前,连汉族都不是“民族”而是“部族”,这是许多中国人无法接受的。*这曾是国内学术界最具争议的议题。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牙含章、孙青:《建国以来民族理论战线的一场论战——从民族形成问题谈起》,《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蔡美彪:《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讨论》,《科学通报》1955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张建军:《斯大林民族定义与汉民族形成》,《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1期。其实,问题还是在斯大林所谓的нация指称的是现代政治范畴的“国族”,而不是具有历史和血缘意义上的“族群”或“族裔”。如果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因此而过于困惑了。同样,列宁、斯大林既不是民族人类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如最近的研究表明,他们经常将нация(nation)、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nationality)、народ(people) 当作同义词使用,*⑤⑦ 何俊芳等:《俄语“民族”(нация)概念的内涵及其争论》,《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这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不能以此苛求列宁和斯大林,毕竟列宁、斯大林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而提出民族平等的观念;斯大林定义尽管不断受到质疑,但它还是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出重大贡献。此外,研究表明,苏联政界和学术界长期以来将“этнонация”(族裔民族)混同于нация,⑤这是事实;直至苏联解体后,著名的民族学家季什科夫教授认真地分析了нация(nation)和этнос(ethnos)的差别,一度被指责为否定一切民族、民族共同体的“病态的后现代主义”*季什科夫:《民族政治学论集》,高永久,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何俊芳先生研究的结论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已逐渐形成了把“нация”理解为“гражанская нация”(公民民族)和“этнонация”(族裔民族)两种内涵并存的话语体系。但从原苏联范围内发表的论著看,在传统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的人至今还占多数,因此,要完全把“民族”的内涵从族裔民族转向公民民族理解,还需要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⑦
nation(нация),属于现代政治范畴,与历史文化范畴的、甚至有生物性和文化性的“族裔”“族群”,本就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而至今经常被混为一谈,这是不是受到苏联学术界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MINZU
有学者认为,汉语“民族”一词源于19世纪用来对译西文的日文汉字,甚至认为是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黄晓峰:《姚大力谈民族与民族主义》,《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8月22日; 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21世纪》2003年6月号。。但另有学者以为,在1500年间,出现在汉文文献里并代代相传的汉语“民族”概念形成了一条古籍链。*龚永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郝时远先生以大量文献证明:“民族”一词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固有的名词,他同时指出,“‘民族’一词在日译西方著作中明确对应了volk、ethnos和nation等词语的定义及其有关理论”*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在中国、严格地说在中国大陆,“民族”是有着丰富涵义的术语,它既可谓“中华民族”,也可谓汉、藏、蒙古、维吾尔等文化高度发展的现代族体,还可谓滞于封建甚至更早期的族体;甚至还可谓历史上早已消失的部族,如匈奴、突厥、契丹等。用龚永辉先生的话说:“无论我国的‘例外’还是他国的‘例外’,各种历史形态和各种层次的‘民族’都是民族。”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民族”是包罗了各种历史形态和各种层次的人们共同体。因此,不少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的“民族”,在国际交流时不妨写作MINZU。*〔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来仪:《也谈我国的“民族”概念及其学术争论》,《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4年。
但说来说去,在汉语中MINZU主要有两类概念,如日本学者所说的:一是相当于西语系中的“国民”(nation),具体指有中国籍的“中华民族”;一是指少数民族,如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等。*〔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惠,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3页。其实,在中国、至少在中国大陆语境下,说到“民族”,如一位民族问题专家所言,就是被“普遍地、约定俗成地理解为生物性和文化性的人们共同体”*⑦ 都永哠:《华夏—汉族,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1期。。当然,这种“约定俗成”说准确不准确,则是另一个问题。
那么,MINZU如何定义,原先采用的斯大林四要素定义说不清、道不明。2005年,有中国特色的MINZU终于有了官方最权威的定义:“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9页。这一定义被认为终于将中国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和社会形态高低的人们共同体“一网打尽”,被称颂为古今中外都适合的定义。*龚永辉先生认为:它“涵盖了中华本土与世界各地多形态、多层面族体的基本特征”。参见龚永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但是,这一定义不再将“共同地域”作为民族定义的要素,而强调种种民族性特征,终究将其内涵止于生物性和文化性的“族裔”或“族群”,而无法包容具有现代国家或“国族”涵义的nation。
须注意,“中华民族”的“民族”和“56个民族”的“民族”,都是“MINZU”,由此可能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果将“族裔”为内涵的少数民族与“国族”为内涵的Nation混为一谈,那中国不得不面对分裂的严重挑战;二是,担忧“如果与生物性、文化性的‘民族’相联系容易引起少数民族成员误读,以为‘中华民族’就是指汉族,或者提‘中华民族’就是要同化少数民族”⑦,这是一些少数民族群体不安之所在。
出于前者考虑,马戎提出:“‘中华民族’的称呼不变,以便与英文的‘Chinese nation’相对应,而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ethnic group)”*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此议一出,即面对着许多反对声,但实际上可以看到,近年愈来愈多的学者在适当场合中借用“族群”或“族裔”概念讨论问题,似乎可以谈清楚许多复杂问题。出于后者考虑,也有学者建议:用复数的“中华各民族”,或在其他场合放弃使用“中华民族”而启用“中华人民”。*都永哠:《华夏—汉族,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令人奇怪的是,此说不知为何没引起关注?!为了纠结于生物性和文化性的“民族”(MINZU),就可以不要“中华民族”?!难道不值得认真地讨论一下?!我很怀疑,这是否是一不小心说出不要中华民族的话正是一些人想说又不敢说出的话?!
三、国族、Nation与State
按照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观点:“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national)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请注意,在盖尔纳那里,national和ethnic,似乎是同义的。无论如何,“一族一国”论成为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要求。问题在于,用族裔(ethnic)混同、取代国族(nation),在多民族(族裔)的国家里,以族裔为边界推动民族国家的建立,那就是民族分裂主义(ethnic sparatism)。
1999年,我就提出:由nation的“国家、民族一体”理论派生出来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在当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迷恋于“独立”,打的就是“民族自决权”牌;而一些多民族国家政府拒不承认多民族现实,执意搞单一民族国家,打的是“民族国家”的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方面的冲突和对抗竟根源于同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nation的国家、民族一体的理论。当今全球性民族分离主义既受到西方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es)激励,又受到封闭、狭隘、排他的民族情绪的鼓舞,是对当代政治的反动。当前,首先应批判、摈除貌似公理的Nation的“国家、民族一体”理论,以驱除民族理论上的种种迷雾。*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以上认识提出已十多年了,但我始终觉得好象有些问题,现认真反思,我原先之提议还需再斟酌。因为,Nation作为现代意义上“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强调的是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不宜简单地否定。而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正是“国家”(State)的基本特征,因此,Nation确切的含义为“国族”,或“国家”“国民”,可能更适合;而在一些场合下将Nation硬对译为“民族”,则不甚达意。如众所周知,联合国(United Nations)是Nation的联合。
然而,Nation毕竟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一刀切地作“国族”,也有麻烦。比如,Nation-State如果译成“国族国家”有叠床架屋之嫌,而经常被译成“民族国家”,也有译成“国民国家”的提议。*朱伦:《走出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的误区》,《世界民族》2000年第2期。再如,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说:
Four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e continent a new nation.
〔87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nation)。〕
文中的“nation”,既不能作“民族”,也不宜作“国族”,还是作“国家”为宜。
同样,我们天天说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中华nation”,说成“中华国族”,理虽不错,但说起来却有点拗口。
问题是如何认识“一族一国”论或“一国一族”论?
“一族一国”,如强调一个族裔(或族群)一个国,那就有对拥有多族裔(或多族群)国家的分裂企图;“一国一族”,如强调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国族”(Nation),理所当然。反之,一个国家弄出多个“国族”,国家就有走向分裂的可能。这里说的是“可能”,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可能”就会“合理合法”地变成现实,如苏联当初搞出15个“国族”( Нация),最终在合适时机就分裂成15个国家。
或以为,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就有多“国族”(Nation)并存的,并没有必然导致民族分裂问题。此说未妥,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多“国族”(Nation)并存,不一定立马分裂,但在合适的时机则有可能走向分裂,魁北克和苏格兰要求分离的“公投”不是没有搞过,还真让加拿大和英国当局吓了一大跳。多年来,一直有个小团体——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简称UNPO,为“没有国家的民族组织”),号称“小联合国”,实际上就是那些自称Nation的独立分子俱乐部。藏独、台独(台湾“民进党”)、“东突”都曾是这个小团体的积极成员,世维会的首任主席艾尔肯曾出任这个小团体的秘书长。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如库尔德人、车臣人、俾路支人、巴斯克人、魁北克人、苏格兰人、科西嘉人的一些组织,眼下或许没什么力量,但没有力量不等于没有想法,若有适当时机就可能搞出大动作,×× Nation,就是其独立的旗号。
四、国族一体论
2002年,我在完成一项国家课题的过程中发现,“东突”分裂主义的核心思想集中体现为如下三段论,即: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发现其分裂中国最大的障碍在于,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如果说,有什么“国族一体论”,那么,“五个认同”之一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国族一体论”。这里再三强调的是:
一是,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中华nation的认同。
二是,中华nation,不是汉族,而是56个民族的总和,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的全体国民、公民。这56个“民族”,是什么呢?是“族裔”“族群”“族体”,或者是表现为族裔内涵的“民族”,但就不是nation。
三是,作为一个族裔(ethnos)成员对自己族裔认同,即对于本族裔的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无比热爱,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认同不能高于或取代国家层次的认同,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认同必须高于族裔认同。
如此的“国族一体论”,又有什么错?!
再谈谈苏联的教训,一个苏联15个нация(nation),从法理上看,这既是苏联成立的理由,也是苏联解体成15个国家的滥觞。最新研究揭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季什科夫等人力主将Нация重新界定为“公民的”,而不是“族裔的”,也就是让Нация回归政治共同体和公民共同体。俄罗斯最近的官方文件将俄联邦“多民族人民”(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народ)界定为俄罗斯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普京则明确说:160多个俄罗斯人民(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是统一的民族(единая нация)。*何俊芳等:《俄语“民族”(нация)概念的内涵及其争论》。俄罗斯当今的国族一体论,实际上是对苏联解体反思后的产物,值得深思。
五、“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当然,在内地,特别是很少见到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甚至没有什么概念的地方,有些自以为是地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有意无意地将少数民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的一些观念和意识,可以看作是大汉族情节和意识。这些情节和意识对于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是有害的,需要的是教育、再教育。至于伊力哈木之流以此宣称,我不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就不是中国人,正暴露其分裂的本质,那就是另一回事。
其实,在欧美,包括俄罗斯,习惯地以为中国是汉人的民族国家,汉人与中国人是划等号的,而非汉人就不是中国人,英文和俄文中的Chinese和Китаец,即中国人和汉人之义。比如,米华德(J.A.Millward))就认真地使用“汉人”(Han Chinese)和“非汉”(No-Han)、“汉移民的殖民统治”(Colonial settment by Han Chinese immigrants)之类的观念和说法。*S.Frederick Starr,Xinjiang:China's Musliim Bordeland,M.E.Sharpe,NewYork~London,2003,p.62.
如果说,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表现在国内,应该是有些“大汉族”情节,严重点就有大汉族主义之嫌疑;那么,在外方人士那里,顽固地认定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就仅限于汉人之居地,那就是“小中国”观念,居心未免叵测。想当年(1939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之时,国内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马戎先生对于这一讨论有最详尽的分析,参见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顾颉刚先生指出:“外人称我们的满洲为Manchuria,称滿人为Manchus,称蒙古为Mongolia,称蒙人为Mongolian,称新疆为East Turkistan,称回民为Mohammadans,而称我们的18省为China Proper,称汉人Chinese,简直把我国裂成五国,而屏满蒙回藏于中国之外!”*顾颉刚:《续论“中华民国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1939年5月8日、《边疆周刊》第20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先生疾呼:“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顾颉刚:《中华民国是一个》,《益世报》1939年5月8日、《边疆周刊》第9期。顾颉刚先生之论引起广泛讨论:有极力赞成的,如张维华、白寿彝、马毅先生等;有保留地支持的,如傅斯年先生;*傅斯年先生虽未直接参与论战,但在致朱家骅等信件中表示:“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即谓不要分汉、满、蒙、回、藏、苗、瑶、猓猓等),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惟一之立场”(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编:《傅斯年遗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14~1017页,转自马戎主编:《民族社会学通讯》第122期, 第48页)。也有质疑的,如费孝通、翦伯赞先生。现在看来,顾颉刚先生之论固然可贵,但也有粗疏之处,*后来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提出“中华民族宗支论”,可能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参见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讨论》,第3页。现有评论指出:“在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费孝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顾颉刚则强调了它的一体性。顾颉刚为了强调一体性而否定了多民族之存在,使其理论带有严重的缺陷,但他对一体性的认识和论证,对费孝通以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还是有意义的”*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这一评价比较中肯。
我还想提请注意的是,1944年,麦斯武德、伊敏、艾沙操控的“东突厥斯坦(新疆)同乡会”*该会对内称“东突厥斯坦同乡会”,对外则称“新疆同乡会”。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宪法修正之意见》中说道:
中华民国建国之初,即以五族共和相号召,则中华民国并非单一民族所组成至为明显。茲五五宪章*由国民党中央审查和蒋中正批准,于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五五宪章》。第五条有“中华国族”之说,百思不得其意义,甚滋疑虑。倘承认国内各小民族之永久存在, 则中华国族之说不能成立。……因中华国族之定义,至难捉摸也。总理在为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昭示,民族构成之条件,须具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及风俗习惯五种力量,突厥民族,据此五种条件,无不具备,与国内其他民族共建民国,一律平等,绝无愧色。*《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大公报》1944年10月13日、《阿尔泰月刊》1944年第2期。
此《意见》一经公诸于世,便立即受到史学大家黎东方先生的批驳。1944年冬,黎东方与伊敏在《中央日报》上展开了关于“突厥民族大论战”。*《中央日报》:10月14日,黎东方:《新疆省同胞是突厥吗?》;10月31日,伊敏:《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11月3日,黎东方:《再论新疆省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民族,新疆省不应称为突厥斯坦》;11月24日,伊敏:《再论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突厥斯坦人就是突厥人)。亦可见《阿尔泰月刊》1944年第2期。看来,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力斥“中华国族”,以族裔混同于国族,其要害就是要制造一个可以独立建国的“突厥nation”。
现在看来,国共两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有同有异。如日本学者所说:“国民党认为的‘中华民族’是汉化为汉族的全体。中国共产党所认为的‘民族’是要承认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基础上的存在和多元性的基础上,将其集合体称为‘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境内的所有人这一点上,两者是共同的。”*〔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第20页。抛开党派之异见,中国共产党的“中华多元一体”的理论构建,力排大汉族情节,追求56个民族平等共荣,既符合时代精神又契合各民族民心,更为可取。如学者所赞誉的:“在承认民族多样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体,这是一种充满自信的高度政治智慧。”*郝时远:《中国民族政策并非“技不如人”》,《环球时报》2015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