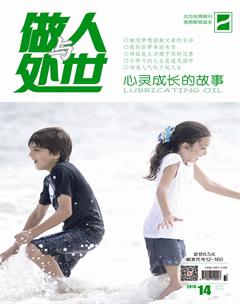名家的第一笔稿费
郑泽琼 陈卫华
1.沈从文:5毛钱的购书券燃起写作谋生的希望
从湘西山区走出的沈从文,在长期的打闹和逃课中勉强读完小学,16岁便因家道中落而辍学,加入地方部队行军打仗。无数次目睹杀人和被杀的血腥场景,使他愈来愈厌倦行伍生涯。1923年,21岁的沈从文彻底离开部队,辗转到京城开始了艰难的“北漂”生活。他租住在破旧发霉的小屋里,一面在大学当旁听生,一面写文章四处投稿。但寄出的文章如石沉大海,到后来连吃饭都成问题。在绝望中,他给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郁达夫接信来到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看他。见沈从文在冬天还身着单衣,郁达夫便将自己的羊毛围巾解下来披在沈从文身上,又带他到餐馆吃了一顿饱饭,还将结账后剩下的3块多钱留给了沈从文。这才暂时解决沈从文的生存之虞。
1924年12月,沈从文的第一篇作品在《晨报》刊出,并得到了第一笔“稿费”——5毛钱的购书券。沈从文本来已经打算年底去“照相底板学校”做学徒,这下看到了以写作谋生的可能性。此后,沈从文接连出版了几部小说集,获取了丰厚的稿酬,走上了职业作家之路,到20世纪30年代更是以其代表作《边城》轰动文坛,引发广泛关注。
2.周立波:写一件趣事发一笔“意外之财”
周立波以农村革命题材的创作著称,曾写下颇有知名度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这位长期扎根乡土的现代作家,写作生涯其实是从大都市开始的。1928年,20岁的周立波初到上海,为了生计,试图做店员、瓷器工人、跑街的伙计,甚至还去考过电影演员,但都没被录用。在处处碰壁的谋生途中,周立波仍然兴致勃勃地出入十里洋场,即便口袋里没有几毛钱,却还是精气神十足地在上海玩了个痛快。
其间他遇到一桩买菜的趣事,给朋友讲过之后还嫌不过瘾,就写了一篇风趣的千字小文,谈被迫早起去菜场的无奈、菜市的活力和市井的趣味。文章经过反复推敲打磨后,署了“小妮”这样一个女性化的笔名,寄给了当时上海的一家副刊。没多久,这篇文章果然见诸报端。周立波异常兴奋,文章发表的喜悦和成就感远远超出了其他,以至当报社通知他去领稿费时,他也没放在心上。周立波托一位表弟去代领并承诺稿费全部奉送。表弟领了4块大洋——相当于普通劳工1个多月的工钱,他一路品尝各种平时想吃又没钱买的美食,回到家把剩下的两块大洋给了周立波。周立波拿这笔“意外之财”请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而正是这次发表,让周立波慢慢发现了自己的文学潜质,从此走上写作之路。
3.莫言:被战友围着请客
莫言早年的创作异常艰难。他尝试写过很多小说、诗歌和话剧,并把稿件投向全国几十家刊物。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投稿都是手写的,未被录用的稿子被编辑部退回,信上印着醒目的“退稿函”3个字。莫言由此没少受过冷嘲热讽,当时一个老邮递员就抱怨:“如果每个单位都有你们这么一个人,我们邮电局得天天给你们送邮件。”
1981年,26歲的莫言终于在河北保定的文学双月刊《莲池》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这篇现在看来不算出色的处女作,据说还是莫言按照编辑的要求反复修订才勉强被录用的。但这毕竟是零的突破,而且莫言还收到72元钱的稿费。他当时是个解放军战士,每月工资15元钱。部队的战友们围着要莫言请客,莫言当即买了烧鸡、酒、烟和大家。
在处女作发表的鼓励下,莫言投入更大的热忱从事创作,又陆续在《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等高端刊物上发表作品。尤其小说《红高粱》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后,莫言轰动文坛。
4.舒婷:没有发表作品却收到“稿费单”
1969年,舒婷从厦门鼓浪屿到闽西山区插队。因为没有时间读书写作,满怀作家梦想的她为自己的理想即将夭折而沮丧。父亲知道后不远千里赶到女儿身旁,反复开导她。在父亲的鼓励下,舒婷继续跋涉在自己最爱的文学路上:夜深了,当别的知青早已进梦乡的时候,她仍坐在灯下看书写作。3年间,她密密麻麻地写了几百本的笔记和诗稿,可投出的稿件没有一家正规刊物录用。
1972年,舒婷返回厦门当了一名工人。这期间,艰苦的环境和超负荷的劳动并没影响舒婷的创作热情,她仍然坚持写作、投稿,但照样屡屡碰壁。舒婷万分沮丧中,把所有的诗稿装进麻袋,发誓以后告别写作。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她意外收到了一张《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稿费单。附言栏里还有一行工整的字迹:“您的诗歌被本刊采用,望不要放弃,继续努力。”舒婷捧着这张5元钱的稿费单,顿时百感交集。
多年后,舒婷依然珍藏着这张“稿费单”。令她无论如何没想到的是,第一笔“稿费”竟然是父亲寄来的。父亲后来告诉她:“是我用自己的工资给你汇了这笔稿费。”舒婷由此真正感到了父爱如山的含义。当年正是这“稿费单”,让舒婷走出沉沦,继续发奋创作,很快就于1977年在《诗刊》杂志发表了成名作《致橡树》。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