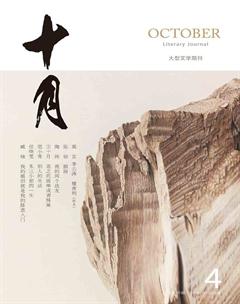我的眼泪就是我的膝盖入门
臧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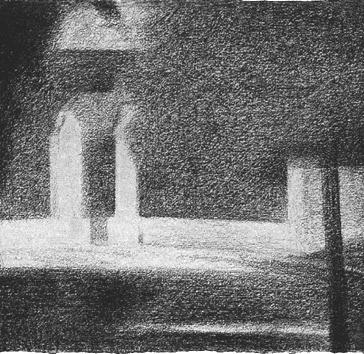
垂柳的感激入门
擅长发侧芽,令早春朦胧于
我们有时可以逃离
已变形的铁屋,将天真
消化为天真的计谋。荷塘边,
它们是安静的伙伴,安静到
时间也无法出卖它们的安静。
不管你使多大的劲儿
将它们拽向你的好奇,
它们仍会弹回到风景的摇篮之中。
它们的蒴果小得令你奇想到
紫燕的口粮。为了秀一秀
父亲的榜样,我确实用它们的枝条
编织过一个简陋的篮子;
但好在这样的事,你拥有
最终的衡量权。尽管你刚吃了
半个苹果,它依然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篮子,
绝对盛得下心爱的一切。
你准备把你的所有宝贝
都放到里面,过一过瘾;
至少要让玩具熊抱着布老虎,
体会到从未有过的震颤。
完美的山楂入门
风味独特,酸甜到
从最初的童年,你的成长
比邻它的生长,一直到
虽然隔着一堵墙,也无法阻断
它生长在你的成长中。
果树的陪伴培养的是
天性中的友善,我觉得
我很少会像在院子里种下它那样
赌对了一点什么东西。
伞状花序稍一撑开,
春雨就及时到绵绵;
果木之中,它的姿态偏于朴素之美。
人体之中,元素之谜
始于它知道如何在温火之上
慢慢搂紧荸荠和冰糖。
它是忠于记忆的果实,
通红到游戏即测试:橘子和山楂,
如果让你选,你会选山楂。
换一组,多增几个选项,
香蕉苹果桂圆和山楂,
如果让你选,你依然会选山楂。
冬枣脆甜,口感十足,
但如果二者必居其一,
你还是会选山楂;因为事情简单到
其他的水果都是买来的,
只有山楂,是我抱着你——
倾身向前,胳膊伸得直直的,
你终于从悬空的事物中把握到
原来好吃的红果果是可以
亲手采摘到的。
刺猬向导入门
草丛的幽暗中,秘密小径
不交叉宇宙之谜,反而
从人生的死角里抽出
一条窸窸窣窣的线索——
我搂着你的影子,盲目于
我们竟然可以非凡地走向
盲目竟然比死亡还奢侈。
在我们身边,它羞怯犹如
你先于我们在它身上发现了
一个小小的向导。而在成人世界
太多的偏见令它的敏感垂直于
美德的匮乏。更深的沉溺
将我们带到它的刺面前——
不多不少,每一次触摸,
都会留下不止一个教训。
受惊时,它浑身卷成刺球,
给宇宙送去一个强硬的礼物;
但你一点也不怕,好奇如
我们本应是神秘的受益者。
放生之前,它蜷缩在阳台上
用了七天时间竭力扮演你的宠物。
小小的主人身上竟然埋伏了
那么多膨胀的责任。你最初的
平等意识来源于:全身布满尖刺,
它居然和我们一样也是哺乳动物。
安静的旁观中,照耀在它身上的星光
一直在美丽的黑暗中加班,
而黑暗在星光的歌唱里仿佛已失业。
它是你的灵感,僭越了童年的边界;
但更难得的,它也是我们共同的灵感,
僭越了世界的破产。它完美的警惕性
如同一具带刺的王冠,肉感于
可能的话,我们只想站在它那一边。
我的眼泪就是我的膝盖入门
僻静的落叶,将我积累
在陌生的覆盖中。如果冷的话,
就让我听到那抓紧的声音。
或者,假如我们的倾听
最终并不以我们自身为
倾听的边界,那么,最后的虫鸣
也在加紧润色大地的安魂曲——
金色的记忆涌向你锋利的影子,
就好像在附近,幽亮的湖面
刚刚制作好一个宽大的刀鞘;
秋风中,人性的污点已开过刃;
无底洞算什么?当我从野鹅的叫喊中懂得
个人的悲痛不仅仅是无法测量的,
它并不屈从于故事的逻辑。
它也不浅薄于任何可能的比较。
事情的另一面,作为归宿,
大地和時间同样有限;
你深埋在纯粹的碧蓝中,
从另一群野鹅的叫喊里得到
新的催眠。悠悠浮云
如同洗白的靠垫,塞向你的软肋。
哦。时间的软肋又有何不同?
你的告别竟如此富有弹性,
将人父的悲伤垫高到
我必须坚硬成新的世界台阶。
跪下,我的眼泪就是我的膝盖。
跪下,我的心跳就是我的膝盖。
跪下,我的呼吸就是我的膝盖。
假如还有奇迹,今生今世,
我的悲伤就是你的道路。
天蓝得就好像真实终于有了新的边界入门
一抬头,人生如戏
怎么沉默,都不如
碧蓝更入戏。忙来忙去,
原来一切都还需要秋风的点拨。
刚洗过的碧蓝,像新推出的
超级冷却剂,令悲伤无边到
木星仿佛又有了一道新光环。
舞台已移向秋日的天空,
难以想象碧蓝竟然替宇宙
过滤了这么多的台词:
譬如,我挣脱了我的角色,
但面具并未蒙上新的灰尘。
你的死,把人父的孤独
重新介绍给神圣;但新的情况是
时间比时光还偏僻。
我是我的新生,真的
就这么绕不开因人而异吗?
或者,从今往后,我是我最陌生的骨头,
真的还需要给试金石留点面子吗?
阳光很秋高,我将我
一点点喂给无边的碧蓝;
哦,亲爱的孩子,我能感到
你的胃口突然变得好大。
多么春秋入门
北方的秋雨下出了
南方的感觉。潮水和泪水
在你的影子里交流
如何缩影于天若有情。
燕园深处,灰喜鹊刚一展翅,
悲伤就在我身体里
飞快地换了一个姿势。
借幽灵一用,时光的线索即使断了,
萧索仍将辽阔地慰劳孤独,
就好像光荣属于起风时,
石头已不再是对象,
我最想踢的是死亡的屁股。
并且我不再担忧人父的愤怒
是否已出离神秘的力量。
多么春秋,从我身上
掉落的东西,假如你想知道
它像什么的话,
它介于落叶和刀光之间。
童心学入门
天坛东门对面,天堂的出口
仿佛也低调过一回。自然博物馆里
有一颗童心,像刚刚洗过的
时间的球茎,随着标本
突然换成巨大的恐龙骨架,
开始忽大忽小起来——
大的时候,像我中有你,
小的时候,像你中有我。
从节奏上看,变换很随意,
似乎毫无规律可循;
除非长大后你会追踪到
爸爸曾经的感触:自然的奥秘
并不害怕我们将它们陈列的
就如同仿真玩具店刚刚开张。
石斧的记忆带着狼牙上的小孔
涌向你睁大的小眼睛。
新的空间里,全是陌生的东西
原始到了自然的真相
只能靠自然的历史来想象。
身为人父,我更看重的是,
你的兴奋已构成纯粹的
超越年龄的人性经历,光滑得
近乎不断向未知的边界滑动的
一条单轨。有一瞬间,
我几乎想断定:世道如此晦暗,
最大的幸福莫不就是还有
一颗不知疲倦的童心
可供亲人们秘密地分享。
壁虎学入门
你的第一只壁虎
将我们重新带入古老的夜色。
仪式是临时加进来的,
你一点也不紧张,你的神色
新鲜得如同大象的背上正驮着
一只刚赢得了比赛的乌龟。
除了童话,什么都可能是
世界的漏洞。但是别着急,
看不见的缝隙环绕着
还没有来得及讲述的故事;
它是暧昧的闯入者,却正确于
家也可以是小小的生物博物馆。
它潜伏在想象的角落里,
从不担心角色的大小
会耽误它的疗效。它专治
成年人不相信分身术。
比好奇还专注,你看它的樣子
就好像它是一小截专门用来
疏通特殊管道的工具。
只有一种可能,成年后,
我被我死死堵住了。
而宇宙不过是后遗症。
但是,天真自有天真的秘诀;
你的问题永远都是我的出口——
爸爸,它真的会吃蜘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