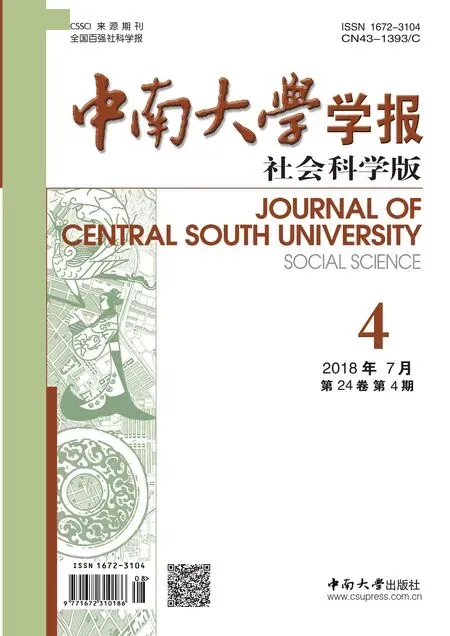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的逻辑与策略——基于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框架
杜倩博
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的逻辑与策略——基于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框架
杜倩博
(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21)
政府部门内设机构的改革逻辑不仅应基于自身,更应当在中国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分析。在中国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政府部门内设机构处于引导与控制整个机构治理体系的“核心层”位置。因此,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便具备双重逻辑:一方面,遵循官僚制治理模式的基本规律,顺应核心层内部的横向均衡逻辑推进内设机构精干设置,顺应核心层内部纵向集分权逻辑,优化内设机构的权力配置;另一方面,在核心层外部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框架中,通过内设机构改革,推进平行专业化、垂直专业化两种公共机构治理模式的融合发展。基于上述逻辑,内设机构改革应该发挥现有组织治理优势,并针对各种治理弊端采取相应的具体改革策略。
机构改革;内设机构;精干设置;权力配置;公共机构治理
政府机构改革不仅仅限于部门之间的调整,更需深入到政府部门内部,调整和优化部门内设机构的组织设置与权力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1]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再次提出“精干设置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科学配置权力”[2]。这就为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改革过去内设机构过于分散的状态,通过机构整合实现内设机构精干设置;二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推进内设机构权力配置的优化。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布以后,制定新组建部门的“三定”方案成为下一步机构改革的重点工作,内设机构的改革问题开始在实践中进入具体方案的研究阶段。在此背景下,阐释政府部门内设机构的改革逻辑,并据此提出内设机构改革的策略成为学术研究重要的任务。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与实践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界针对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的专门研究数量很少(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以“篇名”为“内设机构”为条件进行查询,尚无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探讨;仅有关于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的研究成果)。但是,以“大部制”“机构改革”为主题的一些论文注意到了政府部门的内设机构问题,为专门研究该主题提供了重要借鉴。例如:改革杂志社专题组考察了大部门内设机构存在的职能交叉、整合不力的问题[3],胡象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大司局”的概念与建议[4]。傅小随、王湘军从决策权和执行权关系的角度提出大部门内部机构改革的设想[5−6];张翔提出大部门制改革应当注重大部门内部机构的运行机制[7]。笔者的前期成果也从大部制权力结构的角度,提出了内设机构自主权及其控制的理论逻辑与改革建议[8]。然而,这些观点比较零散,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亟需学术界对此展开深入、专门的研究。
国外并无“内设机构”的专门称呼,但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公共机构治理(agency governance)框架中存在着与中国内设机构较为相似的组织形态。从其实践来看,公共机构治理框架由两大部分组成:①由部门领导、若干对部门领导起辅助作用且无法律独立地位的机构(类似于中国的内设机构)组成的“核心层”,掌握政府部门的宏观决策权和综合管控权,是整个政府部门机构治理框架中的“掌舵”部分。②数量较多的专业机构(agency,国内很多文献称之为“执行机构”),是政府部门机构治理框架中的“划桨”部分。这些专业机构是遵循市场化治理、网络化治理等原则建立起来的,具有多种不同形式。诸如: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半自治机构、基于公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独立机构、基于私法设立的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组织、执行部门政策的地方性机构、通过服务外包承担公共职能的私人组织。在此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政府部门首长依靠内设机构的辅助,对分散化的专业机构实施战略控制。
针对公共机构治理的上述实践,国外公共机构治理理论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有学者认为这些专业机构具有不同程度的政策自主权、人事自主权、财务自主权、管理自主权、业务自主权[9]。还有学者认为核心层采取的是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相结合的双重模式,将传统等级控制与市场化控制、网络化控制、合作化控制等多种控制技术相结合[10]。更有学者提出由于专业机构自主权造成的“半官方机构难题”,政府部门核心层除战略宏观控制外,还要加强对专业机构事务重要环节的微观控制,以形成机构联盟治理模 式[11]。综合这些理论可以发现,公共机构治理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政府部门核心层”(以内设机构为主体)与“分散化的专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核心层的综合控制(以内设机构为关键力量)与专业机构自主权相得益彰,使公共机构治理体系真正融合为统一的整体。
国外公共机构治理理论与实践,虽然难以直接解决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能够为中国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的逻辑分析提供理论借鉴——政府部门内设机构处于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结构框架中。研究的问题便由此产生,中国的公共机构治理框架呈现出怎样的形态,政府部门内设机构在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处于什么位置?内设机构的现状,能够体现出怎样的公共机构治理逻辑,具有怎样的治理优势与困境?应当通过怎样的改革举措来推进政府部门内设机构的精干设置与权力科学配置?
二、中国公共机构治理整体框架中的政府部门内设机构
中国公共机构设置框架的现实状态,既与国外公共机构治理具有相同的规律,又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形成了中国的公共机构治理框架如图1所示。
一方面,部门“机关”成为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的“核心层”。由部门领导班子、内设机构组成的中国政府部门“机关”,虽仅占部门编制总数的极小部分,但具有政府职能领域内的综合领导权,以“核心层”的地位对分散化的专业机构进行政策引导与集中控制。并且,经过多次机构整合,中国政府逐步形成了多个职能整合的、综合性的“部门机关”。
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门“机关”外部,还存在数量较多的专业机构,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分散化、网络化的公共机构治理模式。这些专业机构可以分为如下五种类型:①部门直属行政单位。这类机构的性质多数为承担行政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监管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应当伴随着事业单位改革转变为行政机构,并且他们往往还管理着多个次级直属事业单位。例如:交通运输部的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水利部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等。②部门直属事业单位。从其公益性来看,可以划分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从其承担的职能来看,可以分为政策研究、专业技术支撑、公共服务提供等具体类别。③部门归口管理机构。这类机构在中央政府部门称之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具有自身独立的经费渠道、人事管理权限,但接受部长通过会议方式进行的管理,是政府部门的“半内部”机构。④部门联系单位。这类机构属于非政府组织,但与部门机关具有紧密的联系,同样处于政府治理的组织体系当中。⑤公民、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遵循着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政府治理逻辑,公民、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也会以行政契约的方式参与政府治理,与政府部门内设机构发生权力关系。

图1 中国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框架
交通运输部经过了两轮机构改革,形成了部门内部机构设置的典型案例。如表1所示,交通运输部“部机关”(领导班子、内设机构组成)构成了整个机构治理体系的核心层,核心层管理着7个直属机构(可以划分为直属行政单位、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公益类事业单位等具体类型)、18个联系单位、3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其中,“部机关”的编制仅为647名,交通部直属机构与联系单位的行政编制为24 849名、事业编制40 205为名①。可见,“部机关”占机构编制总额的比例不足1%,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规模核心层”。“部机关”这个小规模的核心层对众多的专业机构进行引导与综合控制,并将社会组织、企业吸纳到公共机构治理框架当中。
在上述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内设机构处于政府部门公共机构治理体系“核心层”的位置上,并受整个公共机构治理整体框架的限定与约束。因此,内设机构改革应当遵循双重逻辑:第一,在核心层内部治理框架中,内设机构作为部门领导班子辅助机构的改革逻辑。由于核心层是一种典型的官僚治理框架,因此在核心层内部的治理框架中,应当按照官僚治理框架的逻辑进行内设机构的精干设置与权力配置。第二,在核心层外部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内设机构作为治理框架导向者与监控者的改革逻辑。这样的双重逻辑与国外政府部门核心层内部机构设置具有逻辑相似性、一致性,但是在内设机构设置的具体形态、改革逻辑的具体表现上,又明显具有中国特色。
上述双重逻辑之间存在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上述双重逻辑是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逻辑的两个部分,这与中国公共机构治理框架的两个部分存在逻辑一致性,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在双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成为政府机构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上述双重逻辑之间具有相互交织性,核心层内部的内设机构改革,能够形成核心层内部的理性官僚治理机制,提供核心层的整体治理效能,进而对核心层外部的专业机构产生管控能力;核心层外部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必然对核心层内部运行的理性化产生外部推动力。

表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的机构设置
资料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www.mot.gov.cn/jigou/
三、公共机构治理核心层的内设机构改革逻辑
由领导班子、内设机构组成的部门核心层,是一个按照官僚制的治理原则运行的行政机关。即使是在新公共治理时代,“官僚治理”的模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特别是“较之于政府外部,‘等级制的影子’在政府内部更为明显”[12]。内设机构处于核心层内部纵向与横向的交叉关系当中,并由此产生改革的基本 诉求。
(一) 基于核心层内部横向均衡逻辑的内设机构精干设置
在官僚治理框架中,内设机构精干设置来源于内设机构间的横向均衡与协同需要。这种横向均衡与协同需要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各内设机构间应当相互衔接、相互合作,任务大体均衡,应当尽力避免内设机构之间的权力交叉、多头管理、权力分配欠均衡等问题。然而,由于内设机构的设置过于分散,常常出现内设机构之间的上述问题,政府部门对外管理力量分散。例如,交通运输部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不断推进内设机构的整合,以16个内设机构的较少数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内设机构设置相对精干化的代表。然而,其他部门能够达到交通运输部内设机构精干化程度的情况比较少见。
除此之外,核心层内部还需在参谋类内设机构与业务类内设机构之间达成横向的均衡状态。参谋类内设机构是辅助部门领导班子对整个政府部门组织治理体系进行管控的内设机构,例如交通运输部的办公厅、政策研究室、法制局、综合规划司、财务审计司等;业务类内设机构是承担政府部门具体行业管理业务的部门,往往与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对象发生直接关系,如交通运输部的公路局、水运局、运输服务司等。在这样的直线职能制组织中,参谋类内设机构具有政策研究职能,他们为领导班子提出的建议一旦被采纳,便对业务类内设机构具有约束作用;绩效管理、监督监察、政策法规等参谋类内设机构对业务类内设机构的政策起草过程和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监督权,对业务类内设机构形成制约作用。业务类内设机构具有更多的业务管理权,能够将业务管理中的客观问题反馈给参谋部门,对参谋部门也相应具有限制作用。因此,这两类内设机构共同服务于政府部门的总体目标,他们之间应当紧密合作、保持均衡。
然而,中国政府部门往往强化专业类内设机构,弱化参谋类内设机构。专业类内设机构不仅行使各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担负着起草、承担和研究等职责;相反,参谋类内设机构设置相对简单,政策研究与审查的职责也相对弱化。从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情况来看,参谋类内设机构的职能明显弱于英国、美国,这也使其意识到需不断加强参谋类内设机构。例如交通运输部最近就增加了综合规划司对国家铁路局相关项目规划的管理职能。但是,其他部门遵循这种改革思路的并不多,甚至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内设机构的改革实践中,出于突出主业的目的,还大幅压缩参谋类内设机构的数量和人员编制。
当然,这种内设机构的设置状况具有相应的治理优势。由于业务类内设机构广泛接触机关业务,能够将政策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政策建议形成过程中能够切实考虑政策执行中的各种问题;相反,较多依赖参谋类内设机构的政策研究、起草职能,往往使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产生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之间的冲突。
但是,过多依赖业务类内设机构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弊端:一是弱化了参谋类内设机构对业务类内设机构的制约,参谋类内设机构对业务类内设机构政策的合法性、民主性、科学性的审查力度不够,对业务类内设机构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力度不强;二是由于业务类内设机构往往专注于实务,而对政策方向、机制改革等业务理论并不敏感,加之业务类内设机构之间分工过细,容易导致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能力和宏观管理能力欠缺。
因此,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之一,是解决内设机构过于分散化弊端的同时,推进参谋类内设机构与业务类内设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均衡,实现公共机构治理核心层内部的横向均衡。
(二) 基于核心层内部纵向集分权逻辑的内设机构权力配置
内设机构的性质是部门领导班子的辅助机构,这就形成了核心层集权的组织治理框架,内设机构正是处于这种集权的结构中。在组织治理框架中,“沿着权力链(从战略高层到中间线)自上而下地分派决策 权”[13]。当决策权较多地处于组织高层时,组织呈现较为集权的状态;相反,当决策权较多地处于组织的低层级时,组织则呈现出较为分权的状态。一般而言,只有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才能够作为部门的正式代表,对外采取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内设机构通常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也不能作为民法意义上的机关法人,并不具备法律上的独立性[14]。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内设机构得到了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才能具有外部行政主体资格,可以对外行使行政管理权[15]。例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负责国家重点公路工程的相关工作,因此作为内设机构的公路局就能够以招标人的身份,以公路局的名义从事“国家重点公路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批、技术咨询服务、招标评标”等工作[16]。另外,国家工商部门的内设商标机关、公安机关的内设交通管理机构、农业部门的内设渔业船舶检验检疫机构、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内设专利复审机构等,也具有类似情况。
在这种集权的组织治理结构中,内设机构也具有较多的“事实自主权”,构成了一定的组织分权力量。①内设机构在行政实践中具有三类辅助性权力,在集权的组织治理框架中体现着事实自主权。一是领导班子决定的“承办权”,即领导班子做出各种行政事务的决定后,由内设机构具体承办相关事务并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二是领导班子制定政策的“建议权”,即领导班子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可以由内设机构提出政策议程设置建议,具体负责政策方案的草拟;三是领导班子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前定权”,即诸如审批、赔偿、资金分配、项目设定等具体行政行为,需要内设机构在领导决定之前进行业务受理、审查和判断。②内设机构也具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由此带来事实自主权。例如:内设机构处于组织的较低层次上,能够直接获得来自公民、企业、社会的一线信息,能够与社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公共治理主体共同构成政策联盟[17],由此形成领导班子不易管控的力量。
当然,这样的内设机构权力配置模式具有相应的治理优势。首先,对内设机构行政主体资格的严格限制,是保证部门机关组织政令统一的基本前提,利于形成部门权威和稳定的行政秩序。其次,内设机构具有的“事实自主权”与“法定自主权”,能够使领导班子成员不便随意插手下级事务,对领导班子权力产生一定的制约效果。
但是,上述内设机构权力配置模式也容易造成“部门内部权力过分集中”和“内设机构自主权失范”的双重问题。一方面,政府部门核心层内部广泛存在着集权结构的弊病。例如,由于内设机构法定自主权较少,政府部门内部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班子,往往产生部门一把手权力制约与监督的难题;内设机构缺乏相应的法定自主权,由此便失去了承担相应责任的制度安排,致使本应属于下级的责任被制度化或人格化地“上推”至领导班子成员;由于权力集中程度高,行政实践中便存在着诸多不必要的报告请示、签字盖章等程序,进而带来降低行政效率、降低组织回应性、缺乏组织灵活性、阻碍组织学习与创新等一系列难题。另一方面,内设机构的事实自主权也往往造成对内设机构的控制难题。例如,由于内设机构在政策制定上的自主权,政府部门往往出现“司长策国”“处长治国”等现象;由于内设机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具有事实上的自主权,易于造成政策的“中梗阻”,领导班子的政策与意志在向下传递的过程中被中层干部过滤;上级对下级的监督陷入困境,内设机构权力失范及其制约难的问题也时常出现。
因此,内设机构改革应当顺应中国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权力配置的现状,在尊重内设机构事实自主权的前提下,发现并解决内设机构权力配置的上述弊端,合理设定内设机构的法定自主权,推进内设机构事实自主权的合理利用与制度化限制,形成稳定、高效的政府部门内部纵向集权与分权有机结合的组织治理框架。
四、核心层外部机构治理框架中的内设机构改革逻辑
内设机构不仅存在于核心层内部,而且存在于核心层外部的整个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与国外公共机构治理的相似之处在于,中国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框架同样融合了“平行专业化治理”“垂直专业化治 理”[18]两种治理模式。内设机构不仅作为领导班子的辅助力量对专业机构进行管理,还事实上承担着管理与联系专业机构的职责,因此成为平行专业化、垂直专业化治理模式中的重要治理力量。
(一) 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中的内设机构改革 逻辑
在中国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核心层外部汇聚了多元的专业机构,并在核心层与专业机构之间开始塑造明显具有平等性质的合作关系,平行专业化的网络治理模式正在形成之中。这种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具体呈现在治理框架中的每一个机构关系维度上:一是公益类事业单位被正式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19],较多运用了市场机制、网络机制,与部门及内设机构之间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始形成;二是在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组织加入到政府购买服务的业务中来,注重运用基于治理主体间平等关系的合同治理模式;三是在部门直属行政类事业单位、部门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管理上,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具有平等属性的结果控制战略,不断加大这些单位的业务、财务、人事、政策等方面的专业自主权。
但是,这种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的运用范围还相当有限。例如,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运用主要集中于民政、文化等少数部门,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呈现出适用范围较为狭窄的集聚现象[20]。这种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运用范围有限,固然是受环境条件、主体条件、操作条件的约束,但是政府部门内设机构的不完备性也是这种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内设机构的组织设置与权力配置状况,正在制约着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的运用。
首先,从内设机构设置情况来看,政府部门核心层缺乏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外包、外部合作等公共治理机制所需的内设机构。在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核心层与多元化的专业机构之间是一种“决策—执行”职能分离的结构。在推行职能分离以后,核心层的主要内设机构包括“政策参谋人员、与其他组织签订绩效合同的签约单位、绩效测量与评估单位以及处理预算、人事、采购和其他行政事务的小型行政单位”[21]。在这些内设机构职能履行的前提下,政府部门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掌舵的核心组织,与外部多元治理主体形成平等的治理关系,发挥出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的行政效能。但是,中国政府部门内部较少设立这些专门的内设机构。例如,从表1可见,交通运输部没有设置公共服务外包的签约机构,而是将合同签约的职能分散到了各个专业类内设机构当中,并且这些职能处于比较弱化的状态。
其次,从内设机构权力配置的情况来看,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推进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的权力配置并未得到真正强化。在网络化治理框架中,政府部门核心层承担着增强网络治理能力的角色,需要“具备良好的制度供给能力、达成共识能力、建立信任能力、利益调节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以及工具运用能力”[22]。政府部门这些治理能力的形成,主要立足于部门及内设机构相应的权力配置,并且在权力和资源转移的基础上形成专业机构的自主权力,通过柔性的治理技术实现核心层的上述能力。但是,对于柔性化的网络治理能力所需的内设机构权力,中国政府部门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权力的配置状况与行使方式自然也难以成熟。
因此,内设机构改革的重要逻辑在于,通过完善现代治理所需的内设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以推进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的应用,使政府具备现代社会网络化治理的基本能力,使内设机构适应新公共治理时代“组织间的关系以及过程的治理,强调公共服务组织与其环境互动基础上的服务效益和效果”[23]。
(二) 垂直专业化治理模式中的内设机构改革 逻辑
在世界各国的网络化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虽然政府部门核心层与专业机构之间建立了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等级关系。例如在英国,专业机构化过程增强了专业机构的自主权,强调核心层对专业机构事务的最低限度参与,强调政策网络的自组织,但也由此造成管控薄弱的“国家空心化”现象。英国由此被迫开启了治理的“元治理”(meta-governance)进程,推动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的“中心反击”(the center strikes back),强化各个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监督和控制权力,减少专业机构的自主权,推进专业机构权力向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重新集中[24]。
在中国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部门机关与专业机构之间的等级关系更加明显,使部门核心层对专业机构的管理能力始终保持较强的存在。其中,直属单位作为政府部门机关的“二级机构”,二者处于“上级决策、下级执行”的等级链条中。特别是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其设立或是出于控制行政编制规模的政治需要,或是因为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等繁重的事务处理,而具有专业性、复杂性的特点,需要保持并发挥机构独立而灵活的优势[25]。因此,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不能完全并入行政机关,属于等级化治理模式中、具有管理自主权的法定机构。即使是公益类事业单位,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行政机关等级链条的控制,以保证政治意志、行政命令能够自上而下地顺畅传递。
内设机构作为部门领导班子的辅助机构,处于这种等级色彩明显的治理框架之中。这就具有显著的治理优势:①具有较强的治理体系掌控能力,在行政实践中能够较好的行使“核心层”的基本权力。例如:为整个部门治理框架提供战略领导、宏观政策、长远计划;寻求并探索新的国家或地区发展机会,寻找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创新点;分析本部门职责领域面临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推动本部门职责领域内的各项改革;为本部门争取财政支持,通过政府资源的开发、获取和部署为专业机构提供财政引导与资金投入;对各专业机构的执行事务进行结果控制与绩效评估、问责管理、审计监督、标杆管理与监督。通过行使这些核心层权力,中国政府部门的核心层可以“永远保留制定政策的权力”“利用人力资源或技术资源激活一个网络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为组织和个人提供合作机会,促使通过协商达成共识”[26]。②在等级色彩较重的治理模式中,内设机构具有较强的网络嵌入能力。公共机构治理框架可以被看作一种多元主体的网络联结,这个网络联结内部存在多元互动关系,而且这个网络联结还处于外部社会关系当中。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作为“核心层”所需要的权力,不仅需要使其在这个网络联结内部将其势力嵌入到专业机构当中,而且也应当使其直接嵌入网络联结所服务、管理的社会关系当中。否则,公共机构治理体系当中就会产生职能交叉、信息沟通不畅、目标不一致、监督管理困难、责任困境等一系列难题[27]。在中国,恰恰由于治理框架中的权力与资源明显向部门及内设机构倾斜,政府部门及内设机构因此具有地位、资源、权力、声誉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些优势使政府部门及内设机构无论在治理网络的内部结构还是外部社会关系中,均具有较强的嵌入能力。因此,中国政府部门往往采用“史上最严格”的管理方式,发动各种治理主体加入网络化的公共治理框架中,能够以不同于国外的政策网络类型发挥出相同的网络功能和网络绩效[28]。
但是,在这样的等级关系中,中国政府部门核心层对专业机构进行集中管控所需的内设机构权力,尚未得到合理的配置与行使。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在协助领导班子对专业机构发布命令权方面,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尚未能够以柔性且有力的方式嵌入到专业机构的组织治理结构当中。第二,在对专业机构的监督权、控制权方面,部门核心层尚未能通过合理的内设机构权力配置进而有效地监测专业机构的政策执行情况,监控专业机构运作过程与绩效。第三,在对整个组织资源的管理权方面,内设机构协助领导班子对专业机构的财务与人力资源管理尚未突出战略性。第四,在对组织进行整合与协调权方面,部门核心层尚未能通过合理的内设机构权力配置促进专业机构之间的横向整合,推进部门机关与专业机构之间的纵向协调。第五,在协助部门领导行使代表权方面,内设机构未能在合理配置权力的前提下,向党委、政府、人大报告有关专业机构的重要工作,并接受公民、法人对专业机构的投诉。
同时,这种等级色彩较浓的治理框架还存在着明显弊端。首先,政府部门及内设机构对专业机构管控过多过细,妨碍了专业机构的自主权与专业性,易于影响专业机构的灵活性、运行效率、公共服务或社会监管质量。其次,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过多关注于专业机构的具体业务,势必减少进行宏观政策研究与制定、政策执行效果监督的时间与资源,降低整个部门组织治理体系的治理能力,尤其是部门核心层的宏观管理能力。
因此,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的重要逻辑,在于发挥垂直专业化治理模式优势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专业机构的专业性,通过对内设机构权力的合理配置与限定,来增强核心层合理的集中管控权、专业机构的专业自主权,由此提高专业机构与核心层两类机构的治理效能。
五、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的内设机构改革策略
在中国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内设机构组织设置与权力配置现状,使其具有核心层内外部治理框架中的重要优势,因此内设机构改革应当维持现有基本组织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的稳定性。同时,由于内设机构的组织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具有多方面弊端,应当遵循着保持优势的基础上弥补缺陷的逻辑思路,通过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此,文章提出如下改革策略以供借鉴。
首先,完善与优化内设机构的组织设置。遵循内设机构横向平衡的逻辑,设置或完善政策研究、政策审查、监督控制、内部审计、综合协调、法制管理等辅助类内设机构,整合与重组业务类内设机构,达到内设机构精干、全面设置的目标。顺应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设置合同管理与服务外包、绩效监督与控制、政策规划与发展等掌舵型内设机构,减少直接管理经济与社会、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内设 机构。
其次,以完善核心层内部的理性官僚制为指向,优化内设机构权力配置。①通过内设机构权力配置优化纵向权力结构。合理扩大内设机构的法律授权范围,使内设机构能够在依法设权的前提下,行使更多的法定自主权,以实现有效的层级间法定分权结构。鼓励政府部门领导班子与内设机构充分协商的前提下,通过行政授权的方式,采用部门规章、行政授权令等形式为内设机构授权,同时由内设机构承担相应职责。完善政策制定以及各种行政行为的流程与规则,明确在流程各个环节当中的内设机构权力,以此保护和约束内设机构的自主权。对部门内部的工作进行“决策分析”,明确内设机构及其工作岗位上的决策权,使组织在尽可能低的层次上、接近于行政活动的现场做出决策,同时在保证事务得到充分考虑的层级上做出决策[29]。②通过内设机构权力配置优化横向关系。对部门内设机构的权力配置尽量实现均衡化,纠正部分内设机构权力过重的问题。强化参谋类内设机构职责,促使其很好地行使政策综合的研究与协调、战略方向判断、监督业务类内设机构行政行为等职责,形成参谋类内设机构对业务类内设机构的监督制约机制。③推进对内设机构事实自主权的制度化保护与限制。制定和完善政府部门政策的制定、监督管理、具体行政行为等各种事务的行政程序,在程序的各环节明确内设机构的责任与权力,塑造组织管理各项流程中的内设机构的自主权及其约束机制。
再次,以业务的专业化程度为标准,推进内设机构权力向专业机构转移。判断内设机构各项业务的性质是否属于行政事务,将非行政事务转移到相应的直属单位。判断内设机构权力的专业性,将某些专业性强的事务转移到专业机构,并减少对专业机构具体专业事务的管理。明确政府部门“三重一大”事项的具体范围,使内设机构在明确的范围内协助领导班子做出决定,承办领导班子交办的事项。同时,强化对内设机构综合形势的研究、分析、判断和宏观管理的权力,明确内设机构对专业机构进行绩效评估、政策监管的权力范围,增强部门核心层的宏观管控能力。
最后,增强公共机构治理能力所需的内设机构权力的科学配置。减少内设机构对专业机构的等级化命令的同时,增强内设机构的柔性治理能力。①内设机构应当具备协助部门领导班子激活网络的权力。例如:调动各种人力和财力资源、提供网络运作的各种制度、构建主体间的对话协商与共识形成机制、通过协调建立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使治理网络能够有效运转并实现治理目标。②内设机构应当具备协助领导班子对治理网络进行有效管控的权力。例如:平衡与调解各方利益以实现多元治理主体行动的一致性,为治理网络提供明确的治理目标,通过加强权力监控防止治理过程中的腐败,建立并运用各种监管程序来化解治理风险,强化对专业机构的问责来进行网络治理绩效的管控。③恰当配置内设机构对专业机构等级化的治理权力。例如:内设机构嵌入专业机构治理结构的权力、协助领导班子监督专业机构的资源管理权、对专业机构的整合与协调权力等。
注释:
① 该资料为笔者申请获得的政府信息公开数据,见《交通运输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5年第161号),告知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2]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2018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 2018-3-5(1).
[3] 改革杂志社专题研究部. 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政策演进、实践探索与走向判断[J]. 改革, 2013(3): 5−17.
[4] 胡象明, 陈晓正. “大司局”视野下大部制改革内部运行机制探微[J]. 南京社会科学, 2011(5): 68−72.
[5] 傅小随. 以大部门内的纵向改革促进建设服务型政府[J]. 桂海论丛, 2013(3): 6−9.
[6] 王湘军. 大部门内部机构设置和权力结构研究[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4(3): 91−95.
[7] 张翔. 从体制改革到机制调整: “大部门体制”深度推进的应然逻辑[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2(2): 61−68.
[8] 杜倩博. 大部制的权力结构: 机构合并与分立相融合的内在机理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2012(6): 48−72.
[9] THIEL S V. Comparing agencies across countries[C]// VERHOEST K, THIEL S V, BOUCKAERT G, et al. Government Agencies: Practices and Lessons from 30 Countri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20.
[10] DOMMETT K, MACCARTHAIGH M, HARDIMAN N. Reforming the westminster model of agency governance: Britain and ireland after the crisis[J]. Governance, 2016, 29(4): 535−552.
[11] FLINDERS M, THNKISS K. From ‘poor parenting’ to micro- management: Coalition governance and the sponsorship of arm’s length bo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0-13[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6, 33(3): 1−21.
[12] 史蒂芬·P. 奥斯本. 新公共治理?——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观点[M]. 包国宪, 赵晓军, 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35.
[13] 亨利·明茨伯格. 卓有成效的组织[M]. 魏青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37.
[14] 屈茂辉. 机关法人制度解释论[J]. 清华法学, 2017(5): 128−138.
[15] 任进. 行政组织法研究[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0: 220.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国家重点公路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批技术咨询服务招标评标结果公示[EB/OL]. (2018-4-27)[2018-5-26]. http://zizhan.mot.gov.cn/zfxxgk/bnssj/ glj/201804/t20180427_3014797.html.
[17] 陈玲. 官僚体系与协商网络: 中国政策过程的理论建构和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 2006(2): 46−62.
[18] TRONDAL J. Agencification[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4, 74(4): 545−549.
[19] 财政部、中央编办. 关于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Z]. 当代农村财经, 2017(4): 39−41.
[20] 邓金霞. 政府购买中的集聚现象: 一个合作发生机制的分析框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5): 89−95.
[21] 戴维·奥斯本, 彼得·普拉斯特里克. 政府改革手册: 战略与工具[M]. 谭功荣, 颜剑英, 魏军妹,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09.
[22] 党秀云. 论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能力要求及提升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4): 46−52.
[23] 竺乾威. 新公共治理: 新的治理模式?[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7): 132−139.
[24] DOMMETT K, FLINSERS M. The centre strikes back: Meta-governance, delegation and the core executive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1—2014[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5, 93(1): 1−16.
[25] 刘小康. 行政类事业单位改革路径初探[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2(2): 1−4.
[26] 田凯. 治理理论中的政府作用研究: 基于国外文献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12): 118−124.
[27]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 威廉·D. 埃格斯. 网络化治理: 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 孙迎春,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6−50.
[28] 龚虹波. “水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中美水资源管理政策网络的比较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4): 143−152.
[29] 彼得·德鲁克. 管理: 使命、责任、实务(实务篇)[M]. 王永贵,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173.
Logic and strategy of reformation in internal bodies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agency governance
DU Qianbo
(School of Law,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The logic of reformation in internal bodies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s not only existing in itself, but also 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Chinese agency governance, in which the internal bodies lie at the core level of guiding and controlling the whole agency governance system. Therefore, the reform of internal bodies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bears double logic. On the one hand, by abiding by the basic rules of the bureaucracy model, we should promote the capable set-up of internal bodies conforming to the horizontal equilibrium logic within the core layer, and the capable power distribution of internal bodies conforming to the vertical decentralization logic within the core layer.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agency governance outside the core level, we shoul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agency-governance model of parallel specialization and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by reforming the internal bodies reform. Based on the above logic, the reform of internal bodie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existing agency governance, and take specific strategies agaist various disadvantages.
institutional reform; internal bodies; capable setting; power distribution; agency governance
[编辑: 谭晓萍,游玉佩]
2018−03−14;
2018−06−0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府部门内部治理结构现代化研究”(17FZZ010);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南机构改革后的大部门内部权力制约与协调研究”(14YBA1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杜倩博(1982—),男,河北石家庄人,博士,湖南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组织理论、政府治理与改革,联系邮箱:duqianbo@126.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4.015
F830.91
A
1672-3104(2018)04−012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