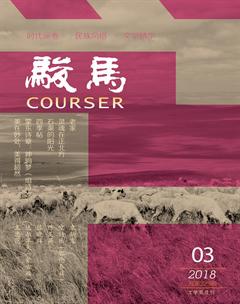石渠的阳光
陈美英

把井水抽起来
走出石渠牧场,为我联络的援石干部回老家休假去了,我按他走前的嘱咐在援石干部集体宿舍住下。
整理牧场笔记成了我的当务之急。宝贵的生产人类学第一手资料作为亲爱的朋友陪伴,使我在这高寒处又安顿下来。
中队的水泥坝子里停着不少小车,三面是红瓦水泥墙的平房。其一是援石干部宿舍。屋里拥挤地摆着上下铺铁床,床上是统一的方格铺盖。有几张木桌子,塑料凳子很多破的,大家将其重叠着坐。
石渠野狗横行,包虫病高发。干部们喝水都得一再注意。他们住的中队院子里扔着许多装矿泉水的桶,就是喝外面运来的水的原因。
他们为什么叫做援石干部?因为是从甘孜州其他17个县派来帮助石渠的。
“其他的县不需要这样帮助吗?”我问。
援石干部是个新名词,一开始觉得突兀,为什么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援藏干部?这是石渠的特殊性,需要州内推进现代化。这里是四川最大的县,县城海拔4260米,比拉萨还高六百多米,位于川青藏结合部,远离交通主干道。除了来自成都的援藏干部,张博他们这批州内来援助的干部有一百多人。
女干部宿舍人少,主要是一个干部在。她开始对我友好,跟着不理我,无论我怎么对她打招呼。碰了冷面孔的我也不主动了。
过了几天,隔壁宿舍一个瘦高的年轻人走到门口对我说:“你到这边来坐吧。”
我起身走出去。他带我到很多人坐着打麻将的宿舍。一个矮胖的干部给我倒了茶,把我引到布帘子隔了一半的里间。
叫我来坐的干部坐到一张没人的桌子前,对我说:“这里热闹。你不要拘束,我们都在这里玩。”
一下跟他坐得很近,我感到脸热,看他也抬不起眼睛。这样不说话不礼貌,说话不看人家也不行。他看我这样,也忍不住脸红了。
过了片刻,我调整了心情,才把面前的他和身后的人们收纳眼底,跟他正常地说话。
他是这里年龄最小的,我说他像高中生,像越野族。他说是的,他叫张博。与西藏打篮球联欢时,西藏那边叹息四川这边就没人了,怎么派个高中生来打球?
第二天中午在院坝里,张博看到我时说:“吃饭去。”
他们向一座平房走去,我才知道还有食堂。
饭十五元一份,很不错。援石的在里间围坐一桌,一边有说有笑,一边把几个菜吃得精光。援藏的坐在客厅,人数少。援藏的相对安静,且成都化。
这天中午,疾控中心的援藏干部来得晚,一进来就拉扯重叠得太高的塑料凳子,想抽出一只来坐,无奈再怎么使劲也办不到。
我不禁笑道:“还真是考验人啊。”
大家一阵呵呵。有食堂吃饭是多么幸福,我很喜欢过一阵这样的集体生活。
我抽不起来地下井水,费力地压了大半桶,这就是最高成就了。这使我用水像非洲沙漠居民一样拮据。只洗了几次袜子,也不去街上的公共浴室洗澡,省去洗衣服。
午饭后,阳光罩下明晃晃的金色大伞。张博在井旁端着杯子漱口。
我把桶拿到井旁,问他怎样才能把水抽上来。
他接过我的桶,放在手压水井的出水口下面。压了几下,水出来了。接了小半桶,他倒向水井的进水口,马上又压,水就源源不断地出来了。
他说:“先引一点,迅速地接着压。”
我马上实验,开始不成功。接着行了,把刚吃饱的胃弄得很难受。
能自己抽水了,自给自足的集体生活才得心应手。我感到这是我的大学、我的童年。
女干部为大家洗衣服洗被子。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也嘻哈打闹打麻将,胡乱地说话。
牦牛不知道自己的美
我用了几天时间和石渠告别,是在同学回德格后。我认为该按原计划去德格了,也没顾留恋石渠的心情本身意味着什么。
那时我几乎都是在大酒店草坪边坐着,望着山坡上的牦牛,看着天空,还有雄鹰。
牦牛攀爬自如。有时一个小黑点在跑,我无法确定是牛还是狗。有时大的黑点也这样跑。站在山脊上的牦牛,其剪影以防寒保暖的黑色体型展示高踞的骄傲。越陡的草坡越将其布局展示,移动更加明显。但是牦牛不知道自己的美。它在那里,不悲不喜。
有一天我看着都快哭了。张博开车进来上厕所,我从草坪的水泥围栏上站起来,他的车在我身边停下,他探出头来。
“我在做最后的告别。”我说。
他点点头,眼睛潮湿。
“我也要跟你好好告别,走之前。因为我已经把你当朋友了。”我哽咽地说。
他很感动,看着我孤独地站在草坪边。他说:“回去吧。”
我坐进他的车。车开半分钟就到了中队坝子。他去打牌那间屋坐,叫我一起进去。人们在打牌,一屋子的温暖就把我的心融化了。
离开石渠前一晚,我抽出时间去大家喝茶打牌的宿舍,把张博和背我过河的干部叫到我住的宿舍坐在一起。
木桌的对面,张博正襟危坐地端着水杯,眼睛湿润又慌乱。
桌子上有一袋瓜子,我顺手拿起,递到张博面前。
他拘谨地倒出了一些在手里。
我们吃着瓜子,开始无话。忽然张博说:“作家,你觉得应该如何发展石渠?”
我心里一惊,张博的确不像别的干部。
这是个宽泛的话题。由于有干部刚才使我烦躁,我回答张博时心不在焉,还拿出地理教材来敷衍。后来谈话进入正轨,我们分析了该区发展的制约,不杀生的传统使野狗横行,在这里找到了天堂。这里包虫病发病第一。如果不管理好野狗,消灭传染源,不可能有效控制。还谈到有信仰的民族区别。张博表示他是藏族,谈的这些问题本就存在。
张博单位的车明天要回康定,我可以搭一段车再转车去德格。于是我请张博帮忙。已经夜深了,他马上电话联系,为我确定了搭车事宜。
第二天天未亮,手機闹铃响起。我起床弄好行李,走到隔壁宿舍门口,无力地敲门叫醒背过我的干部。这时张博早已在车上等候。我们驱车去他们单位下榻的酒店用早餐,之后他俩送我上车。站在车门口互道再见,我几乎哽咽。车门关闭的时候,我觉得生活的一扇大门倏然关闭了。
重逢在冰雹中
第二年六月我又到石渠,提前给张博打电话了解石渠的气候情况。他说:“张博温馨提示你买个睡袋,因为你打算跟畜牧局下乡。我们单位的车最近要来石渠,你可以搭下车。”
搭公车始终是个不定的事情,我没有搭上。一路走走停停花了一周时间,才艰难地抵达石渠。
在车站一下车,冰雹打得我睁不开眼睛。前面下车的人跑得快,后面的人我来不及看他们怎么办,根本看不清。没发觉天气就变成这样了,从停车到走到车门口。
我打着伞,希望拿着行李冲进冰雹雷电风雨大作中,并到前面去找到街边店铺站一下,但是不行。狂风挟着冰雹倾泻下来,伞被吹歪,我的全身和背包湿透,鞋子进水。
我慌忙给张博打电话说我到了,叫他来接我。打了我又后悔,觉得太不该这时叫他,他也得冒着冰雹危险啊。
很快张博来了,他的灰色汽车无法靠近班车门。我招手,并且接近,他钻出车接过我的背包。我去车尾把箱子拿进车。我上了他的车。一路开行,无语。车子的雨刮器都无法把冰雹刷干净。
风雪迷蒙中,车子经过扎溪卡宾馆的黄色房子,石渠坑坑洼洼积水的街道,低矮的建筑。尤其进入中队的水泥坝子时,使我感到思念了大半年的地方像亲人出现在心灵的位置。
到了宿舍,张博也湿透了全身。他拍拍身上的雨水,拿毛巾擦了擦。鞋子里也进了水。
冰雹很快就停止了。我想起同坐班车的藏族大哥提醒我去车尾躲和去车上躲,要是早点就好了。
我说:“很抱歉,我该在车里躲一下再给你打电话,当时太慌了,不知會下多久。”
“没关系。”张博满不在乎地说。
火锅、啤酒。他们欢迎我。湿透的鞋子里脚冷,我顶住寒冷,揣着感冒的担心,和他们吃晚饭。
然后我去女干部宿舍,拿出吹风吹了一下鞋子,勉强可穿。
张博找我过去他们宿舍聊天。有个健壮的干部沉浸在讲述中,面带微笑,眼睛看着地面,把我们吸引住了。他讲起小时候对爷爷说要爷爷娶七个老婆。认真听着,我感到置身他们中的每一分钟流逝,都是生命的浪花在翻涌。
这批援石干部就精简了,张博说。上批时,每个部门都派了,有的人来了干不上活,没有对口专业岗位,比如水质检测员,这里的水都是地下水。这批全是干得上的,必须起到指导作用。医生、教师资源奇缺。有个宿舍住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
狗也怕你
和援石、援藏、本地三组干部相处食堂,大家闹嚷嚷,倒能迅速获得密集信息。这是三种视角,我需要每次马上记下。
这一年干部们都坐在一间屋里吃饭了。援石的一桌挤得紧紧的,我一般在这拥挤的人群中坐下。本地干部来吃饭的不多,一般在援藏干部那桌坐。大家说起包虫病,都怕得溢于言表,赶快去参加州里下来的体检。
发改局援藏干部每天自带碗筷吃饭。他说:“援藏,是拿生命来援!”
我觉得狗更多了。他们说玉树又运了些过来扔在这里。
晚上犬吠此起彼伏,可谓热闹非凡。狗太多,成为夜晚的“市声”。这些狗有小牛犊一般大,毛发厚长、头大腿短。它们睡在街边安然自得,大白天也在梦乡中幸福着。在大酒店草坪上盘桓的几只狗,比去年的更爱追人。
要是人有这些狗顺其自然的境界就好了。
被狗咬了三次,杨师傅愤恨地道。去年下大雪时,雪积一尺多厚,他被院子里大石头绊倒了,狗就冲过来。他又是踢又是蹬,要是几条狗一起上,他就完了。他受了伤,打了针。
帮忙做饭的老大爷说:“不要太害怕。狗也怕你。你对它狠点,给它一棒,动作迅速!”
食堂门口天天围着几只狗,长得体大毛厚。大家给它们喂骨头,刚扔出去,狗追着落点跑去,头一低就挤得打架。这些狗跟干部们熟了,有的还跟着上街走很远。我喜欢带骨头回去喂酒店草坪上的狗。有几只小狗见到我就摇着尾巴跑过来,还扯我的裙子。不过草坪上的狗并不都认得人。
尴尬角色
下雪时尤其缺氧,寒流似箭。鼻子充血,都怀疑是否感冒了。这时躺在被窝里戴上口罩方能度过。大家都饱胀、气紧、头重。那风声,那把头轻易吹痛的天气,六月份了,真是恶劣啊。
六月底去了畜牧局,我感到选对了关注对象。继续高寒草原生产人类学调查——草地、畜牧。其次是对康巴文化完整保存地区的系统关注。最后是对现代化推进的青藏牧区发展的思考,平时也可和张博探讨。
在坝子里偶尔见到张博,我们总说几句。他经常不在食堂吃饭,而在他们宿舍自己做。
谈到干部工作,张博主要负责物价这块。他们单位的科室有二十多个。居然有水泥科,是管修建房屋公路的。石渠县的物价单位就给他管。
他每天下访调查,之后整改,给出限期令。不听话的,就电视曝光,再者上大字报。也有走后门的,张博对走到宿舍门口找张局长的人说:“不在!”物价每天都以梯形速度上报到国家物价局。所以国家物价局每天都掌握着地方物价。原来国家机器这样运转啊。
我看到他和领导沟通,叹必须思路清晰。通过和他交谈,知道我对于干部工作还是门外汉。以后注意多多听取。
用电筒照着那些狗
夜里,要走过草坪、街道、坝子,才能到达中队。九月中旬张博回来了,我去和他说话。估计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搭公车离开石渠已在申请中。
打算找援藏干部要根打狗棒,他们备有这东西,去山上散步打狗防身。结果发现走廊上有长把扫帚,我就拿了。酒店草坪上的狗跟随我跑了几步自动停下,我还没向其出示扫帚。中队门口这次倒是没有狗。走过坝子来到张博宿舍,我把扫帚放在门外。
他们在喝酒。投稿前给他看看,张博告诉我有问题问问他们,不要写错了遭人笑话。还有就是不要唱高调,不要美化。就要像去年我叫他看的博客图片说明那样写。
他们也不聊天了,就是唱歌,我听得畅快。唱到道孚县歌,我才听说石渠县歌是《情洒扎溪卡》。张博唱歌不行,只能听。他说他一般不喝酒,醉了就睡三天,钱不多,但不愁,人生就这样。
他坐在堆满东西的桌子旁,还是瘦高的高中生模样。眼神坚定,动作自如。旁边是铁架床,他住下铺。他是两届援石的干部,要做四年。
“缺氧不缺志,苦干不苦熬。能坐在这里就算奉献。”我想起援石口号,问他怎么在集体宿舍应对喧闹。
他说:“必须适应。我要休息怎么办?我就拉上帘子,睡我的。在这里不是一天两天,不是说你坚持一下就完了。”
人生必须别离,我说要回去休息了。张博送我回去,黑白花狗起身也送他。我们三个走了短短的一段路。黑白花狗和酒店草坪上的狗有点不和,它们驱赶它,张博叫它先回。他站在草坪外面,用电筒照着那些狗,以免它们跟我。草坪上的狗有两只和我很亲,它们直跑过来迎接我。
我说再见,他说你快走吧,只顾照着狗。走了几步我回头看,他站在石渠夜晚的昏暗街灯下,身影显得飘摇,狗在他的电筒光下逡巡躁动,但不敢靠近。我不太担心他,这支电筒是防身的。出门前张博拿起在那位要爷爷娶七个老婆的干部身上电了一下。
穿过草坪,我向酒店大厅走去,拿着没用上的扫帚。身后跟着两只很亲的狗,我们三个走了短短的一段路。到了台阶我再回头,只见街灯的微弱光芒。一切消失在昏暗的夜色中。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