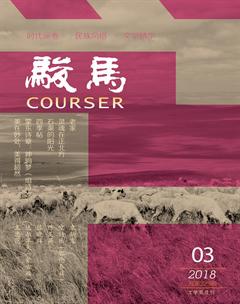逃逸
王淼
一
公车沿着桥爬坡上行。水泥旧桥每隔几年新漆,路面都已斑驳,挖挖补补,可见其使用频率与耗损。跨越双和城与绿城的这座桥,建成于1981年,初期须缴过桥费。桥下水岸以假日早晨的二手市场闻名,千百个帐篷搭起的市集,从古董、家具、电器,到各类大小物品,吃喝用度,俨然一个百货俱足的“二手物”世界。
N骑着他的二手宗申车,辗转在城市里游荡。如今他再也不用开着警车巡逻,却依然保持着四处搜寻的习惯。
上桥、下桥,五分钟路程就进入新北城区,一桥之隔,隔开两个世界。调查员N将位于北市区狭窄租屋内的物品全部净空,在接下调查案后第二日,就迁入命案发生的大楼。此大楼为公交站附近的旧楼改建,楼高二十层,住户近百。
他最新的居处为大楼中短期租赁的出租套房,此套房持有人与管理者并非同一人,而是由某租户通过中介,向屋主租下五户套房,改建成商务型短租套房。内部装潢雅致,家电全包,房价为每周五千,含管理费与每日房务清洁。调查员的房租由申请调查人R小姐支付。
N从北市租屋带走的私人物品不多,上一个住处也才待了一个半月。一台笔记本电脑、相机、录音笔、几件换洗衣物、几本资料簿、一组五公斤的杠铃、一箱杂物,就是全部家当。三年来他几乎都在各个短租房间内游走,随着调查案件迁移。他另于父母老家所在的小镇租一旧屋空房当仓库,堆放他之前所有“私人财物”。亦即以前还有“家”的时期,所拥有的举凡家具、家电、生活用品、纪念品全部封藏。
曾经,他回老家探看父母,到仓库过夜。说是仓库,反而比他现今住处更有居家感。床铺上的防尘布一掀,周遭摆放着沙发、餐桌、冰箱、电视的屋子,生活里的魅影追赶上来,使他连夜奔逃。
事件之后,N几乎都在移动。最初有大半年时间,他整日开车乱转,累了就睡车上,发须不剪不刮,浑身酒气,因此被警察盘查过几回。后来他住过廉价旅社、宾馆,慢慢才有能力租赁短期套房。但无论住在何处,他都不添购家具、不睡在床铺,而是习惯于窝身在睡袋里,好像随时可以起身逃跑。
这次的居所已经是许久以来未曾体验过的“奢华”,新近改建的楼中楼套房,装潢犹新,他初进屋内就仓皇想逃。若不是为了就近观察,他恐怕会立刻搬离。
幸而卧室设在二楼,他不用上去,也见不到。他把家具靠墙堆放,维持屋内的空旷,因应工作需要,委托人R小姐请人送来黑白雷射印表机一台。N每日将各种资讯列印,逐一清查、笔记、圈号。他交代清洁房务的大姐要进入房间,只清洁浴室与洗手间。垃圾也由他全部用碎纸机处理过后,自行丢弃。
N将最近收集的剪报、影印的资料从袋中取出,套房内没有大桌子,他用客厅茶几权充书桌,在木头地板上铺上壁报纸,以便写字、画图。墙壁设有固定式橱柜,仅有一面空墙,男人用3M可重复撕贴的胶带,在墙上贴满白纸,方便张贴资料。
他喜欢趴着或站着工作,在地板与墙壁间,将线索如地图全张挂起来,照片、剪报、地图、大头针标志着的资讯层层叠叠,使房间变成以往警局的特别侦察室。倘若有人误入其中,或许以为N已陷入疯狂。然而他必须如此专注,唯有进入工作状态,他才可稍微缓解对于居所的不安,摆脱往事与幽魂的困扰。唯有进入寻找他人的生死之谜,方可解除他对自身命运的质问。
二
夜里,他研究大楼的平面图,每个出入口、闸门、通道、梯间,甚至连管线都仔细研究。他想起日本人迷恋香港的九龙城寨,曾有建筑师画过极为细密的剖面图,真是令人赞叹。然而那是怎么做到的?如何敲门、拜访,使得这上百户人家愿意让他入内观察?
N揣摩着这栋大楼的生态,真是非得住进来不然便无法理解的。即使入住后,也像是仍在黑暗中摸寻。每一户住屋将门关上,漫长的走道就哪儿都通达不了,电梯与电梯之间连结的只是楼层。他深觉这里或许非常合适他,外观崭新、内里老旧、缺乏管理,彼此不相闻,房租直接汇入银行帐户。关上房门,与谁都无关。
偏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性格,他的工作就不保了。
他打电话、敲门,在对方挂掉电话或“砰”地关上门之前,争取一点点对话的可能,像是推销员。
他想起以前警察的生涯,不知是否受过去的从业影响,他身上具有一股不容他人拒绝的能力。不知是亲和、信任,或威吓?或几者兼有,总之,他身上有什么特质,使他易于从事调查行业。公司里他的破案率比谁都高,但命案对他而言,依然太过困难了。
失去那张警察证件,也意味着失去合理访谈他人的机会。他现在靠的是收买、讨好、死缠烂打。人们真奇怪,心里明知明哲保身、多说无益,但最后,肚肠子里总埋着些什么想说。你得找个方式让他甘心说出来。
他通过过去的工作关系,搭上一个负责此案的刑警,可同步更新最新案情。但光是这样不够,他像一条蠹虫,找到缝隙就钻进去,即使这案情根本是铜墙铁壁。
一个男人的失踪以及死亡,私下到私家侦探社雇人调查的,并非男子的家人,却是一个神秘女子R小姐。R开宗明义即说明自己是男子情妇,两人相恋两年,原本已相约出逃。没想到男子却离奇失踪,甚至意外死亡。
她不相信警方调查所得“自杀”的结论。她自认男子与其相爱,即使要赴死,也唯有与她殉情,而非选择自杀。
三
每一个人的死亡都令N想起他的妻与子,犹如每个人的丧生都与他切身相关。他拯救不了妻儿的丧命,当然也免除不了那些当事人的失踪或丧亡。然而他以介入旁人的死亡为业,彷彿于生死之途中,还能与死神对弈,令那场死亡拥有更多意义。找出某些解答,尽管可能造就更多伤害,但总有人想要答案。即使是令人失望的结论,仍有人愿意为此付出高额代价,例如R。
多年前的N是个将大多数的时间、心力,都投入工作的警察。他有一段堪称美满的婚姻,一個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刚晋升刑事组,人生、事业正值壮年,即将攀上巅峰。他没日没夜地查案,有时几天不回家,妻子没啥抱怨。
直到五年前那个要命的下午,妻子接回放学的儿子,却因在门口与邻居攀谈,疏忽看顾儿子仅短短一分钟。儿子为追逐手中掉落的皮球,松开母亲的手,独自跑向外边马路,被突然急驶而过的汽车当场辗毙。
N的世界崩塌了。
接下来的日子,生活变得如同在水影中、梦境里,真实不再真切,但噩梦从不间断,水光兀自翻映。丧礼后,妻的情绪起伏瞬变,从悲伤自责,逐渐变成愤怒狂躁,而后臻于愈加严重的妄想与幻觉。
妻说她总是看见孩子在屋里四周,每日回得家来,“我没有放开他的手”,妻说,“从来没有。”
妻不再开车、搭车,渐渐不出门。她似乎想藉由这种行为,将时光退回那个下午,她没有因为邻居的寒暄而分心。她不曾放开孩子的手,孩子不曾为了捡球而跑向马路,那辆汽车不曾在要命的时刻飞快驶过。所有阴错阳差不曾发生。时间凝冻在不幸之前。
妻子甚至坦承自己早有婚外情,与公司同事每周一次幽会汽车旅馆偷欢,认为是自己的出轨导致心不在焉,“这是报应”,造成儿子的死亡。
N没看见现场,无论是偷情或死亡当下。但妻子一次一次诉说,他脑中映现出更为清晰的影像,清楚得使他必须闭上眼睛,避免因悲痛而刺瞎双眼。
“别再说了,我都原谅。”他安慰哭号不停的妻,但内心破散无以凝聚。时间催逼着他,来不及为爱子之死悲伤,便要急着挽救可能寻短的妻。生死在指尖交错,谁有罪、谁无罪,已无从分辨。
妻心中日复一日悲伤与懊悔蔓延,演变成对他的叫骂。原来妻子不快乐已经很久,他以为的不抱怨与宽容,只是因为个性隐忍。
妻子越是恨他,就越恨自己;他越安抚,妻子的自责就更深。他几乎弄不清楚自己该如何说话、反应、作为,才可以使儿子活转,让妻子正常。所有事物都来不及,甚至连自己也无从挽救。
丧假结束,他又投入工作,说是手头上的案子正在破案关头。但N知道,自己也在逃避回家,逃避面对妻的崩坏。
N越是痛苦,就越沉溺于办案。一日他回家,妻子留书出走,“别再找我,我看见你就会想起儿子。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他请了长假,开始寻觅妻子。动用一切关系,使出所有本事,花了三个月,才查出妻子落脚于湖东一处旅馆。警方赶到为时已晚,妻子早于那日凌晨烧炭自杀。
此后,N辞去工作,退掉租屋,他无法再居住于任何有具体形貌的“家”中。他早有饮酒习惯,此后花费更多时间盯着酒杯发愣,仰头长饮让血液注入麻醉剂。一年过去,因酒精中毒住院,老爸、老妈在一旁哀哭,以前的搭档发狠痛骂。骂完也是哀戚,苦劝他到以前朋友开设的侦探社工作。
他活着不为自己,去上班也没什么不可,醉生梦死,在哪都行。他又回到职场,当调查员,没警徽,做的也是类似警察的工作。
每次接案,递送“可靠徵信社”的名片,他怀疑自己并不可靠,知道自己还有随时发作的酒瘾与挥之不去的噩梦。但他是那种一旦开始工作,就像狗咬住骨头不放的人,给他什么他都做,都能做得好,非得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奇怪他内心如此荒败,活得毫无半点滋味,却擅长解除别人的难题。
最初做的都是寻人,妻子失踪的那些时光,他找遍了整个中国,他没寻回他的妻。到了徵信社,却协助了各式各样的人们寻获离开的人。
某些男人寻妻、另些女人寻夫,一些心碎的父母寻子、寻女,某些饲主寻找宠物,他做得得心应手,在业界闯出名号。而后,从寻人的过程导入一桩他杀案件,此后彷彿又回到警局的工作,他又出没于他杀或自杀命案的现场,收钱办事。他的角色与过去的警察身份不同,遵循不同规则,却朝向同样的方向。
他一直在不同的寻找与解谜的过程中,将他人断裂的人生故事补缀起来。而他自己的人生,仍停留在家破人亡的当时。
一个人的消失与离开有各种可能与结果,他自己实际上也是个不断设法消失与离开的人。
每一次启动调查,N都会更换一次以上的住所。即使雇主没有支付住宿费用,他也愿意自费租赁旅社、饭店、民宿,甚至只是一个破旧的房间。重点是,他必须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入睡。任何与家无关的地方,他才得以安眠。
他选择的或许是跟被调查人有关的地点,或者,会随着调查不断移动住所,除却收集资料,另也有熟悉环境的用意。离开警局之后,他鲜少对任何地点产生归属感,甚或,所谓的归属感就是他正在逃避的东西。他失婚失业、家破人亡,他搭公车、高铁、火车,或骑着机车,循着失踪人口、离家逃妻或外遇调查等委托案件,穿行在大小乡镇,赚取生活必需,工作尽可能忙碌。
这些迷失或躲在不知何处的男女老少,这世上还有挂记,需要索求着他们,愿意在正规警察系统以外,通过私人委托的方式持续搜寻。而他,已经是无人需要的人了。一个无用、无爱之人努力搜寻着“还有人爱着”的人,这就是个矛盾,N活在这个矛盾里,像躺在一个已经破损的口袋中。
四
被调查人J先生,于今年二月失踪,四月社区清洗水塔时,发现J陈尸塔中。经各方盘查、讯问,因为遗书具备,且死者无外伤,现场也没有打斗痕迹,警方排除他杀嫌疑,认定为自杀。
N虽然收集这些警方调查进度,但委托人R交与他的,是彻底找出与J生活工作上所有相关人士,进行深度访谈。R想要他重建出J失踪前最后一周的生活关系图表,尤其是J的妻子、岳丈、公司合伙人,以及R小姐始终怀疑的年轻情妇“小四”S小姐。
他必须一一访谈名单上的人,这些可能认识J先生的人士,才能给予他想要的讯息。他打电话约访,几乎不曾被拒绝。人人彷彿都带着歉疚,似乎都想要对命案说点什么,而最后说起的总是自己的人生。
五
真相藏匿在话语之外,并不存在所谓的真相。
有一些事物隐藏在另一些事物之中。
为什么有人愿意对N坦露心事,N觉得困惑,也觉得答案再清楚不过。这些他选中的人,与其说被他选中,不如说他们都在等待一个可以开口说话的机会。明明想要躲得远远的,却又忍不住开口诉说,无论是讨论死者生前与他们的交往,或自己的身世。这些都是因为死亡引起的效应,无论是实话或谎言,无论说话动机为何,如今他们都需要倾吐。这些话语埋藏在他们体内,犹如一个会咬啮他们的怪物,唯有一吐为快。
夜里,当他打开录音档,从电脑喇叭反复播放这些他曾听过的声音,那些他已经刻画在心里的形象:脸部线条、五官、皮肤色泽,说话音调、口吻、措辞、表情,一再一再铭刻在他记忆里。
他飞快挥舞手指敲打键盘,记录下听到的一切,就有更多讯息撑开这些看得见的表象,流溢到画面之外。有时他得停下手中动作,聚集心神,让这些说话者停顿。最后一个字句散落在房间里,留下“咿”的尾音,电脑运转声低低鸣响,彷彿那些未被说出的话语还散落在主机里,随着散热器的热风,飘散在房间内。
当他人的生命正在消失或濒临死亡的边缘,当N集中心志建构起当事人所爱、所恨、所依赖、所逃避、所恐惧、所欲望,一切的一切,人事地物,空旷房间里,各式资料、纸张随着空调轻轻翻动。
那些速拍照片、翻印纸张、表格图记,那些录音档里打字记下的人声话语,那些他企图于脑中慢慢建构起的,关于J的生与死、消失与离去,像逐渐升高的塔楼,带送N攀向某个极其危险,又令他感到安全的所在。像一个漩涡,如一朵随风飘送的云,像一只在沙漠里踟蹰的骆驼。
在深夜的瞌睡中惊醒,N突然感觉J先生附体于他,或说,J再现了他一直未能实现的,将生命的所有重量交付于双手,十指交叠印下深深的指痕。临去的一瞬,掷铜板决定这样或那样,那个幽静的午后,时间很足,可以慢慢行事,所有动作都极其悠然,几乎可以称为艺术。
他将绳索调好,套圈于颈脖,开水服下药物,调整身上衣衫,抚顺几日未洗的乱发。将绳圈套紧,踮踮脚下的矮凳,双手构着顶上的铁杆,试试其坚固程度,能否承担到最后一刻。一切都備妥,再没有需要犹豫与反复思量的,感到终于松懈,与某种愕然欢快。
是啊,在此时,过去终于退后。只要松开手,双腿如舞蹈般下蹲,深吸一口气,跃高、后踢、下坠,拉直身体,就可以到达未来。
责任编辑 乌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