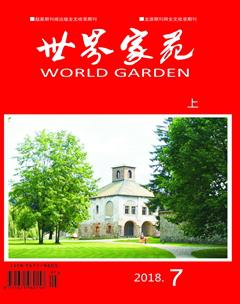《诗》学的嬗变
摘 要: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面世给先秦的思想文化研究又注入了新的生机,其中的《诗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研究《诗》的论著,虽然篇幅不多,但涉及到了今本《诗经》的风、雅、颂三个部分近60首诗作,所以我们可将《诗论》认作先秦诗学的代表和诗经学的滥觞与后世汉儒的治诗进行比较研究,从而窥探从先秦到两汉这段历史中诗学在传承和发展中的流变。王国维先生曾提出做学问的“二重证据法”,既然楚简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笔者也将借此运用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挖掘它的意义。
关键词:上博楚简;《诗论》;毛诗;三家诗
绪论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批楚简公布之后,许多学者已经对竹简的字词考证、类序排定、思想阐发等做出了丰硕的成果,笔者为了更好地理解楚简的内容,参照了李学勤、马承源,廖名春,李零等前辈学者的语言考订成果和陈桐生、晁福林等前辈的专题研究。关于《诗论》的作者问题,前辈已多有论述,基本上可分为孔子作、孔子后学作或孔子作但经后学增补等结论,所以楚简《诗论》又有称为“孔子诗论”者,是通过与《孔子家语》和《说苑》等书的孔子论诗作比照,认定此为孔子所做。又有学者推证《诗论》属于楚简中的《子羔》篇,乃孔门后学所做,对于此种种分歧,笔者不置可否,但十分确定的是,《诗论》乃先秦儒家的诗学代表作,所以已有学者考察了《诗论》与汉代诗学的异同,比如姜广辉先生就认为《诗论》就是“古诗序”,是《毛诗序》的原始本或者前身。然而笔者认为齐、鲁、韩三家治诗比毛诗早出,也曾立为官学,盛极一时,在做比较研究时不应偏废,所以笔者将统括毛诗及三家诗与《诗论》进行比较分析。
[1]《诗论》的本质——从“斷章取义”到“就诗言诗”
《诗论》的出现表明学者对《诗》的本质认识发生了转变。因为《诗》在《诗论》之前早已列为六艺之学,是西周时期贵族士人必须修习的功课,它的应用之广不仅仅体现在日常交流中,更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学习《诗》的话,就不懂得怎样说话和与人交流。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可能难以理解,但当时士大夫日常交流都离不开引用《诗》里的句子,孔子与弟子在平时的问答和解释中经常引《诗》中的句子。《论语·八佾》篇就记载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其中子夏问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句话是出自《诗·卫风·硕人》,与他们所论说的话题关联并不大,但这样以诗为问却得到了孔子的欣赏,认为这才足以见得能够和子夏谈论《诗》了。诸如子夏这样“断章取义”的用诗,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胜枚举,《左传》中更是多达二百多次。比如郑国的大夫子产,就因为十分精妙的引用《诗·郑风·褰裳》中的句子作为外交辞令,而使得晋国放弃了攻打郑国:“晋人欲攻郑,令叔向聘焉,视其有人与无人。子产为之《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叔向曰:‘郑有人,子产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诗有异心,不可攻也。晋人乃辍攻郑。孔子曰:《诗》云:‘无竞惟人。子产一称而郑国免。” 《褰裳》这首诗原本是女子写给情人的表达热烈情感的诗,与国家战事并无关联,而子产根据当时的邦国关系巧妙地引此诗句为外交辞令来告诫晋国,就为国家免除了一场战祸,所以《汉书·艺文志》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周代的《诗》其实是作为一种社交工具而存在的。不论是宴饮外交还是问答应对,引用诗句往往是根据具体的情境进行具体的阐释,或者说,诗句仅仅作为论据证明自己的话语,而不必考虑在引用的时候是否合于《诗》文的本意和原意,若合于原意也不过是凑巧而已。在这个层面上,诗经更像是一部“修辞大全”,不但可以使得言语文雅,也具有说服力。
而楚简《诗论》的颠覆之处在于,它是一部专门对《诗》进行评论的作品,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而仅仅是零散的议论,但有了以文本为中心的自觉。这使得《诗》不再仅以社交工具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被品评,所以说《诗论》的诞生是《诗》的学术化的开端。《诗论》的主要特点就是探求《诗》文本本身的内涵,它的简文评述每一首诗的诗旨大意,简明扼要,没有额外的历史附会。不仅仅局限于此,开头几简是对《诗经》这部作品的总述,将诗与乐、情相融合,比如“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吝言”。以性情礼义来言《诗》,比如“《关雎》以色喻于礼”、“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情爱也”,特别重视《诗》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以《诗论》的立场来看,《诗》在根本上是一种情感载体而非言辞工具。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诗论》开启了专门论《诗》的新学风,改变了之前“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扭转了一直以来世人以《诗》为工具的认知。
[2]诗旨之变——以《关雎》诗组为例
一、《诗论》的“一字论诗”
笔者对于简文的理解主要依据的是马承源先生的释文考,兼采李学勤、李零、庞朴等诸说。第一简为总结整个《诗》的本质特征,引出下文具体的评析。第二到四简概括《讼(颂)》、《大小夏(雅)》、《邦风(国风)》这四大类的主旨,我们可以称之为“诗大旨”以别与具体诗目的诗旨,在其后的简文里,则是对具体的诗目进行评论。鉴于楚简涉及到的诗篇达六十篇之多,所以本文仅择取第十简《关雎》诗组七首进行分析,从第十一简到第十六简都是对第十简诗组的进一步详细发挥,相比之下这七首诗所占比重较大且内容具体详实。《诗论》论诗的主要方法就是概括诗旨,在这点上和汉代诗学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它的诗旨十分简明扼要,全部一个字来定诗旨,即所谓:“《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这种用一字论诗旨的方法是《诗论》所独有的特点,虽然简短但皆十分精当。
二、汉代四家论诗
提及汉代诗学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当时的儒者是否还看得到《诗论》,是否受到了《诗论》的直接影响?就目前的《诗论》内容来看确实有一些联系,比如将诗经分为“四类”来论诗大旨、通过概括诗旨的方式来论诗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可以推知就算没有直接影响也是有渊源的。
汉诗的四家分别是属于今文经学的齐、鲁、韩三家诗和古文经学阵营的毛诗。鲁诗是汉初今文三家中最早兴起且足具影响力的一家,由鲁地的申培公传承,《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曾有《鲁诗》、《鲁说》传世,不过早已亡佚,就《诗三家义集疏》来看,依然存有《风》、《雅》、《颂》的诗大旨和部分诗文的诗旨。而齐诗由辕固生传承,《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留下的文献最为稀少,《汉书·艺文志》所载的《诗经齐家》、《齐后氏故》、《齐杂记》 等都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对齐诗的理论可以说基本无从得知了。韩诗由韩生而传,《史记·儒林列传》:“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目前仅存《韩诗外传》,但它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韩诗的特征是以诗明史,通过诗词来讲明历史,而非用历史来解释诗。至于毛诗,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传诗者为大小毛公,但是未明姓名,直到陆机的《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才指出大小毛公为毛亨、毛苌两兄弟。毛诗虽然兴起最晚但是影响力远在三家之上,且只有它留下了完整的文献,并且由于东汉马融、郑玄、王肃等为之作注,在之后的历史中一直占据主要地位。
三、《诗论》与汉代诗学的异同
下面将通过对具体的诗篇的比较来呈现诗论和汉四家的异同。
1.《周南·关雎》
《诗论》:《关雎》之改。《关雎》以色喻于礼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口口口口口口口好,反纳于礼,不易能改乎?《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
“关雎之改”原作“攺”字,马承源先生训为“怡,认为“关雎是贺新婚之诗,当读为怡,怡和攺双声叠韵……怡当指新人心中的喜悦。”而李零先生将“攺”解读为“君子妃配”,笔者猜测李零先生可能受到了毛诗序的影响而有此说。李学勤先生将“攺”训为“更易”。如果结合后文的“反纳于礼”来看,李学勤先生的说法更为合理。诗论认为关雎虽然表面描写男女情事,实际想要凸显的是礼,“其四章则喻矣”说的就是关雎的第四章写“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琴瑟和钟鼓都是礼乐的代表,君子虽然渴慕佳人美色,但最终是决定按照正式的礼节来求得,和最初相比当然是“改”了。而“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益”是形容“思”的程度之深,毕竟君子已然“寤寐思服”,正因为情不可抑制所以才归于现实中的礼义。
2.《周南·樛木》
《诗论》:《樛木》之时。《樛木》,福斯在君子,不亦口口口时乎。《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
对于“时”的解释是难点,李零先生将之解释为“遇其时,运气好”,马承源先生认为应当读作“持”,李学勤先生解释为“会”,就是“时会”之意,君子获得福禄证明碰到了好的时会,恰逢其时。《樛木》这首诗反复出现“福履绥之”,“福履将之”,“福履成之”这三句,所谓的“福履”就是福禄的意思,所以说这首诗显而易见是古人对他人表达祝福的作品。所以说“福斯在君子”。
鲁诗和韩诗对此首的诗旨缺佚,故不论。
齐诗:《文选》班固《幽通赋》:“葛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曹大家(即班昭)曰:“《诗·周南·国风》日:‘南有樛木,葛蕞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此是安乐之象也。”齐诗认为这首诗讲的是君子十分安乐的境况,
毛诗:“《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也。”按照毛诗的理解,樛木写的是后妃能和众多妻妾和谐相处而无嫉妒之心,“逮下”就是说能将恩惠施于下人。
3.《周南·汉广》
《诗论》:《汉广》之知。《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汉广》不求不]可得,不求不可能,不亦知极乎?
基本上各家都認同将“知”训为“智”,这也符合文字的发展规律。诗文有“汉之游女,不可求思”的句子所以诗论说“则知不可得也”,《诗论》认为意识到不可能求得的事情就不去强求,这是最明智的。
鲁诗和齐诗对此首的诗旨缺佚,故不论。
《韩叙》曰:“《汉广》,说人也。”说,当为“悦”的异体字,根据陈启源的解释:“韩叙‘说人夫说人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即韩诗认为汉广将的是对女子的倾慕之意,但因为只能见到而不能得到,仰慕之感就更加显著了。
毛诗:“《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根据郑玄的解释,认为商纣的时候淫风遍及天下,只有江汉这个地方因为受到文王的教化而没有被污染,所以女子才有贞洁的德行,不会不顾礼仪,所以才使男子“求而不可得”。
4.《召南·甘棠》
《诗论》:《甘棠》之保(报)。……及其人,敬爱其树,其保(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 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
保训读为“报”,对于《甘棠》写的是召公的事迹想来都没有异议,召公为百姓做好事所以百姓为了表达敬爱之情就不砍伐他曾经处理政事的那棵树,这也是“爱屋及乌”,因人及树,是为了报答召公之恩。
鲁诗:《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白侯伯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甘棠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刘向《说苑·贵德》:“《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伯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扬雄《白虎通·巡狩》:“言召公述职,亲税舍于野树之下也。”应劭《风俗通义》:“当农桑之时,重为所烦劳,不舍乡亭,止于棠树之下,听讼决狱,百姓各得其所。寿百九十余乃卒。后人思其德美,爱其树而不敢伐,《诗·甘棠》之所为作也。”
齐诗:《初学记·人事部》引《乐动声仪》:“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分职,常战傈恐惧,故舍于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后乃与圣人齐,是故《周南》无美而《召南》有之。”
总结来说,除了《甘棠》一诗的诗旨没有发生变化以外,对其他诗篇的诗旨解读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迁,其一是《诗论》对《诗》的解读还没有太多美刺的说法,基本都遵从诗文本义,没有汉代独有的王道教化特征。其二是《诗论》比较重视“以情解诗”,同时期的出土竹书中也多有谈及“性情”关系,在诗论看来,情是“民性”所当然,顺情才成礼,所以对情是秉持一种积极的态度的,而汉代解诗对“情”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为了谨防流入“淫情”的境地,都避免在论诗是用情感之说,比较多的都是讲道理,论美刺。
[3]诗教之变——诗学的经学化过程
通过对《关雎》诗组的诗旨流变分析,可以看到对大部分诗文的解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诗论的解释更多从情感上感发,并没有过多的附会史事和讲道理。《礼记·经解》篇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更大程度是指的是个人修养而言,善读诗则有温裕之象,而汉诗尤其是毛诗,惯于以史附诗,从而引出“美刺之教”,这是立足于社会道德而言。所以说在事实层面上,从《诗论》到汉代诗学,经历了由个人到社会,由“情感诗学”到“政治诗学”的转变,也正因为如此,汉诗才发展成完备的经学体系,我们将《诗》称之为“诗经”而非“诗集”就是因为它不仅仅只具有文学性,不仅仅是用来“抒情达意”的辞章而已,尤其是毛诗,它构建的政教体系把上至君王、下至黎庶,都被囊括在内,即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后儒批评毛诗为了说教而牵强附会的确不无道理,与先秦早期的《诗论》体系相比,它的为学路径和目的确实发生了本质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第一版
[2]马瑞辰撰:《毛诗传笺通释》,中華书局,1989.3
[3]程俊英撰:《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07月第1版
[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6]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7]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8]晁福林著,上博简《诗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10,第3页
[9]廖名春:《新出楚简试论》,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2001年。
[10]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04月第1版
作者简介
张彤颐桢(1992—),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在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宋明理学。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