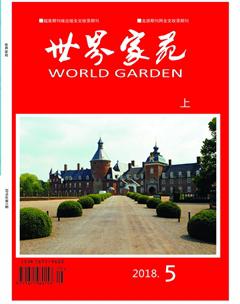从多元系统论谈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摘 要:本文介绍泰戈尔在中国的两次热潮中的作品翻译情况中译介重心的不同,并根据多元系统论分析重心不同问题背后的原因。说明文学系统的变化与不同时期的思想意识、赞助人与诗学会对翻译作品的类型、题材、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译语文学的文学系统也会因翻译行为而发展。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泰戈尔;译介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伟大的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1913年,泰戈尔凭借抒情诗《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东西方世界开始瞩目泰戈尔的文学成就,其作品也被译介传播。从20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中国先后掀起三次泰戈尔研究的热潮,先后有一大批作家与学者受到泰戈尔创作与思想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流注于创作实践中,促进了新诗的发展与一大批作家文学思想的形成。然而,第一、二次泰戈尔研究热中,对泰戈尔作品的译介重心并不相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第一次泰戈尔热中,诗歌是译介的重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二次热潮中,小说则是译介的重点。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会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现象?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思想意识、赞助人的力量、诗学分别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国最早介绍泰戈尔思想的文章,是钱智修的《台峨尔氏之人生观》,刊于1913年《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四号,文章引用泰戈尔的话,介绍了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成泰戈尔是“献身于国家,献身于人类之福音者”。[1]于此同时,日本掀起第一次“泰戈尔”研究热,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后,开始世界巡回演讲,准备于1915年访日,日本人因此表现出极高的热情,1915年,各大报纸、杂志都用大量篇幅介绍泰戈尔的作品、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同年,日本翻译出版了15部泰戈尔的作品。诗歌翻译方面,泰戈尔的几部重要的散文诗集,如《新月集》《园丁集》都被翻译成日文。许多剧本如《暗室之王》《邮电局》等也都有了日译本。苏野绿郎、秋田实、小松秀树等还翻译出版了《泰戈尔杰作集》。这段时间翻译泰戈尔作品最多的是增野三良,共翻译了《泰戈尔的新月》、《吉檀迦利》《迦陀的捧物》《幼儿的诗集——新月》《印度新抒情诗集——园丁》5部作品。此外,吉田絃二郎翻译的《泰戈尔的哲学和文艺》《泰戈尔的诗和语言》介绍了泰戈尔的美学和宗教观念。这一年,泰戈尔的研究专著也出现了10部。冈田哲藏著《泰戈尔的奉纳歌》主要介绍了泰戈尔的代表作《吉檀迦利》;中泽临川在《泰戈尔与生的实现》《梵的行者泰戈尔》中研究了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与印度传统文化及宗教的传承关系;江部鸭村的《泰戈尔思想与宗教》研究了泰戈尔的“人格”及“诗人的宗教观”;斋木仙醉一年内出版了3部有关泰戈尔的专著,《泰戈尔的歌》《尤毕如与泰戈尔》 《泰戈尔的哲学》;吉田絃二郎的《圣者泰戈尔的生涯》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2]
在那个年代,中国有志青年留学日本,日本的文学思潮一直影响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郭沫若在日本求学的过程中接触到泰戈尔的作品,沉醉于泰戈尔诗歌清新、恬淡的风格。郭沫若曾说过“我在岗山图书馆中突然寻找到了这几本书,我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并写诗赞美泰戈尔。1917年,郭沫若还从《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中选译了一部《泰戈尔诗集》。对泰戈尔研究的热潮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在国内,陈独秀则是我国最早介绍泰戈尔作品的人,他于1915年10月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二期上翻译发表了泰戈尔的四首短诗,题为《赞歌》,选自《吉檀迦利》。[3]随后,张闻天、郑振铎等人最早較为系统的介绍了泰戈尔作品和泰戈尔思想生平。对泰戈尔进行长期不懈地介绍和研究的是文研会发起人之一的西谛。他于1922年翻译了《飞鸟集》,这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泰戈尔诗集,1923年又翻译了《新月集》。1923年到1924年期间,他同沈雁冰等人主编的《小说月报》曾三次出版了泰戈尔专号,刊登了泰戈尔的许多诗歌、小说和戏剧的译作和文章。1924年泰戈尔访华,掀起第一次研究泰戈尔的热潮,对泰戈尔诗歌、戏剧与小说与文学思想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冰心作为文研会的成员,也较早的接触到了泰戈尔的作品,她欣赏泰戈尔作品中体现的“爱的哲学”以及自由短小的诗体,这也对她的“小诗体”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新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24年,泰戈尔来华访问,对泰戈尔研究的热潮也到达顶点,并于泰戈尔离开中国后逐渐冷却。
可以说,泰戈尔的诗歌对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歌创作影响广泛,当时的新诗人或多或少受到泰戈尔的影响。这首先与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关,五四时期的文学处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初期,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现存的文学模式不再站得住脚,这样的历史时刻,翻译文学会取得中心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急需建立新的文学范式,推翻旧文学传统,建立新的符合时代发展的传统势在必行,这种转折点导致本土存储的文学内容不再被接受,出现文学真空的结果。回顾五四,苏俄文学、欧美文学与日本文学的译介纷纷进入中国,各种文学潮流和文学进程的发展也紧随翻译文学的大势。这种文学的“幼嫩”状态与“边缘地位”为泰戈尔诗歌的接受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泰戈尔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东方作家,其创作的文学传统与思想(泛神论与泛爱思想)易被中国作家认同,同时,泰戈尔在当时不断发出反对殖民侵略和不正义战争的声音,这也贴合中国文人的思想意识。从诗学的角度来说,泰戈尔诗歌自然清新、真挚而深情,诗体短小自由与新诗运动的发展趋势相一致。1923年,成仿吾在《创造周报》第一期发表了《诗的防御战》反复强调了文学与诗的抒情本质。郭沫若的《女神》正是充分体现这种理论主张,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重视与发挥。这与泰戈尔诗歌的抒情性一致,同时,泰戈尔诗歌的小诗体也有利于表达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冰心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了泰戈尔的诗作,并从中汲取灵感,创作了《繁星》、《春水》,丰富了新诗的形式,自由诗体的句法和章法也在这种模仿式的创作中趋于简化,这些都对新诗的发展有过渡意义。[4]郭沫若也曾翻译泰戈尔的作品,他在《创造十年》中指出:“因为喜欢泰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思想接近了”,在诗歌风格上“先是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5]郭沫若是新诗的代表诗人,他的作品开创了新诗新的范式,这与泰戈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说明当翻译文学满足了较为幼嫩的文学的需要,使其将新建立的(或新修复的)语言方式运用于尽可能多的文学类型,使其成为有效的文学语言,并对新出现的读者群体有所助益。
同样是泰戈尔的作品,对泰戈尔小说的译介却并没有引起译者与作家群体的重视,这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1918年,鲁迅于《新青年》第4卷第5期发表《狂人日记》,“五四”小说拉开序幕。《狂人日记》等现代小说以反封建的精神直指人的现代觉醒和国民灵魂改造,这让中国现代小说从一开始就肩负了城中的社会使命。其次,“林译小说”早开翻译风气,有以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为代表直译了日俄和其他小民族的小说,影响了“五四”小说的内容、形式以及风格。因而在泰戈爾小说作品传入中国时,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范式已经初具雏形,且泰戈尔小说的诗化语言和抒情风格和生活题材与当时中国的“现代觉醒”和“灵魂改造”主题并不契合,因此无法得到读者的认可,也不能引起译者的重视。另一方面,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考虑,泰戈尔小说作品由孟加拉文写作而成,语言的使用并不广泛,因而作品的传播也多靠英译本二次翻译而成。当时的英语文学世界较重视泰戈尔的诗歌而非小说,这也减少了小说的翻译,因而泰戈尔的小说作品也并未能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线之中。直到第二次泰戈尔研究的热潮,泰戈尔小说的作品才得到重视与系统的译介。
当第二次泰戈尔研究热潮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文学的系统已经成型并确立,翻译文学此时处于边缘地位,它对重要的文学进程不产生影响,它所模仿的是译语文学中的主导类型早已确立的传统规范。此时,翻译不再是向文学引入新观念、新内容、新特点的方式,而是维护传统品味的方式,这时对泰戈尔的小说作品由于契合我国的反帝反封建文学传统而得到重视。颜治强在《泰戈尔翻译百年祭》提到,在泰戈尔逝世后中国掀起第二次泰戈尔翻译的热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时黄星圻翻译了《戈拉》,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泰戈尔百年诞辰之际出版十卷《泰戈尔作品集》,收录《戈拉》为了反映泰戈尔的反殖民主义与反封建精神,表现泰戈尔的进步思想。黄健平在《接受学视野下的泰戈尔研究》 提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泰戈尔的《沉船》、《戈拉》、《小沙子》、《四个人》等长篇和中短篇小说相继译成中文。书中反抗阶级压迫、倡导平等博爱的思想又与中国当时的社会语境相符合,加上泰戈尔不时对中国革命战争发表声援,因此,中国又再次掀起了泰戈尔热得到广泛的认可。作出翻译的选择,赞助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长期把反帝爱国作为意识领域的重点表现主题。译者与赞助人的关系中,译者享有的出版自由度很小,赞助人依靠职业工作者使文学进入自己的思想意识。意识形态决定了在泰戈尔诞辰百年之际,这位为亚洲和东方崛起的伟大人物必将受到中国的重视,这其中,体现反帝爱国思想元素的作品更将成为翻译的重中之重。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戈拉》的翻译和解读都以“反帝爱国”主题为中心。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按照赞助人的要求,将书中的人物与情节进行明显的政治性改写,一些原作品中不体现政治立场的人物,在译作中进行了语言和情节的改写,学者也只从政治角度对泰戈尔的小说作品进行解读。于是译作中的人物与情节不无矛盾之处,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很深的关系。这种操纵与改写一直到新世纪后的第三次泰戈尔翻译研究热才得以纠正。
通过泰戈尔作品在中国译介的两个阶段可以得知,文学系统的变化与不同时期的思想意识、赞助人与诗学会对翻译作品的类型、题材、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译语文学的文学系统也会因翻译行为而发展,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去研究。
注释
[1] 孙宜学:《诗人的精神——泰戈尔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
[2] 吴毓华:泰戈尔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初探
[3] 倪培耕:《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4]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 倪培耕:《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侯传文:《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唐仁虎:《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年。
[3]潘一禾:《故事与解释—世界文学经典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4]黎跃进:《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东方出版社,2002年。
[5]孙宜学:《诗人的精神——泰戈尔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
[6]倪培耕:《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7]艾丹: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泰戈尔热”——五四学界对泰戈尔的译介与研究。
[8]吴毓华:泰戈尔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初探。
[9]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郭艳艳(1993—),女,汉族,籍贯:天津,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