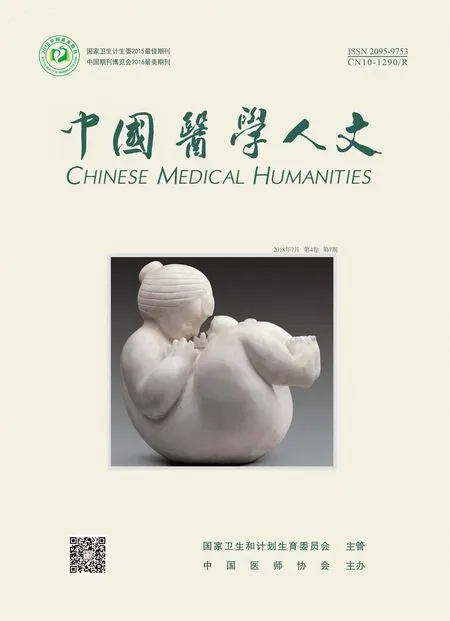书信中的医患缘契
文/秦泗河
书信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在信息时代来临之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要么被地理所阻隔,要么被时间所淹没,能够超越时空限制的沟通途径只有一种,那就是书信往来。我们这个民族尤其钟爱写信,从司马迁《报任安书》的矢志不渝,到李白《与韩荆州书》的豪气冲天,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杜甫仍在吟咏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千百年来,中国人把最可贵的品质、最美好的文化都留在了书信当中。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开始在山东苗山公社医院开展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矫形外科工作,当时在基层小有名气,逐渐就有一些患者闻风而动,写信求医。我在昏暗的灯下拆开信封,那些质朴的字句就迫不及待地跳入眼帘,大声诉说着执笔人患有什么疾病、历经了多少苦难、多么渴望得到救治,满怀希望又唯恐其破灭的心情溢于言表。每读完一封信,我都像听到了自己的使命似的,反复推敲,仔细揣摩写信人的病情,把来信重新折好,小心保管,然后再工工整整地写回信。并不是写几行字那么简单,有时候回一封信,像做一台手术一样郑重其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书信文化早已融入我们中国人的血液了。
80年代我调到黑龙江佳木斯市,创建矫形外科医院,接受国家下达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抢救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那时候一年的手术量最多达到2 000台。随着矫形外科手术的广泛开展,报纸、电视等媒体的持续聚焦,患者来信也开始急剧增加,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求医信件,寄信人早已不限于本省患者,而是遍布全国各个省份,远到新疆克拉玛依、云南红河,都会“鱼传尺素”。通过书信这个小小的媒介,他们用同样的文字,怀着同样的心情,把各不相同的境况送到了我的书桌上。那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前夜,有人已经开始尝试使用电子邮件,而我还是用最传统的方式,每天晚上伏案读信,每封必回,算起来,我写的回信也已经上万了。后来互联网的浪潮席卷全国,年过半百的我也学会了上网,不知不觉中告别了纸质书信。
有一次我到西安做学术演讲,演讲结束时,突然有一位中年妇女从后排座位跑上前台,送给我一包鞋垫,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直到后来我读到她的寄语——“秦大夫,是您为我做了儿麻矫形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这次手术对我的人生有着非凡的意义!20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当面向秦大夫说声‘谢谢’!我偶尔看到附属医院贴在门口的海报:秦泗河教授来医院讲课!我非常的激动!圆了我多年的愿望!那十几双鞋垫是我老母亲早就缝制好的,老人家经常念叨让当面赠送您,今日圆了老人的心愿了……”不用回顾她的治疗过程,也不用展示她的人生蜕变,只需数一数这段话里有多少个感叹号,最朴实的感恩、最饱满的情感,都在里面了。
上万封书信来往,饱含情怀。时至今日,这些老信件我一直舍不得丢弃,把它们装了满满的几个大箱子,珍而重之地保存着。有时候打开箱子,随意翻看几封,往往还会有新的发现。例如,我看到有的患者写道“只要得到您的消息,不论天涯海角,哪怕是爬,我也要找到您!”字里行间透露出坚韧不拔的性格。有的家属写道“每到下雪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些刺痛,想着姐姐走在湿滑的路面,一步一拐地去上班……”手足之情跃然纸上。
正如很多人在来信中所诉说的,肢体残障患者往往遭遇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生活备受挫折,记得有一封信一开头就写“您好,秦大夫:我有一桩非常痛苦的事情讲给您听……”然后一桩桩往事依次叙述,把多年的压抑都倾泻了出来,越写到后面,字体越草,笔画越重,悲愤交加的神态如在眼前。
还有一位朝鲜族的姑娘,对中文不太熟悉,求医信上有很多错别字,但每个字都写得非常方正,仔细分辨,还能看出她是一笔一笔描上去的,可以想见,当时写这封信费了很大的工夫。每每打开这封信,我都能看到她聚精会神、小心翼翼的样子,不由得为之感动。这也是书信的魅力所在,字迹本身就携带了很多信息——信息科技体现不出来的信息。

图为一位爬行29年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的来信
信件中偶尔闪现出来的艺术火花,同样让人眼前一亮。我收到过好几封书法极美的信,都是用潇洒的行书写成,有的甚至是繁体竖排,加上半文言的语句,时不时还能押韵,虽然也是描述病情、询问治疗意见,读起来却多了几分诗情画意。还有很多患者为了把畸形情况解释明白,就直接把自己的腿和脚画在信纸上,其中美术功底出众的,连趾甲、毛发都画得清清楚楚。有人还在小腿肚、脚后跟涂上阴影,画出了光影效果。这些栩栩如生的作品,自然也是信中翘楚。
这种故事成百上千,如果都罗列出来,恐怕写一本书都讲不完。问题就是老信件太多,留心关注的人又太少。现在手写书信的时代已经结束,更新奇、更快捷的通讯手段层出不穷,随着无线多媒体、量子通信等新技术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连电子邮件都会被淘汰,谁还会记得书信呢?如果再不加以整理和总结,这些旧信件很快就会消失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永远湮没无闻。因此,我委托办公室征调专人对这些旧资料展开清查、阅读和扫描归档,期望这些历史资料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