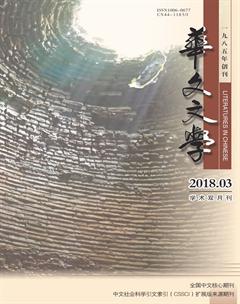余光中诗歌接受生态辨析
摘要:余光中诗歌的研究要走向深入,接受研究正是一条重要而必要的途径。人们对作品接受的3个层面一般是: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研究,作为普通读者的情感审美的阅读欣赏,作为创作者的传承吸收和摹仿借用。与此相联系,余光中诗歌接受生态的考察也就在以下几个方向展开:阐释研究,阅读研究,影响研究。尽管余光中自己非常想把他不仅仅是诗人、不仅仅是“乡愁诗人”的多面体呈现给世界,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接受与学术接受不同,与文学接受也不同,它只认定这个对象最醒目的那一面甚至那一点,这就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片面接受的正当性”。
关键词:余光中诗歌;接受生态;片面接受的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3-0105-07
无论是创作的品质和数量,还是文学活动的多样性和影响力,余光中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均位居前列。在近70年的文学创造活动中,余光中贡献了一批瑰丽多姿的文学作品和富于创见的学术著作,其诗风文采已经远远越出台湾,在大陆、香港、澳门乃至整个华文世界都拥有众多读者。余光中首先是一位诗人,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也首先是他的诗歌。从《舟子的悲歌》到《太阳点名》绘成他右手的掌纹,近70载的耕耘,掷地有声地归之以煌煌20部诗集,引起中外文坛持久的关注。余光中创作了在华文世界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乡愁》等,正如台港文学研究专家古远清所说,论作品之丰富、思想之深广、技巧之超卓、风格之多变、影响之深远,余光中无疑是当代诗坛成就最大者之一,他是中国当代大诗人之一。这一论断指出了余光中诗歌能够在多方话语中游刃有余的内在质素,余光中诗集的畅销和评论研究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标明了余光中在读者中和学术界难以忽视的地位,余光中及其诗歌已然从学术界突围走向民间大众,余光中诗歌在雅俗共赏中被戴上了经典的桂冠。
余光中在备受尊崇的同时也备受争议,海峡两岸部分学者、作家质疑“余光中神话”的声音从未停歇。余光中2017年12月14日在台湾走完了生命的历程,对此海峡两岸的反应差别也较大,在大陆,《余光中:民族美学的传承人》①这样的主流知识界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余光中》之类的网络文章同样令人注目。余光中经历过一系列论战的洗礼和考验,尤其“向历史自首”后,他还能傲视文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屹立不倒吗?本文试图对余光中诗歌丰富而复杂的接受史实作一番简要的梳理和辨析,揭示出余光中诗歌的接受生态。
余光中诗歌的研究要走向深入,接受研究正是一条重要而必要的途径,诚如姚斯所说:“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②人们对作品接受的三个层面一般是: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研究,作为普通读者的情感审美的阅读欣赏,作为创作者的传承吸收和摹仿借用。与此相联系,余光中诗歌接受生态的考察也就在以下几个方向展开:阐释研究,阅读研究,影响研究。当然,这几个维度是一体多面,各具殊相而又浑然一体。
一、以学者为主体的阐释接受
余光中诗歌在大陆、台港澳及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处于持续绵延的状态,从各种选录和品评来看,余诗始终是选家、评家乃至史家视野中的亮点。关于余光中的评论早在1950年代即已开始,著名余学专家黄维樑编选的《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一书收集了1979及以前的评论、介绍、访问余光中的文章目录近二百个,例如1950年代台湾诗坛关于余光中的评论有两篇皆出于梁实秋之手,第三篇是洛夫1961年发表在《现代文学》第9期上的《“天狼星”论》。其后仍由黄维樑主编的《璀璨的五彩笔》又收录了1979至1993的四百余个,两本评论集共计六百多项。2014年香港又出版黄维樑的《壮丽:余光中论》收集他数十年来的余光中评论近50篇,本书的评论兼顾余氏诗歌、散文、批评和翻译各种文体,议论之外,还有丰富珍贵的图片和其他资料。研究余光中的专著有1998年香港出版的钱学武的《自足的宇宙:余光中诗题材研究》,2002年台湾出版的陈幸蕙的《悦读余光中》,傅孟丽的《水仙情操:诗论余光中》,2006年大陆出版的梁笑梅的《壮丽的歌者:余光中诗艺研究》,2008年出版的古远清的《余光中评说五十年》等等。大陆还有数以千计的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几十年间研究者不同的地理政治文化背景给余光中研究带来丰富的视角,对余光中的跨文化写作有比较准确合理的理解。诗评家对余光中诗歌的创作根源、诗旨内涵、风格演变、审美意义等进行分析阐释,其中文本反思与批判的声音比较稀少微弱,但有《诗意不够贯通的〈乡愁〉——余光中的〈乡愁〉指瑕》③之类的存在。
余光中作品的阐释接受之外,余光中传记的书写也是其诗歌接受生态中的有机部分。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君华著《望乡的牧神:余光中传》(2001年),徐学著《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2002年),王尧著《诗意尽在乡愁中》(2003年),傅孟丽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2006年),古远清著《余光中:诗书人生》(2008年),余光中早已进入了历史,传记文学为读者看到一个全面而又真实的余光中提供了丰富鲜活的研究资料。
不能回避的是,两岸四地及其他地区的“非余”现象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批判余光中的浪潮也从未平息,余光中“历史問题”的研究成为余光中阐释研究的热点之一,人们对“余光中神话”从力捧到质疑再到理性还原,为构建一个理性、动态、综合的余光中及其诗歌接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给中国的肌肤烙上了永远的伤疤,在大陆文革结束的时候,与大陆相隔一道浅浅海峡的台湾掀起了一股文坛上的轩然大波。1977年至1978年,台湾发生了激烈的“乡土文学”论战,唇枪舌剑的背后,是剑拔弩张、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这场论战由彭歌揭开语幕,余光中《狼来了》一文把争战的矛头直指乡土作家们,甚至扣上了一顶“台湾工农兵文艺”的帽子。此文一出,一片哗然,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等人的群起而攻之,连那些与此无关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撰文批评余光中,但余光中却得到了政界的支持。台湾文坛和政坛交织在一起,给人以“风声鹤唳”之感,浓厚的火药味让人们深深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见解有分歧的文学争战,而且是两种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
20世纪70年代余光中被美国盛行的摇滚乐深深吸引,这种异国诗乐有别于他所坚持的中国传统诗文之美,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1974年余光中出版诗集《白玉苦瓜》,民歌手杨弦将其中的《乡愁四韵》、《江湖上》、《民歌手》等诗先后谱曲,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推送,余光中亦登台朗诵诗作。这种融合西方现代音乐元素表现传统故乡情的新形式大获好评。对余光中来说,文学和音乐的巧妙结合是现代诗突破羁绊的新路径,同时也开启了自1975年后蔚为风潮的民歌运动,但这种“以诗入歌”的模式却引来非议。不仅学院派的和非学院派的音乐人针对各自论述的所谓民歌“正当性”进行多次交锋,甚至余光中本人的诗作也被冠上了病态“现代诗”的称号,认为余光中在流亡心态与崇洋意识的支配下,发出了现代工商业社会下被歪扭、灼伤、虚弱化的心灵呓语,甚至认为余光中的作品传播色情主义和颓废主义。④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余光中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了一条很好的道路。与乡土文学论战一样,余光中又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余光中是个大才子,骨子里透着清高和桀骜。他重评朱自清,断然否认朱氏的大师地位,并找出了种种理由批判朱氏散文和新诗,引起了文坛的一阵骚动。颠覆大师地位非同小可,余光中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种种质疑,不仅如此,余光中没有放下批判的“利剑”,又向戴望舒、艾青等大詩人“刺”去。余光中种种超乎寻常的表现引来了文坛一片征讨之声。于是,余光中又陷入了文坛争战的漩涡之中。
20世纪末,余光中的一些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的作品也早已赢得了大陆读者的认可和追慕,但有些人还记得那场“乡土文学”论战,对“余光中热”颇有微词。2004年余光中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3年度散文奖”,此事顿时引起文坛地震,台湾学者李敖抛出余光中是“骗子”,并将其诗进行全面批评,并指出大陆对于“台湾历史和文学史无知”,由此在大陆引发一股研究余光中“历史问题”原因及影响的热潮。以赵稀方的《视野之外的余光中》为开端,把论争矛头直指余光中的“历史问题”,也认为目前的“余光中热”是由于大陆读者对于台港历史和文学史的无知,让稍有一些港台文学知识的学者感到惭愧,紧接着他又发表《是谁把余光中推向了神话?》,此文把论争推到了高潮。陈子善、陈漱渝、吕正惠等学者也相继发表文章,认为大陆读者应该反思,对余光中的“历史问题”应该予以重视。针对此现象,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也呼吁,对余光中不应该“翻老底”,不要以偏概全否定余光中的艺术成就,从而误导读者。古远清站在特定历史的角度给出了这样的评论:“台湾政治的复杂迂回,使得很多问题不能简单下结论。在台湾,过去反共很激烈,现在因为憎恶台独,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因而态度一变而为亲近大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吊诡的现象,粗看颇难理解,细想却很自然。对于台湾文坛过去的恩恩怨怨,不必看得过分严重。”⑤这就是著名的“余光中事件”。我们是尊重历史的,就要历史地看待这个事实,余光中终究在反思与借鉴中完成了人性改造和文化人格的重建。
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文学史的书写将余光中的接受推向深入,学术精英们对余光中及其诗歌的阐释基本上是秉承严谨客观的治学态度,试图向历史还原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余光中形象。余光中诗歌的学术阐释历程表明:只有在理解的历史进程中才可能逐步展示作品的全部意义,当下的重新思考和再阐释并非意味阐释的从此终止。选家、评论家是余光中诗歌接受的“理想读者”,他们在各个时期以独特的审美视野,创造性地发掘作品的潜在意蕴,从而使经典作品通过不断的解释积累了丰富的史料。无论是个别诗学家的专著还是集体的编写,在研究者的眼中余光中都是一个矛盾、复杂的存在,他们既纠结于是否让余光中入史或如何归属,又徘徊在真实的余光中之外,对余光中的阐释仍处于未完成的阶段。
二、以普通大众为主体的阅读接受
普通大众对于余光中诗歌的接受显然是在精英学者与官方话语筛选和过滤后进行的,但由于传播媒介的发达和读者自身的差异,他们的接受方式更为自由和自我,因此大众空间中的余光中诗歌接受显得更为明朗纯粹。余光中是极少数以“台湾诗人”身份享誉中国内地和香港等地区的创作者,余光中诗歌持久有效的传播效果是通过静态和动态的传播形式实现的,尤其在大陆,余光中享有“乡愁诗人”的桂冠,可见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文学接受总是片面的,尽管余光中自己非常想把他不仅仅是诗人、不仅仅是“乡愁诗人”的多面体呈现给世界,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接受与学术接受不同,与文学接受也不同,它只认定这个对象最醒目的那一面甚至那一点,这就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片面接受的正当性”。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论证这种正当性,并且分析这种片面接受的形成史和触发机制。
地理空间和与之相关的文化身份是需要首先考量的重要因素。华文诗歌创作地理与传播地理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想象的读者在创作者自己缺席的地方,越是有影响的华文诗歌,其热播地点往往越是偏离于创作者的活动地理。由于文化交流的隔绝及余光中独特的游学经历,余光中最初是以香港诗人的身份被推介到大陆,1980年香港诗人林佑璋评论说:在亚洲进行中文文学创作的地区范围内,现代主义诗人中“余光中是较有代表性的”⑥。此后大陆学者作家开始陆续推介余光中诗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流沙河和李元洛。流沙河时任《星星》诗刊主编,1982年1月,“台湾诗人十二家”专栏正式开始,每月评论一位,1983年他整理出版了《台湾诗人十二家》,这本台湾诗歌评论集影响巨大,尤其是对余光中诗歌大力推崇,流沙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余光中的诗评,其中最早的是《溶哀愁于物象——余光中:〈乡愁〉》,流沙河以一个诗人与诗评家的双重身份对《乡愁》给予了高度评价。李元洛在《名作欣赏》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1982年的《海外游子的恋影——读余光中〈乡愁〉与〈乡愁四韵〉》,1984年的《盛唐的芬芳现代的佳构——余光中〈寻李白〉欣赏》,对于已在大陆文艺集会上被多次朗诵的《乡愁》,以及被《台湾爱国怀乡诗词选》收入的《乡愁四韵》进行了辨析,并对余光中的生平、诗歌创作以及在港台的影响进行了简介,认为“余光中的乡愁诗是我国民族传统的乡愁诗在新的时代和特殊地理条件下的变奏,他的乡愁诗概括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感情。”⑦也正如1980年聂华苓在访问大陆时评价余光中的诗歌:“他的诗充满怀乡的情绪”。⑧《福建文学》也开辟了台湾诗选专栏,在1982年11期的“台湾文学之窗”专栏中向读者引介了12位诗人的12首诗,余光中的《当我死时》等被选的诗歌暗合了当时“思国怀乡”“积极明朗”的主流,但不能否认诗人被类型化、标签化和群体化引介的事实。这些评介促进了余光中及其作品在大陆的传播,同时对此后学术界和大众对余光中及其诗歌的解读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说台湾诗歌早期在大陆的推介与传播主要受制于三方面的约束:政治上,能积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文学上,要与当时居于大陆诗坛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原则相契合并能发挥巩固功用;艺术风格上,受当时正在开展的有关“朦胧诗”的讨论的影响,“明白易懂”成为占据强势地位的诗学主张。⑨1982年《台湾诗选(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艾青在序言中指出“乡愁”和“关心人民生活”可以作为这些所选诗歌的主题概括,余光中被收录的两首诗是《西螺大桥》和《车过枋寮》。1988年刘登翰、陈圣生主编的《余光中诗选》问世,这是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余光中诗歌选集。1980年代后大陆余光中诗歌的传播主要是以对各种选本包括鉴赏辞典的阅读来展开的,将余光中诗歌的文学价值、艺术生命及诗史地位凸显出来,赢得众多读者甚至知音,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余光中热”。
余光中诗歌的立体动态传播也呈现出持续高温状态。例如2003年9月10日到21日福建举行了“‘海峡诗会——余光中诗文系列活动”,2013年两岸诗歌桂冠诗人奖分别颁给了余光中、郑敏、姚风和阎安,余光中成为继罗门获此奖项的台湾诗人,其实在2012年的两岸音乐诗会上,童自荣就朗诵了余光中的《乡愁》和《民歌》,诗歌的独特魅力和朗诵的现场感染力,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这似乎為2013年余光中的获奖埋下了伏笔,2013年两岸诗会上还举办了“乡愁”交响音乐诗歌晚会,通过音乐人的谱曲及演唱,余光中的诗歌以一种通俗且前卫的方式传颂。另外,余光中还参加了许多电视节目,他谈诗歌、谈散文、谈翻译、谈中外文化,也谈儿女情长和高速飞车。他也有极其精彩的演讲,演讲如果以诗歌为发散点,则涉及散文、音乐、绘画等,揭示出它们的异同;如果以创作为发散点,则涉及翻译,传达出一位译者的思考;如果以今为发散点,则超越时空到古代,跨洋越海到欧美。台湾肯丁海洋生物博物馆这座以海洋生物为主题的大型博物馆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海生馆,余光中大概和海生馆颇有渊源,游人在参观的过程中会屡屡看到他关于海洋的诗作,这些旅游置景诗让游人在特定的情境中细细品读,满口“余”香。2011年4月《他们在岛屿写作》文艺电影纪录片在台湾上映,11月份登陆香港,2013年5月份在大陆首映,这部号称“影坛最深刻的文学电影”选取了6位台湾作家作为“在岛屿写作”的“他们”的代表,其中《逍遥游:余光中》里面嵌入《乡愁》的低吟浅唱,唤起大众美好而忧伤的记忆,余光中的幽默风趣也给这部文艺纪录片增加了娱乐色调,余光中在艺术与人生之间潇洒地穿越。由知识精英引发的余光中诗歌经典化运动,在新兴的网络群体即文化消费主体中也得到了相应的接受,从而使余光中诗歌的经典地位得到了双重肯定和巩固。
《乡愁》1991年入选教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认可余光中诗歌的有力佐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官方话语与余光中诗歌互利双赢。“经典依赖于不断流传、编纂、汇集、定型,以及批评家的甄定,读者的阅读,社会的流通,甚至异域文学的交流、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它更是某种意识形态权力运作的结果,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文学经典更容易获得某种权威性和神圣性。”⑩与知识精英话语不同,官方话语对余光中诗歌的接受进行了剪辑与润色,官方话语的认可在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架起了一道彩虹。“在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学校才是场地的中心,教育系统所把持的统治关系,即使对于那些处于文化场域边缘的人也是有效的。”{11}将余光中诗歌选入教材充分地发挥了学校作为场地中心的优势效用。赵毅衡认为:一直以来,筛选和重估经典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但近年来,一种全新的经典化开始出现,大众群选经典的方法进入了传统的文学领域。显然,在余光中诗歌的经典化过程中,普通受众占据了及其重要的位置。谢冕指出:“余光中的这些怀乡诗集中表达了那些在本世纪最大的民族离散中漂流的苦情。……但却升华为对于完整的文化中国的拥抱。……他把当日中国诗从倾注于意识形态转向了历史和文化,从而表现出历史的厚重感,特别是对那种显得漂浮的欢悦的补偿和校正。”{12}乡愁主题因满足现实需要而被选择并反复聚焦,又在学术界和学校教育中得以强化延续,逐渐内化成普遍的诗学话语,对其他作品的解读与作家的创作都产生了持续的导向作用。
余光中诗歌的“乡愁主题”被强化与窄化,普通读者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解读和使用诗歌,在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也传播着诗歌,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霍俊明曾声明:“诗歌不管是以传统的方式来传播,还是通过影视等更为社会化的公共空间,有一点是不变的,即优秀的甚至伟大的诗歌永远都不可能被改写和因为被大众接受而降低了品质”{13}就像余光中极为尊崇的伟大作家叶芝,他在诗歌、戏剧、散文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但在中国最负盛名的就是他早期的《当你老了》。余光中诗歌在大众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被固化和窄性理解,看似影响了普通读者在更广阔的视野以更灵活的方式去理解作家作品,但这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片面接受已具有可论证的正当性,这是余光中诗歌阅读效果考察的独立学术使命和意义。
三、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接受
余光中的诗歌经典究竟对大众的精神心理与文学创作产生什么具体影响,这更加接近文学接受的本质内涵。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接受指影响传承和效拟追摹,包括余光中对前人的接受及对他人的影响。一方面,是余光中对传统的吸收、整合与超越;另一方面,当余光中诗歌对其他作家产生了创作影响,作品被反复摹仿、借鉴、翻用。既要研究其接受影响,也要研究其发挥影响,当然,需以考察其发挥影响的强度、广度和方式为主。
在大陆,“余迷”不计其数,不少青年诗人均把余氏作品当作范本临摹与学习。在台湾,虽然没有出现自命“余派”的诗人,但也是“余风”劲吹。在香港,有“余群”“余派”乃至“沙田帮”“沙田作家群”,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沙田,在人杰地灵依山傍水的学院高墙内,那里曾经集聚着一群饱学之士,他们每日俯仰于山峦花木之间,畅游在吐露港的文学海洋之中,犹如群鲨,风平浪静之时相忘于江湖,当灾难来临之际却能相濡以沫,做到“文人相亲”、相互唱和。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的10年期间,在为学生授课之余仍然勤于笔耕,在沙田中开垦出一片文学的绿洲。在此曾以余光中为核心形成了“沙田诸友”,这些文友与余光中情怀相通、文字相惜,被传为文坛美谈。“但他们的聚合是一种以友谊为纽带的私人文字缘,而不是以艺术观念为旗帜和号召的流派组合,其来去聚散都带来有某种偶然性。”{14}
余光中广泛地参加了香港多样的文学活动,包括主持文学讲座、参与文学奖的评审、支持青年文学社团活动等等,对香港文学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扩大了自己在香港的文学影响。以致在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一些被称为“余派”的年轻诗人,这里说的“余派”诗人,并不是亦步亦趋余光中,而主要是指在某些修辞手段和用语、句法上师承余光中。“余派”也很难界定,那些曾专门临摹余氏笔风的文人自不在话下,有的作品在语法上的确带点余风,而主题、情绪和感触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这类作家也强然被归为“余派”。更为甚者,一些人因为曾对余氏的作品进行过批判,也硬被外人给戴了“余派”的帽子,在戴着这一帽子的作家群中有的是心甘情愿的如胡燕青{15},但也有否认的,认为乱扣帽子会有被“强奸”之嫌疑的郑镜明{16},更有极力批判余氏思想的“非余”派秀实{17},戴天承认余光中在港十年确然对香港诗歌创作的提倡和提高有影响,但对“香港主流”的指谓不以为然。{18}
余光中对马华作家的影响是一个不断改变与建构的开放过程,但余光中对马华文坛的影响表现为马华作家个体的主动建构,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或者吸收。在理论旅行中,扮演锻接叶芝、艾略特欧美现代主义诗学和马华现代主义的催化剂或白金丝的媒介正是余光中。马来西亚青年学者李树枝博士的《余光中对马华作家的影响研究》是第一本论析余光中对马华作家影响的专著,书中建构了余光中现代主义诗学的核心价值观,精细地描绘出众多马华作家接受余光中影响的轨迹,并赋予这种“拿来主义”与“借鉴意识”以积极意义,在诗歌方面,“探讨了刘贵德、何启良、天狼星诗社诗人群、温任平、骆耀庭对余光中的英诗中译文、余光中的莲、屈原、歌者、火焰、天鹅、凤凰、战争、性爱、船9个意象之‘吸收,勾勒了这些诗人化用了余光中的中文译文、诗歌意象以及诗句句法的影响轨迹,论述了余光中的现代诗创作思想,在文学思维和具体文字操作上给了这些马华诗人创作时一个丰富的凭依范式。”{19}
余光中与天狼星诗人群、神州诗人群承受同一文化渊源的华文诗歌书写空间,余光中影响马华诗坛的主要是其融汇古典与现代的诗歌创作理式,此借鉴形成了马华1960年代至1980年代独特的“中国性现代主义”的书写范式,借助中国性的文字符码以建构“政治抵抗诗学”。马华现代主义作家特别是天狼星诗社及神州诗社作家群,移植余光中的创作理论是有其政治性的考量。天狼星诗人群和神州诗人群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与余光中等海外移民的一代具有类同的历史位置,双方共有离散的身份,余光中的乡愁在台湾岛与大陆之间游荡,他们的乡愁则在南洋半岛与想象的神州中游移。温瑞安同样以“五陵少年”来铭刻自己的身份,其散文里的“五陵年少”“黄河”的中国性符号的表征似乎是来自余光中《五陵少年》和《白玉苦瓜》的诗歌理式,温瑞安作品中的“黄河”“长城”“龙”等中国性符号也转化自余光中的诗歌或散文。此外,视余光中为精神导师的温任平,同样以屈原来铭刻自己的身份,他跟余光中一样,以屈原为题材创作的诗歌数量众多,余光中和马华现代主义诗人群都将自身和屈原的流放互比,屈原成了余光中和马华现代主义诗人群安身立命的诗歌文化主题。{20}当然,在接受余光中诗歌带来的正面浸染的同时,创作者如何保持主体性或自觉性,是接受研究的延伸议题。
由上可见,一些优秀的诗句、意象或主题不断被沿袭之后,就被固定下来形成经典,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余诗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他文人的接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承認艺术创新的多样性和影响模仿的必然性,既是提出影响研究的理论前提,也是随着影响意识的确立,有待深化的诗学观念。
在经典作家接受研究中,在典型文学现象处理上,“读者文学史”的观念和接受意识提醒人们重视作为“普通读者”的大众,改变以往过于倚重“理想读者”即诗评家的观念。对于余光中的文学成就,他曾经的追随者,也是决裂者的《台湾新文学史》作者陈芳明曾这样评价: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斐然可观;那已不是属于一位作者的毕生成就,也应属于台湾文坛创造力的重要指标。{21}古继堂在《台湾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提倡我们用辩证的观点研究余光中,他一方面承认余光中在台湾诗坛乃至中国诗坛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指出,余光中涉及的领域很广且自成一片天地,纵横交错,使得给余光中的准确定位变得复杂而又不单纯,余光中诗风多变,造成其诗“庞沛多姿”“良莠兼具”。{22}未来的余光中诗歌接受研究需要在建立一种符合其接受实际的结构体制基础上,从中抽绎出一个个具体的学术话题,作更深入充分的辨析和阐释,提出具有新意的创见,努力超越一般的接受研究层面而达到接受史论的高度。
① 李少君:《余光中:民族美学的传承人》,载2017年12月15日《中国艺术报》。
② 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③ 汪剑钊:《诗意不够贯通的“乡愁”——余光中的〈乡愁〉指瑕》,《江南》2014年第2期。
④ 参见陈鼓应《这样的诗人余光中》,大汉出版社1977年版。
⑤ 古远清:《余光中向历史自首?——两岸三地对余光中“历史问题”的争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⑥ 林佑璋:《香港诗坛一瞥》,《花城·文艺丛刊》1980年第5期。
⑦ 李元洛:《海外游子的恋影——读余光中〈乡愁〉与〈乡愁四韵〉》,《名作欣赏》1982年第6期。
⑧ 聂华苓:《海外文学与台湾文学现状》,《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⑨ 参见何敏芳《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接受研究》,2015年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⑩ 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
{11} 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利(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
{12} 謝冕:《再现一个历史阶段的诗歌形态》,《小说界》1997年第6期。
{13} 霍俊明:《拟像的欢娱影视公共空间与诗歌的生态》,《山花》2013年第17期。
{14} 刘登翰:《余光中·香港·沙田文学》,选自黄曼君等主编《火浴的凤凰,恒在的缪斯》,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5} 胡燕青:《余派以外——一些回顾,一些感觉》,《香港文艺》总第5期,1985年7月。
{16} 郑镜明:《余派》,载1987年2月24日香港《星岛日报》。
{17} 秀实:《非余》,载1988年12月30日香港《快报》。
{18} 戴天:《流矣,派乎!》,载1986年11月3日香港《信报》。
{19} 张一文:《价值、创新与操演——评〈余光中对马华作家的影响研究〉》,《华文文学》2015年第4期。
{20} 李树枝:《现代主义的理论旅行:从叶芝、艾略特、余光中到马华天狼星及神州诗社》,《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
{21}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版。
{22} 古继堂:《台湾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n Analysis of Receptive Ecology of the Poetry by Yu Kwang-chung
Liang Xiaomei
Abstract: For Yu Kwang-chungs poetry to go further in depth, a study of its reception will be an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approach as there are generally three levels on which literary works are received as objects for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by commentators, for emotional and aesthetic enjoyment by ordinary readers and for absorption and imitation or borrowing by literary creators. In this regar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ceptive ecology of Yus poetry can be conducted in such areas as interpretative research, and research on its reading as well its impact. Even though Yu has very much liked to present a multifaceted image of himself to the world, not just as a poet or just as a‘nostalgic poet, reception in the social sense is bound to b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academic or literary sense as it only recognizes the most eye-catching side or point of the subject, and that is the ‘validity of one-sided receptionin the social-cultural sense.
Keywords: Poetry by Yu Kwang-chung, receptive ecology, validity of one-sided rece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