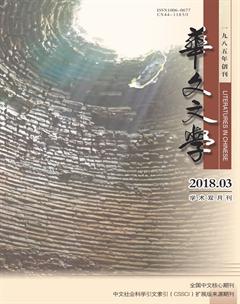“华文文学”与《华文文学》

摘要:这是本刊主编朱寿桐在2018年3月30日在汕头大学举行的“华文文学”论坛上的讲话,是对《华文文学》这个刊物以及“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华文文学这门学术,还有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关键词:华文文学;《华文文学》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3-0005-05
非常荣幸被汕头大学聘为《华文文学》主编,也很荣幸参加我们举办的“华文文学论坛”这样一个活动,感谢来自汕头市的作家、学者,还有来自潮州的学者朋友出席这一论坛。
我想对各位报告一下我对《华文文学》这个刊物以及“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华文文学这门学术,还有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华文文学》这个刊物历史虽然不算悠久,从1985年创刊到现在是33年,但它在众多学术刊物特别是文学学术刊物中创造了一个中国之最:这是与相关学科的建立、成长联系最为紧密的刊物,它应该是唯一一个与相应的学科一起产生、一起发展的学术期刊。应该说,华文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学术中的一门显学,连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都设立了阵容强大的华文文学研究团队,全国各地重要高校的中文学科都开设了这一课程或组建了这一学科,在各个重要学术机构,也都拥有一批杰出的学者专业从事这一学科和这门学术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令人刮目相看。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几乎每年都会发布与这一学科和学术相关的招标课题。总之,华文文学已经成为国家目录中重要的三级学科,已经成为国家学术研究指标中的重大课题,它在中国大学文学院和中文系学科体系中已经成为大气候的学科,在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建构中已拥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力。而所有这样的成就,都与我们面前的这个学术期刊,与这个期刊的倡导、鼓吹、探索、承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华文文学学科在今天已经成为中文学科中不可或缺的内涵,华文文学学术在目前已经成为中文学术中举足轻重的成分,则《华文文学》作为这一学科和学术的主要学术平台,便可谓功不可没,贡献卓著,可喜可贺!
华文文学是一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学科,也是一种得改革开放成就之利的学术。是改革开放让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有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看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并将它列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和学术范畴。从改革开放之初走过来的研究者都知道,文学研究拨乱反正之际,人们对来自台湾、香港的文学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期盼,充满着阅读与研究的热忱。但有条件去阅读和研究的人不多,信息沟通阻隔,资料来源不畅,只有处身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特别是汕头、广州、深圳等地的重要学者才能得地利、人和之便,较早、较多地接触到港台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被当之无愧地称为这一学科和这一学术的最初开拓者的陈贤茂先生,饶芃子先生,古继堂先生,正身处此域,此域之外的古远清先生、陆士清先生、陈辽先生、汤淑敏先生、赵遐秋先生、杨匡汉先生、曹明先生等也都“遥相呼应”,成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和学术的第一代奠基人。
华文文学作为新兴学科和新起学术,理所当然地与《华文文学》联系在一起。今天,无论身处何处,如论持怎样的学术立场,只要审视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和这门学术,就会非常自然地联想到《华文文学》这个期刊,这个平台,这个港口,这个焦点。不熟悉相关历史的研究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是汕头大学?历史与事实的回答是,因为陈贤茂先生,因为他当年非常有远见地在汕头大学迅速组建了海外华文文学学科,迅速主办了《华文文学》期刊。那时候,不满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们还只是翘首观望着台港文学(澳门文学则是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迟迟地挤进了人们的学术视野的);而陈贤茂领导的学术团队,就已经将眼光投向了更加遥远的海外华文文学。都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才是成事的根本,可天时——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是共同的,地利——汕头固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并不是最重要最醒目的阵地,与海外的联络也不是最便捷的地区,因此,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当文学研究的大部分学术人士还主要聚焦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候,陈贤茂等这一批敏感的学者已经将学术的聚焦点锁定了共时性的远方,在港台和海外的空域拓展中开扩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当台港文学以一种新异的姿态走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时候,陈贤茂等又能将眼光放远一点,看到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巨大场景和充沛活力,以发现的姿态引进了向来不被中国文学主流方面所关注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板块;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都还在纠结着如何接纳台港文学,如何面对那些不属于“中国”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时候,陈贤茂在汕头立起了“山头”,组成了他自己的研究团队,并且创办了《华文文学》,使之成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成为这一新兴学科一个海纳百川的港口与平台,成为这一新起学术的一个有力的支撑,也成为外界窥望这一新兴学科和学术的一个开放的窗口。陈贤茂先生等人的远见卓识成就了《华文文学》的历史,成就了这个期刊堪称辉煌的历史。当然,陈贤茂先生之后的历届主编和编辑班子的作用同样非常关键。大家多年的坚持和精心的努力,才使得这个平台焕发出学术的光彩,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作家、评论家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成为汕头大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学术亮点。
《华文文学》一路走来相当不容易,这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最初遭逢的尴尬连在一起。曾几何时,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对这个学科存有偏见。有一个流传了一阵的调侃语,说是做不了古代(文学)的做现代(文学),做不了现代的做当代(文学),做不了当代的做比较(文学),做不了比较的做港台(文学)。这一调侃语估计是十足外行的戏谑,因为它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不符合逻辑,我们都知道比较文学其实是很难做的,它所要求的外语背景和多元文化的学术训练可能比任何学科都高。但这一调侃语所以能流传一阵,说明读书界对华文文学一度存有的不公正评价。
是华文文学界以自己的积累与实力破解了这种不公正评价。经过了几乎是三辈学人3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经过一批又一批华文文学研究者队伍的化育与成熟,经过一批又一批富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的产出与推出,这一学科已经成为具有相当学术原创力和竞争力的学科,这门学术已经成为拥有自己稳定的学术力量,拥有相对健全的学术格局,擁有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的成熟而富有魅力的学术。这种学科与学术的成熟,每一步都有《华文文学》的参与,每一步都有《华文文学》的见证,每一阶段都有《华文文学》的心血,当然,每一点收获也都有《华文文学》的记录与承载。
华文文学这个学科和这门学术的形成,与整个海外华文文学压抑不住的发展势头大有关系。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世界格局更加趋于和谐、涵容和多元化,世界地球村的效应以及中国对世界、对海外世界包括学界的拥抱和接纳,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媒体时代交流平台的便捷化和集约化,都使得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越来越密集地、频繁地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和学术视野。如果说30多年前对于许多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华文文学在哪里都还是一个问题,那么,现今的情形是,我们可能会很轻易地发现我们已经被通常所说的华文文学包围了,华文文学已经与我们的文学生活,与我们的文学接受和文化氛围融成一体,作为华文文学作家的白先勇、卢新华、严歌苓、洛夫、张翎、虹影等等一度几乎构成了我们文学呼吸的空气,至少是空气中的一股难以离开的清流。其实,如果我们都将他们的文学理解为汉语文学,他们与莫言、王蒙、贾平凹、余光中等等处于同一的汉语文学的“等分线”,不必分出他们是属于“华人”还是“国人”,因而也不必分出他们的作品使用了“华文”还是“国文”,那样的文化对待将更加理想。但还必须尊重我们曾经开拓并且一直遵守的语言习惯,我们的“华文文学”常常非常遗憾地自处于“国文文学”之外,这是《华文文学》常设“汉语新文学”栏目的原因,我们在内心里想让“华文文学”与“国语文学”一体化,都是“汉语文学”。但是没关系,《华文文学》中的“华文文学”是特殊的研究领域,是特定的研究对象,也是特别的学术标识。
《华文文学》依靠了一批老一辈重要学者,聚集了一批实力派作者,培养了一批华文文学的学术生力军,而且也召唤了一批对华文文学越来越感兴趣的杰出的文学研究者,于是有资格成为华文文学学科的踊跃倡导者,热忱参与者和忠实推动者。历史地看,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每一个学术话题,都有《华文文学》参与甚至导引的痕迹。作為历史相对悠久的华文文学主打刊物,《华文文学》不仅倡导、参与、推动了华文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且名副其实地进入了学科设计和学术设计的角色,并以自己的坚守、推进、引领的形象为这个学科的诞生和强有力的发展站台。跳出华文文学学科、学术看待华文文学的整个学术格局,审视我们的《华文文学》杂志,同样能够发现这一刊物30多年坚持下来的不易。这30多年来,经过了各种荣耀和挫折,经历了各种兴奋与沮丧,经验了各种通畅与崎岖,在汕头大学领导始终如一的重视和支持下,经过各任主编的辛勤努力、编辑部同仁的勤奋工作,这个学术期刊奇迹般地坚持了下来,并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加辉煌。这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我们应当认真记取。
首先是,《华文文学》的办刊方针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当前世界文化的潮流主要是涵容、互渗、互含,然后趋于和谐。在汉语文学和文化世界,那种按照地域甚至政治板块划分的习惯越来越受到挑战与责难,我们的文学需要一种包容性的也许可以是统一性的认知。世界各个角落的华文文学都是中国经验的表达,中国人情感的抒写,中国文化的发酵的结果,我们都应该将其视为自己的东西,视为与自己的生命记忆和生活记忆相关的精神现象和产品,应该本着吸纳和包容的态度对待。有一种文化和学术的力量试图将边缘的汉语文学和文化分离出去,而我们的学术应该将它尽可能地内化为我们自己的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华文文学》正是以这样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视角取视这样的精神现象和产品的。相信通过《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和研究者也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几年,“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势头,一是名家叠出,名作迭出,精品不断,其势夺人,甚至在一定的题材开拓和影响力拓展方面压过了主流文坛的“风头”;二是“海外”纷纷变为“海归”,至少是“海流”或者“海留”,华文文学作家正在与当代文学作家形成水乳交融的局面,在发表平台、影响区域和接受途径上涵容一体,互不可分。在这样的情形下,《华文文学》和“华文文学”的文化地位会得到凸显,华文文学越来越会被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视为自己及自己周边的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华文文学》的影响力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其次是华文文学的研究者资源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充实。《华文文学》在历次的内部归属和编辑集体的变更中之所以未伤元气,甚至未减活力,是因为它所拥有的作者资源、研究资源都没有流失。这是一个在汕头大学创办的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但它的学术资源并不仅仅依赖于汕头大学,更多的学术资源来自于领域广大的华文文学学术界。固然,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力量相当集中,也有很厚重的传统,有相当重要的成果,但《华文文学》从来就没有定位为汕头大学相关研究机构的机关刊物,这是非常成功的一种学术定位。中国的学术杂志,特别是文学研究类的杂志,如果要办得相当出色,其主要学术资源就不能依靠本身隶属的学术单位。《文学评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刊物,但只要了解到这个刊物,就不会想到它是文学研究所的刊物,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学术刊物,是一个所有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从业者的发表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文文学》这个刊物的办刊思想和学术定位非常准确,也非常得当。打开这个杂志,你没有理由认为这是汕头大学文学院学者的园地,它是全国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共有平台,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通用平台,它在汕头大学,但从办刊之时开始就走出了汕头,走出了大学。随着华文文学学科地位的稳固,学术地位的提高,《华文文学》还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使得华文文学这个学术领域得到更多的学者资源。
这是我们建立刊物自身的学术自信的基础条件。目前,《华文文学》与其他所有的传统媒体杂志一样,面临着网络媒体等电子媒体的包围与严重挑衅,同时,我们这个刊物还面临着自身的尴尬,那就是华文文学刊物所处的纠结局面——学术文化上对中心的消解意识。不言而喻,《华文文学》杂志恰恰处在华文文学学术领域的中心位置,但这个学科和学术的发展将会导向对中心平台的消解。我们的文学研究首先就面临着重新消解的问题,现在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心到底在哪里?这很难说。不像20年前30年前那么明确,那时候一个主要的学术平台,几个重要的发声学者,就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造成某种中心效应。但现在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平台的中心力量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消解与挑战,发声学者的声音也很容易被淹没在嘈杂的众声喧哗之中。当代传播的多向性早已经取代了传统传播的单向性,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也早已经冲溃了传统传播的一元化,我们的学术交流,学术信息的获取,学术资源的发散,都已经到了消解中心的杂合时代。当然这是从纯粹的学术传播和学术交流的角度而言的,学术正在走向多元,走向多平台的立体交汇,很难再形成中心,原有的学术交流中心也会处在消解之中。信息方面的网络文化、多媒体文化、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以及现当代文化立体化的推进,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几乎是无缝对接,传统媒介和平台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其结果是作为学术资讯和学术文化交流中心的刊物,《华文文学》的平台效力就会降低,文化影响力就会降低。事实也正是如此,华文文学的网络平台现在已经隐约有形成一种新的刊物矩阵的势头,而传统学术媒介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也在发展之中。
《华文文学》在今天的这种影响力来之不易,守之更难。以一个好的平台可以形成一个学术交流中心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我们并不是无所事事。事实上这样的平台仍然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一优势的存在以及持续性影响会比别人做得更有效力。《华文文学》应该珍视在世界华文文学学界的地位与威望,珍视这一平台的影响力,珍视这一平台发声的文化麦克风效应,清晰地认知这个刊物在华文文学界定于一尊的地位,强化它作为核心刊物、中心刊物、重心刊物的意识。
《华文文学》伴随着华文文学这一新兴学科,华文文学这一新起学术的发展而壮大,其核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容否定;当然也是现实成就的,是它的编者、作者、读者共同营构共同努力的结果。它拥有各个时期最强大的华文文学研究作者群,这是这一刊物始终处于这一学科核心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在众声喧哗的当代学术环境中,《华文文学》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团结各年龄层次的实力派学者,培养不同研究方向的年轻学者,同时召唤关注华文文学但又有所疏离的文学研究者,组成最强势的学者和作者阵容,使得刊物的核心地位更加稳固。《华文文学》同时也拥有各个时期最理想的读者群,关注和閱读它的读者都是华文文学学科和学术的有心人,这是这个学术期刊成为影响这一学科与学术的重要核心期刊的关键性因素。
随着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学术地位的提高,陆陆续续绘会有一些其他的刊物加入,包括网络刊物,他们的学术技能、资源和影响力还没有办法和我们比较。但这些纸质刊物和电子刊物的出现,对我们来说一方面增加了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是凸显了我们刊物的中心位置。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对我们的刊物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它已经成为海外与大陆、港澳台地区交流的平台。同类刊物出现越多,我们的中心刊物的位置就更加突出。
从文学研究的刊物构成来说,《华文文学》的重心刊物地位也应该得到强化。当代的文学研究重心明显发生了几方面转移,一个是向网络文学方面转移,主流文学研究者从不承认、不屑到开始关注、接受,使得这一文化事实得到普遍承认,网络成了当代文学学术的一个重心。第二个重心是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也是从不怎么重视到慢慢地重视起来。第三个毫无疑问,就是华文文学,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都开始密切关注华文文学,现在我们有条件、有理由将这一学科和这一学术领域开拓为学术的重心。
总之,处在华文文学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关键时刻,主办《华文文学》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尽管我们会面临许多挑战,尽管我们的努力比起前人要艰难一些。《华文文学》同华文文学一样,面临着挑战,但同时也面临着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进一步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意识到局限于一国一地的文化思维会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在这样的情形下,华文文学和世界范围内统一的汉语文学远比一国一地的文学关注更有意义。由于地球村的效应,也由于社会格局的变化,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由于迁移、交流的便利,更由于中国的崛起,“海外”与“海内”的疏隔情状会越来越被忽略,文学表现和文学认定的那种画地为牢的局面将会被逐渐打破。只要我们想一想白先勇、严歌苓、卢新华、张翎、洛夫等卓越文学家的生存状态和文学活动半径,我们就会发现华文文学的空域圈正处在不断内化的状态,他们的文学创作,文学活动、文学影响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华文文学空间范围和文化范围,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当然内容,成为汉语文学文化的当然内容。
华文文学以及包括华文文学在内的汉语文学,将在歌德式的世界文学框架下,在时代性更鲜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思维中,更容易占据当代国人和学人的中心与重心。《华文文学》应该勇敢地面对这样的新机遇,将华文文学在汉语文学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进行系统的学理的和文化的理析。这是刊物的生存之道,也是刊物的发展之本。
当移民不再是人们的生存选择,而仅仅是生活选择甚至是审美选择的时候,“海外华文文学”的“海外”二字就显得越来越含义模糊,于是,“华文文学”越来越名副其实,《华文文学》的存在感也就越来越明显。华文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它已成为当代文学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参与者,甚至是某种潮流的引领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重视华文文学。这使得《华文文学》杂志,绝无仅有地成为海外华文作家及不同行业的文学研究者关注的交汇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优势很明显,我们这个刊物的机遇总是会大于挑战的。这就是我对于《华文文学》杂志以及这个学科、学术的一些理解,以就教于各位专家、教授,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