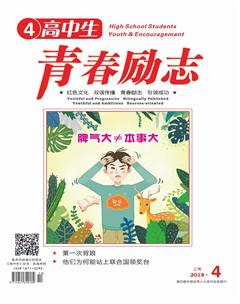第一次背娘
刘俊奇
我第一次背娘,是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初秋。那一年,我53岁,娘72岁。
每到秋冬季节,娘的膝关节病便会复发。于是,我给娘打去电话。
电话那头,娘全无往日的欢欣,声音沉闷而又有些迟疑。娘说:“你要是不忙,就回来带我去医院看看也好……”我心里一阵恐慌。
娘一个人在老家住的时候,因为担心儿女的惦念,总是报喜不报忧。像这次这样,她主动提出让我回去,还是第一次。
我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驱车三百多千米,从济南赶到沂蒙山老家。
一路上,我忧心如焚,娘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父亲去世时,娘才33岁,我最小的妹妹刚刚三个月。为了把我们兄妹五个拉扯大,尽早还清为父亲治病欠下的债,娘就像一台机器,不分昼夜地运转。
那时候,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咱不能让人家看不起,不能让人家笑话你们……”
为了这个承诺,娘吃的苦、流的汗,娘经受的委屈和磨难,难以用文字描述出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的农活有许多靠肩挑人抬,不少人被压弯了腰。那时候,农村驼背的人比比皆是。
身高不到16米,体重不到40千克,看似柔弱的娘,却有着一副似乎压不垮的腰板。
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娘不知道用坏了多少钩担、扁担、筐与水桶,而娘的腰板一直挺着。娘知道,自己一旦倒下,会是怎样的后果。娘说,不能让没有爹的孩子再没有娘,没有娘的孩子才叫可怜……娘咬紧牙关撑起这个家。
在我的记忆中,特别令人恐惧的农活之一,是从村西的渠道里挑水抗旱。
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娘就挽起裤子、赤着脚,一次次走进冰凉的渠水。在陡峭、湿滑的坡道上,娘弓着腰,挑着两个与自己的体重差不多的水桶,一趟又一趟,在水渠和坑坑洼洼的庄稼地里来回奔波。
后来,渐渐长大的我加入到挑水抗旱的行列中来后,才体会到那是怎样的一种苦不堪言:一根钩担挂着两个装满水的桶,沿着约45度、近20米高的一条又湿又滑的陡坡上上下下,步步惊心。上坡时,必须保持身体与陡坡的平衡,脚要稳,脚趾必须像钉子一样抓在湿滑的坡道上,稍微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桶滚进水渠……
娘说,那时候,有时她一天挑过70多担水,膝关节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我曾经到多家医院为娘看病,医生说是长期劳累引起的病变。
汽车驶过一条小河,我远远地就看见了熟悉的村庄,还有那条令人生畏的渠道。一群鸭子在水里悠闲地游动觅食。渠水依然在流淌,乡亲们却再也不需要挑水种地,大大小小的电灌站分布在渠道的两岸。
因为连续下雨,路面到处泥泞。我让司机把车停在村头,心急火燎地向家里走去。
娘见到我,艰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的手抚在肿得像大馒头的膝盖上,脸上呈现出痛苦而又有些歉意的表情。
我在娘的跟前蹲了下来,想背着她上车。娘犹豫了片刻,说:“你背不动吧?”看着院子里的泥和水,娘还是顺从地趴在了我的背上。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背娘。娘看我有些摇摇晃晃,几次想下来,我阻止了。
街上,一位婶子正在大门口做针线活儿。看见娘趴在我的背上,那位婶子便哈哈地笑了起来:“哎呦,年幼时背着儿子,如今老了,得让儿子背着喽……”娘嘿嘿地笑着,笑声中,有羞涩,又有些幸福的味道。婶子的话,让我心头一热,眼泪差一点流出来。
瘦小的娘,有一个宽阔而又温暖的背。儿时,娘的背是我們兄妹最温暖的家。多少次,生活压弯了娘的腰,娘却舍不得把背上的儿女放在劳作的地头上,娘担心虫子会爬上孩子的脸……多少个雨雪天,我们爬下娘的背、钻进娘的怀。娘用单薄的身体为我们遮风避雨……
我是娘的第一个孩子,娘对我的疼爱和付出,可想而知。
记得我15岁那年,一次,我突然肚子剧烈疼痛。娘被吓得不知所措,慌忙背起比她还高的我,撒腿便往村卫生室跑……
这次,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我背着娘楼上、楼下做各种检查,到处是温馨的目光和礼让的举动。医生说娘的腿并无大碍,开了一些消炎和外敷的药,提醒她要注意保暖等。
中午,我背着娘走进一家比较气派的饭店。正在饭店用餐的人们向我们行注目礼,一些人还站起来鼓掌。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老人来到我的身边,竖起拇指,说着地道的家乡话:“背着的是老娘吧?俺很长时间没看到背着老娘来吃饭的了,一看就是孝子啊!”
吃过饭,我劝娘随我一起回省城住。娘说家里还有喂的鸡,离不开,还是像往年一样,天气冷了再去吧。我拗不过娘,只好把娘送回家。
晚上七点多钟回到省城,我立即给娘打电话报平安,电话里却传来娘的哽咽声。我大惊失色,慌忙说:“娘,你不要紧吧?腿是不是还是疼得厉害?”娘没有回答,抽泣了许久才问我:“你的腿、腰没事吧?你也是50多岁的人了,背了我一天,心疼死我了……”
那一刻,我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