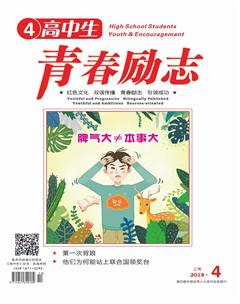生活的底气
雪小婵
八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
那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而是母亲替我选择的。生下我一年后,母亲再度怀孕,不得已,她将我送到乡下外婆家。外婆那年还不到50岁。
我从有记忆开始,便觉得乡下是广阔天地。
北方的农村都辽阔,河北尤其是这样。华北平原一望无际的田地里,有玉米、谷子、棉花、黄豆、芝麻,还有茄子、西红柿、黄瓜、豆角、南瓜、马铃薯……北方所有的农作物,我都如数家珍。
外婆那时去地里干活,总要带上我。
玉米地里有清香。外婆剥了新鲜玉米给我吃,玉米有米白色鲜嫩的汁液。玉米秆是清甜的,我一个人坐在地里吃呀吃……
我的这段乡村记忆,是这样敦厚、诚恳,甚至那些脏乱差,都成了日后回忆里的丰沛与温度,格局与气象。
一个酷暑的下午,我翻看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几度心酸。苏北少年与华北少年同样孤独,盼望过年穿新衣、吃肉,盼望周末,盼望母亲带来奶粉和红糖……物质的匮乏总是刻骨铭心。
麦收过后,村子外面出现无数花秸垛。在更远的北方,就叫麦秸垛。铁凝小说里便有一篇《麦秸垛》。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是幸福的,在漫长的人生中,那段经历和回忆是丰沛、厚实的滋养。
我每天去地里看鹅,運气好时能捡个鹅蛋。有时和邻居的铁蛋、二丫玩,玩一会儿便打了起来,互不相让。
我盼着说书人来。
秋收过后,村里会有说书人来,他说《三侠五义》《西厢记》……我坐在板凳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月亮爬上来,露水湿了衣裳,外婆抱我回家。醒来后,发现说书人不见了,我便怅然若失。忆起他穿的长衫和他的声调,觉得怪迷人的。所以,那时我盼着长大后与说书人游走江湖。
工作之后,有几年我甚是洋气,喝咖啡,吃西餐。我在西湖边、上海外滩,喝着上百元一杯的咖啡,穿着几千元一件的衣服,身上每件东西都来自或大或小的品牌。那几年,我虚荣极了,并且摆出姿态,无论是文字,还是人。
自八岁之后,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多数时候,我穿行于国内的一线城市,那些洋气无师自通。没有人看出我在乡下住过七年。我也试图表明,我是地道的城里人。
但不是。我与别的女子去西藏旅行,她们对酥油茶大呼小叫,对一年不洗澡的藏民不理解,对住的旅馆没有24小时热水供应抱怨。我倒头便睡,并在旅途中渴了就喝山涧的水。
中年以后,我选择棉、麻材质做的,不过百十元钱的衣裳。我记得小时候躺过的棉花垛,记得棉花的温暖。我自己腌咸菜,像外婆那样卷起袖子干活,蒸一锅纯碱的馒头,炖一锅红烧肉,定期去乡下走走。这么多年,我依然喜欢乡下的味道。尽管失掉了从前的朴素、淡然,但仍旧比城市好很多。
那些村里的老人还认识我。他们叫着我的乳名,说庄稼越来越少了,这里成了开发区,很多年轻人去住楼房…
铁凝、乔叶、毕飞宇……我忽然想起他们,他们拥有农村生活经验,对农村生活的细节记忆深刻。我在乡下度过了童年,这是老天爷的恩赐。这样的生活经验,可以成为一辈子的生活底气——那么苦的生活我都经历过了,还怕什么?
有了这样的底气,多么的自足——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有这样的底气,可以丰满地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