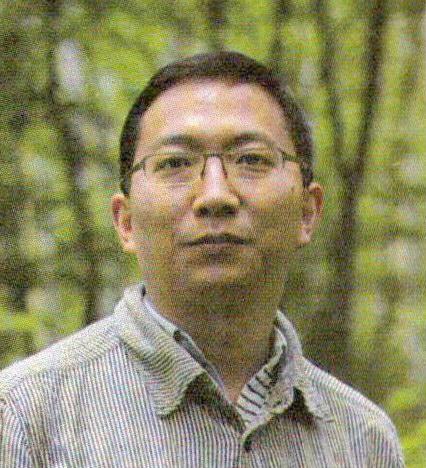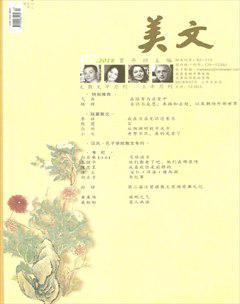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
王国华
一
《傻子》开篇,汪曾祺写道:“这一带有好几个傻子。”
文末说:“北京从前好像没有那么多傻子,现在为什么这么多?”我在北京住处的附近也有好几个。
一个是卖气球的。小伙子,大高个,立正姿势,站在路边,目光漂浮无着。脚边放着一个包,手举一个气球,男的路过,他说:先生,买个气球吧!女的路过,他说:太太,买个气球吧!人都绕着走,边走边回看,表情复杂。
冬季有一回见他时,裤裆已经湿了一片,瑟瑟发抖,依然在喊:先生,买个气球吧!
一个走路不顺当,口齿也不清。经常坐在公交车站旁的椅子上,大声嚷嚷,自己跟自己说话,一浪高过一浪,越说越生气,抡起拐杖砸得广告灯箱“咣咣”响。
车站旁有个修自行车的摊点,这时修车师傅都要吼一声:嘿,别砸了,嘿!他就停手了,乖乖地低头,轻声嘀咕,酝酿声浪,渐次加码,“咕噜咕噜”往上涌,眼瞅着到了爆发点,又动手了,“咣咣,咣咣咣,咣——”
修车师傅正跟豁嘴老头下棋,“车”快保不住了,心急,大喝一声“嘿!”嘎嘣脆。又静了下来。
一个是在小区里住着的。总是穿着一肥大的白背心,胡子拉碴,脖子上挂一牌子,上面写有家人的手机号码。牵一条小狗,在院子里四处巡查,见谁有空就聊几句。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边说事儿,脏话顺口滑溜而出,说上一通,末了不忘缀上一句,“你知道吧?”
小区业主停车不顺畅,他顺畅地介入,很热心,“左……往左……X,使劲呀!……多了!……再来!……X,行不行,您哪!……停!X,真‘面!”
谁非过客,他是主人。
还记得老家有一个。小时,在乡村引发孩子集体兴趣的,除了追赶路过的汽车,还有就是他的出现。
孩子们喜欢围观,他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当然会保持适当距离。他烦躁了,就掉头来追赶,孩子们“呼啦”四散,慢慢又聚拢在一起,像是在玩一个游戏。
课间他冲到教室,在黑板上端正地写下三个字。再把黑板擦往桌上严肃一拍,凶巴巴的样子,开始上课:
“跟——我——读——周——慧——敏——”
他说周慧敏是他的“浑家”。
后来再也没见着他,也没有他的消息。当时不知道还有“一期一会”的说法。
美国摄影家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喜欢拍摄“怪人”,她为这些人身上的某种特质着迷:
就像一个神话故事里的人物,拦在你面前,让你回答一个谜语……大多数人都在“恐惧未来会有什么创伤”的担忧中生活,而怪人天生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所以他们是贵族。
1808年1月22日,当拿破仑践踏欧洲版图,正在穿越葡萄牙边境线时,葡萄牙王室仓皇出逃,整个场景犹如疯人院。率先迁移的玛丽王后脑子不太好。她反而劝告大家:“别跑得太快,好像我们是逃跑似的。”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评点道,这是“那个疯人院里唯一的一句清醒话”。
所谓的贵族,还不如有创伤的“贵族”。
这些人,有时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
可惜,他们的命运和生活时有令人唏嘘之处。
老家还有一个,轻微的病,后来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了。但是方圆都知道有这么回事,討不到媳妇。他有个妹妹,很好的一个姑娘,放出话来,“哥不娶,妹不嫁”。如果哪一家也是兄未婚妹未嫁,那就互换好了,她对男方不设防。
上次回家,听说没有后续。
现在九月中旬了,老家的天还热着,三十度以上。
二
《冬天的树·公共汽车》,汪曾祺写了北京公交车上“精力旺盛的、机敏灵活的、不知疲倦的售票员”,他们其中的一位有着“一副配在最大的演出会上报幕的真正漂亮的嗓子”,另一个小伙子则总是“高高兴兴而又精细认真”。
读毕这篇小文。我用铅笔在天头写下两行字:“感到深深的悲哀,好东西都让人给写完了。2016年9月18日上午8时39分。”再从书房移入卧室,将自己往床上一扔,把头埋在枕头里。
脑海闪过一名售票员的影子。
北京52路公交车上的。
顶部微秃,头发干枯、稀疏,无精打采,软绵绵地趴着。0600XXX,是工号,立在工服的胸部位置。工服是浓郁的深蓝色,颗粒松散地连缀着,敷衍,拖沓。淡红色领带,白色条纹等比例倾斜。右手戴粗布白色手套,左手裸露,待遇有别。
就像汪曾祺说的,北京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上下班高峰时一般都得扯着嗓子喊:
“挤挤。挤挤,多上一个好一个!”
“上不来了!后边车就来啦!我不愿意多上几个呀!我愿意都上来才好哩,也得挤得下呀!”
这个更普遍了:
“往中间走!往前后门走!动一动!把门口让出来!”
有点声嘶力竭,尖锐。急促。
坐车的,人挨人、脚抵脚。而且由于拥堵,车辆给钉住了,一动不动,内心的烦躁逼近临界点,再来这么一下子催促甚至是号令,凝重窒闷的气氛加码升级。
52路上的这位,有自己的路子:
“老师傅,少师傅,小师傅,走一走,移一移,挪一挪哩!”
腔调脆响,近乎唱。
无望之际,听了这么一嗓子,焦虑感被冲淡稀释了。
他叮嘱要下车的:
“下车记得刷卡!不刷卡浪费你的钱不带商量的!”
报站,一般来说,要么是“下一站,西单路口东”,要么是“西单路口东站到了”。规范,标准。他不走寻常路:
“门开开,西单路口东。”
或者是:
“坐着的,站着的,眯着的,注意啦!到站了!看景的,看手机的,听着点,东单路口西到啦!”
而且老是有新花样:
“往里走走啊,把东西往里边挪。劳驾,那个男同志,看手机的师傅,对,说的就是你,等会儿给朋友点赞也不迟,先动一动,啊!”
有时还来这么一出:
“门口要下车的几位,来!听我口令,齐步走!”
这就顽皮了。
沉闷清冷的车厢,他以一己之力,点燃了。
汪曾祺发现,公共汽车上张贴的《公约》,第一条是“热爱乘客”。他遇见的一位司机冷静、坚定,225号售票员小伙子有着“开朗的笑容”,都是因为热爱。这位0600XXX,变着法子给乘客带来欢乐和新奇,也是因为热爱吧。
三
《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汪曾祺说詹大胖子工作的校园没有多大点,有两棵桃树,两棵李树,一棵柳树。一笔带过,“今日无事”。于我却勾起一段回忆。
早年,家乡有为官的,传言贪腐几乎是“明码标价、公开透明”的。亲属提醒官太太,还是小心为好。官太太不屑,先是谩骂这是没影的事,乱讲的,心术不正,不干好事,看不得人家过好日子,造谣之人,生孩子没屁眼,洗头都要给淹死,走路跌到坑里。有本事来查呀!
中气十足。
再退一步说,家里有大树罩着,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一棵“柳树”,怕什么,没事,该吃的吃,该喝的喝!
她的意思是,她家官人的上游,有姓陶的、姓李的、姓柳的帮忙撑腰,总之是“上头有人”。
这是公开警告:少给我捣乱,没用的。
也是自我减压:树下好乘凉,没事的。
坊间女人智慧,地气盛,又直冲云天。
不知道现在这些人都是怎么过日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