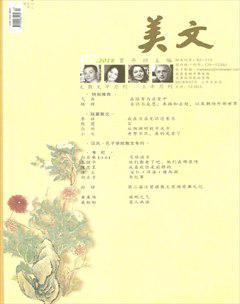自识与反思,来路和去处,以及朝向外部世界
杨辉
以《在恒常与流变中》为总题的这一组文章,差不多都有着一种潜在的论辩性质。论辩的对象,也未必总是他者,它还可以指向并最终指向自身,也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指向你我共处的世界。这便是何以作者从同为“70后”作家,却早以评论文章知名的梁鸿对一代人的精神境况的描述中意会到一种总体性的自我突破的可能的原因。也在同样的意义上,他开始反省“现代性”以及我们对它的看法,反思“恒常”与“流变”的辩证的真实意谓,并最终反省作为写作者既有的“来路”和可能的“去处”。但最终的问题仍如田耳所论,“遍察全地之后,何以反观自身”,经由“不断加深思维的自律和理性”以“通达小说的浑沌之境”何以可能?又或者,在“恒常”与“流变”,“理性”与“浑沌”之间,是否可能存着某种尚未被意识到的重要的问题?这种问题,形成了有待突破的对于写作的限制。
稍稍放开视域,从《随园》说起。黄德海发现,相较于此前作品的“细致周密”,这一部作品的“内在空间”已被打开,且长出了一些新鲜的血肉,尤为重要的是,“对世界的容含度也高了”。那些出现在作品中的意味深长的意象,已经不再被牢固地镶嵌于整体性的“整饬”之中,而是有着俗世烟火和普通人生的况味。譬如“白骨穿出褲脚”,“缆车轻慢了雪峰”,意象虽然奇崛、鲜烈,却仍在世界之中,呈现的是世界的模样,而不是将世界的棱角磨平,将一切毛茸茸的细节整一化,并最终组织到作品整体性的单纯氛围之中。一如刘晓东,他所秉有的“先天的孤独因为脱离了与时代的关系,上升到了纯粹的高度,仿佛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人类心理状况,似乎与世界有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对照关系”。这几乎是一代写作者普遍性的精神诉求,我们希望经由对一个人的命运的书写,让更多人的命运涌现在自己的笔下。但这样的写作仍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这样的问题:“这个纯粹化的孤独,却也会因此脱离了与时代和生活的深层关系,把内心生活与外部世界完全对立起来,显得失掉了生活的根基。”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如是“企图把日常生活上升到所谓哲理或先天高度的努力,说不定恰是一种时代病,会把人困在孤独的概念里不能自拔”。困于某种概念以及由此概念所开启之思想视域,偏于一隅而不遑他顾,甚至由之生出排他的心态,已经接近于佛家所说的“理障”。唯有破我执,去无明,方能得大自在。这差不多又接近于于连从中国古典思想中读解出的“无意”的智慧。“无意”的意思是,不偏于一隅,不故步自封,而是平等地接纳不同的阐释并表达世界的可能,因为,“任何一个观念都没有特权”。所谓的特权,均不过是逻辑的幻象。差不多因着同样的原因,田耳喜欢弋舟文学言论的灵动飘逸,却觉得其小说并不曾放开,“过多的控制,缺少失控,过多的诚意,有时又难掩说教”。即便一些小画,一些似乎出自“小憩”时的创作,仍然有着“致命的郑重”。即便这种“‘郑重已经构成了某种压迫”,且已部分地损害着作为小说家的弋舟的写作,即便有黄德海对他的作品细部与总体以及和现实的关系的洞见,弋舟似乎仍无意于摆脱“郑重”。他将“郑重”等同于“专注”,而处于其对立面的,则是“松弛”与“草率”,前者乃为“恒常”,后者则属“流变”。在“恒常”与“流变”中,弋舟自然而然地选择前者,宁多“匠气”,也不愿“松弛”。对一位严肃的写作者而言,这样的选择并无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汪曾祺所谓的“苦心经营的随便”?写作中过多的“才子气”,就一定会导致“松弛”与“草率”吗?在这之间,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或许,弋舟并不赞同这样的文章传统。一切文章乃性灵自出,不假强求,无意于佳乃佳。一如刘勰所论,“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小说家力图摆脱做小说的痕迹,恰恰又证明还是在做小说。反之亦然。其间微妙的差别,寸心自知。
也因此,作为一部“放开了”的作品,《随园》并不“整饬”,它的细部不乏貌似旁枝斜出的闲笔,文笔也多摇曳,一些意象和偶然一现的情感也并不总能融汇到整体的氛围之中。但这种种意象种种貌似杂乱的情感最终汇聚成《随园》极具纵深感的精神世界。不单是袁枚的随园与薛子仪的随园相隔百年分处两地巨大的时空差异,还有杨洁个人的生活,在并不长的篇幅里仿佛已然有了几生几世。而一种巨大的虚无和人世的苍凉感也就在结尾处悄然发生。或许,在另外的意义上,并不具有较大篇幅的《随园》比《蝌蚪》和《刘晓东》包含着更多的“现实”。因为,在这部作品中,弋舟努力去接近“那些相对陌生的事物”。他的笔下出现了雪山、戈壁和白骨,而这些意象使他“部分地躲开了习焉不察的那些‘圆熟”。它们或许比较“拗”,“但恰恰是它们亘古地存在着,世界才得以平衡与整全,我们的历史与我们的现实,风中的诗歌与风中的沙砾,都因此得以可靠地安放”。或许可以这样说,《随园》有着如是现实本身的粗粝的风格。它并非是全然裁剪得当的现实,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接近日常的现实本身。但日常的现实,也未必就没有超越自身的东西,也未必不能表现作家对于总体性的人类生存的洞见。黄永玉对沈从文《长河》的评说或可为参照。黄永玉发现,《长河》是一部依赖“永不枯竭的故乡思维”写就的作品,沈从文“排除了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正因此,沈从文获得了写作的超越定规的自由。再如刘熙载所言,“《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彼固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蹈大方处求之?”“蹈乎大方”乃为从心所欲率性而行却合乎大道,非肆意妄为无端挥洒。在郑重之外,为文之妙,或许也在此处。
对此,弋舟也并非没有意识。他并不赞同目下关于“现代性”的种种“定见”,以为此间尚有诸多可以商榷之处。如果其仅仅被用来指称“早期实验性质的有缺陷并且在文体上都模棱两可的东西”,那它就不是文学的“恒常”,而是无可置疑地具有某种暂时的过渡的性质。因为,无论就何种意义而言。单纯的“方法”的标新立异并非文学的根本目的。它的目的仍在对外部世界的深刻洞见,对存在的勘探,从而表达那些唯有小说能够表达的东西。也因此,“现代性”的反叛姿态或许最终偏离了他自身。如同对写作过程的兴趣无法取代对作品完成性的追求。卡夫卡笔下具有丰富寓意的世界自然包含着对人之境遇的洞见,当然首先必然指向其所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从与父亲的关系中卡夫卡足以体会到柔弱的个体面对外部世界时巨大的无力。那个被父亲判决投河的年轻商人格奥尔格,也何尝不是如此。他小心翼翼地面对着父亲所主宰的强大的世界,并在其中体会到个人的虚弱和无力。他仅有的狭窄的个人世界被父亲一再强行介入,他一度“喜不自胜地玩味着这一共同物(那个在又不在的远在彼得堡的朋友),以为已经赢得了父亲,一切在他眼前都显得那么安宁,包括一闪即逝的伤感”。但这种安宁不过是格奥尔格一厢情愿地营构的精神的幻象。父亲最终以其强大的力量再度粉碎了格奥尔格最后一点“自主的力量”。而“正因为他除了看着父亲以外,别的一无所能,所以父亲对他的最后判决才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或许,换句话说,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和这个世界之间的“欲望介体”,唯有通过这一介体,他才能恰如其分地切近外部世界。而最终,这个介体抛弃了他,也切断了他和这个世界之间最为稳固的联系。在这里,卡夫卡表达了他对柔弱的个体被迫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荒诞的洞见。由此,我们可能还会想起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开篇所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但,如弋舟所言,卡夫卡写下了“忧伤”,却并不想叫我们“绝望”。他希望经由写作的方式。来创造出某种堪称“希望”的事物。正因为如此,他只能朝向“内在”,从而必须面对持久的“内心的激辩”:在希望与绝望,存在与虚无之间,似乎包含着难以跨越的巨大的鸿沟。而写作,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构成了精神的泅渡的方式。或者,所谓的希望不过是一种话语的制造物,我们需要着力而为的,也不过是将其“现实化”,至少,在最低限度上,将其“精神化”。缘此,“绝望与信心的交织”,“构成了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认识到世界根本性的虚无和绝望的无可避免并非最终的目的。写作者最终的目的始终在于,在绝望中创造希望,以永恒的信心抵御虚无……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但,哪怕最终只有抗拒的姿态,也是好的。
由对“现代性”的诸种可能性的反思,以及通过对卡夫卡《判决》的个人化读解,弋舟最终抵达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学的现实。他表达了对目下小说写作的不满。在他看来,“小说过度做回了故事和趣味的囚徒,不再逼视存在的真实境遇,进而远离了那个内在的人(他从卡夫卡作品中体会到的那个转向“内在”的人)”是为当下小说弊端之一。而在另一方面,当下的小说还陈陈相因,它们“片面地放大了虚无与绝望”。这里的陈陈相因,应该别有所指。它所指向的,可能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迄今中国无远弗届的影响。几乎可以这样说,新时期以降之中国文学,根本上奠基于由此形塑之文学观念及批评语法。现代主义在80年代的解放意义无需多言,但这个曾经给予作家极大的启示的传统,是否存在着话语的霸权和对他种可能的遮蔽?对此,艾伟有过较为详尽的论述,他将“情感信服力的不足”,“社会反思能力的欠缺”等等视为“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而这种疑难,在很大程度上,或许与现代主义及其所持存开显之世界观念不无关系。在多重意义上,艾伟的判断可以视为是对弋舟的反思的先在的呼应。“一个内在的人,一个有存在感的人,一个勇于与世界和内心激辩的人,他的书写,代表的是对存在的不懈追索,而‘不懈追索这一积极的态度,这一命定了的‘徒劳的姿态,这种‘与世界和内心激辩的热情,在我看来,却构成了現代小说的精神基石。”为了抵抗现代的遗忘,我们必须直面存在的真实。这也是昆德拉抵御“存在的遗忘”的共通的方式。但我们还应思考的是。如此切近存在和现实的写作理路,也并不仅存于现代小说的路径之中。无需上溯太久,便不难察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80年代现实的整体性的关系,以及柳青《创业史》与50年代时代精神之间的根本性关联,是否也意味着另一种切近阔大的现实,从而深度抵达存在的有力的方式?如悬置既定的文学成见。这种方式,与现代主义的存在的勘探,究竟构成了何样一种关系?
从总体性的生命历程看,张新颖先生以为,沈从文在刚过三十岁时写作《从文自传》,有着别样的用心。他写湘西的“日子”“人物”和“声音”,以便反思自身从中所受的教育;他还写杀人,写于此种可谓残酷的环境中个人无量数的快乐等等等等,最终的目的,却在对人类的智慧的光辉的领会,并在最为深入的意义上“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这个“自”是自身的精神的来路,而反思来路的目的,却是面向未来。面向诸多的可能性并在其中做出个人的选择。沈从文后来写作的《论西南漆器及其他》,在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时段,也起过差不多相同的意义。经由与梁鸿对“70后”整体性的精神处境之反思的对话,弋舟以为梁鸿所开出的方案,于己意义重大。“它不仅仅是方法论,还是重塑世界观的契机。”世界观的重塑,当然有着巨大的革故鼎新的意义。但这种革新,仍然要以对自身来路的自识与反省为基础。在为《丁酉故事集》所做的序言中,弋舟谈到了个人最初的记忆,并渴望从“那些‘蛰伏在意识深处的映象开始”,“努力去回溯自己的‘文学的起点”。当然,那些最初的记忆所存留的映象,几乎也形成了一位写作者可能的写作的想象的起点。他的记忆中既有《小逻辑》这样的艰深之作,又有《吹牛大王历险记》《唐诗三百首》这样的几乎标准的启蒙读物。这些读物以物象的方式存在,自然牵连到已逝的事物,以及与那些事物密切关联的或熟悉或陌生的人。他们虽以回忆的方式呈现,却潜在地影响着一位优秀的写作者的最初的世界观察。林汉达编著的《春秋故事》有着美妙的叙述。多年以后重读,弋舟迅速从中辨认出一种自己熟悉的风格,他将之称为“自己审美的渊薮”,那里面有“知识与美的传播者平易的姿态,戏谑的格调,耐心的教养,以及不动声色的自信”。他从这里面还发现与博尔赫斯的叙述在文学精神上的“完美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尚不拘囿于文学的精神,它更可能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论,是一个人言说时的根本调性与理解生命时行走的基础路径。”这种调性和根基的确立,是在70年代末,在作者的童年期。童年期出自偶然的阅读,决定了一个人很多年后作为写作者的写作路径。而在十四岁时对于吕新的处女作《那是个幽幽的湖》的阅读,奠定了此后弋舟阅读的偏好。他把自己的文学意识起点,标志在1986年,以及由吕新的处女作开启的可能。这或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发现,而产生这一发现的眼光,当然与吕新以及吕新们的前辈博尔赫斯有关。至此,一个符合现代主义及其在中国催生的先锋小说的思想和审美路径得以形成。这便可以理解何以弋舟对思想、形式以及美学的现代趣味颇多倾心的原因所在。作为“70后”写作者,他们未能赶上先锋小说迅猛发展的时代,但却无可置疑地成为这种写作路线的继承者。可以想见,在文学观念的草创阶段和写作的摸索期。他们可能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过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等以及他们的先驱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伍尔夫、马尔克斯等等。从他们那里,这些大师那里,他们学会了如何思想如何表达,以及对某一种文学的根深蒂固的偏好。并由此在指认自己的写作的先驱的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发现了自己的来路,且预备着由此延伸自己写作的去处。但是,他们与沈从文的自我反思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他们不曾将回顾与反思的触角伸向自我更为广阔的过去,伸向自己曾经有过的现实的记忆,以及产生这些记忆的土地上曾经有并且还在发展着的一切。这块土地当然也有自己的或许不堪回首的过去。和令人难以忍受的现在和无法相见的未来。如果不去思考这些,不从这些记忆和经验中发掘自我更为复杂的来路,或许会错失与仅属于自我的世界独特的相遇的时刻。那种因为这种相遇而可能有灵光一闪的发现也不会存在。
现成的参照,仍然是梁鸿。梁鸿的文学创作,起念于对个人生活状态的不满。如其所言,在写作《中国在梁庄》之前,“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在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她自然习得了一整套指认并演绎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使用得“圆熟”之后,也极容易给人一种真理在握的感觉。但由一些概念范畴和术语建构的世界并不包含个人切身的记忆和现实的经验。那种被阿多称为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于今已成绝响,大多数的理论体系只对其所开启和持存的世界有效,那些千万人置身其中的日常的、粗粝却也鲜活生动的现实,照例被遮蔽或者遗忘。梁鸿不满于这种被架空的生活,她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对现实发言。但这个现实的直接的出发点,却并不是北京,而是千里之外的穰县。在那里,她的亲人们的日常现实,以其难于抗拒的巨大的力量,唤起了一位写作者对自我的发现。她在可能的通道中游走、探索,进入一种生活的内部,她发现了一种与我们此前所知全然不同的现实。这种现实在召唤它的忠实的记录者的同时,也在召唤着一种与之相应的写作方式。这种后来被称为“非虚构”的方式及其所携带的思想和粗粝的美学实践由此而生,并在最为深入的意义上,呈现出当下中国乡土世界的真实面向。既有的秩序逐一崩溃,一切有价值的事物行将消失,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现实”,它的恰如其分的写作者忠实地记录下了它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无法预知的未来。一个人或者一代人如何与历史发生关联。在这里有堪称完美的答案。而从批评家到作家,其问的转换无疑有着“变法”的意味。不仅是知识结构变更这么简单。“历史兑现在有能力将其廓清的主角身上,她也由此享有了解题的权力并且注定要承担问题的重荷。”也因此,她面对着许多亟待澄清的问题。这些问题吸引和困扰着她,当然,也成就着她的写作。“没有一劳永逸的学术、实践和方法,就像没有一劳永逸的人生一样。”她或许时刻准备着新的精神革新的可能,从而使自己始终处于发现之中。
没有人能够自外于这个世界,去过一种被架空的“二手生活”。我们就在世界之中,体会着属于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兴衰际遇,此种际遇也未必仅对个人有意义,它还可能在多重意义上与他者相通,与那些和我们天各一方且绝无可能熟识的人们成为精神与情感上的难兄难弟。这或许便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所在,它所敞开的,只是个人的虚拟的世界,却有无数的可能身份、际遇全然不同的人从中发现自身。无论北京、上海、西安还是兰州,细部的差别无损于我们对世界可能拥有的整全的认识。因是之故,“生活”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只是识力的分野,而非其他。如得“神思”之妙,则“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而从《随园》的写作中,作者已经意识到由“术”进“道”的解放意义。也因此,援引颜昆阳对于庄子艺术精神的如下判断作参照。便不是没有意义的。“‘道是庄子思想所开显的最高境界,此一境界具有主客合一而超越主客之性格,既是主体自由无限之自然心灵,又是客体物物各在其自己的真实。艺术的理想,在于表现这一道的境界,因此它不以个人之情欲成见,以及在此情欲成见观照下之宇宙为其表现之终极。它以个体生命为基础,却能超越个体生命,而提升到普遍的生命的境域。在此艺术观念之下,他的表现便独出于诸多个人表现之上,而为‘表现即再现,再现即表现,主客天人双廻向之特殊形态。”而“主客天人双翅向”之状态,或许是身处这个时代。我们所能设想的最大也最为重要的精神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