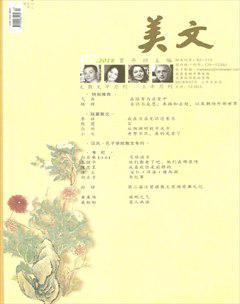苔
熊莺
那些物,有象,或者无象,记录而已。
一、碑
“杨柳堆烟”,是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开篇选注的第一首词——欧阳修《蝶恋花》中的景象,也是先生墓碑后不远处“荷塘月色”旁的镜像。
荷塘边,清霜在一位老者的面前结成一团白雾,他揭下口罩,架好车,湖面,被某个学子或一对恋人砸碎的冰,约一拳厚。早落的失色的柳叶,被子一样轻覆冰面。老者轴一般,整个身子转过去,为你指路:前面,拐过右弯,再往前走。一教学楼的后面,就是(王国维墓碑)。
王国维那时家住何处?1927年6月2日那个清晨,他是路经这里,还是径直走到第一教学楼的对面,那幢白色洋楼,清华学堂里那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公室?
最后一次给学生阅完作业,他跟同事借钱,二洋元——校园至颐和园的人力三轮车费——一趟单程、没有返程。他再没有回来。被八国联军蹂躏践踏得满目疮夷的前清朝皇家园林,颐和园内昆明湖,在他充满复杂情愫的“故国”,生于浙江海宁的江河湖畔的孩子,静静沉入湖底。同时被沉入的,是享誉海外,精通日、英、德文,被郭沫若敬为“新史学开山”的国学泰斗。
人们在先生的衣襟里发现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语,留谜至今。
那日在清华大学听课,我请益老师。老师望向虚空:梁漱溟的父亲也沉湖。
1918年冬前清举人梁济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梁漱溟回:“会。”次日,举人梁济缓缓沉入冰封的净业湖。
2017年,王国维先生沉湖九十年。那日晨,先生的墓碑前清霜穆穆,雪松后面,一株断头的古国槐,槐树顶,勃发新绿。一枝新绿,华盖一般伸向怀里的墓碑。墓碑正面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面,铭有陈寅恪先生痛挽之词。
数字化时代的黄黄澄澄的共享单车,蜻蜓一样泊滿清华大学清华园,新旧两幢教学楼之间的小道。碑后坡上几粒忍冬枝头余下的新泪一样的小果,殷红。
二、香
两座寺庙,楼上楼下,“住”在空山里的山腹中。下面一层叫下古寺,上面一层叫上古寺。在上下古寺之间的陡阶上,一个十来岁的女孩,直着倒在阶上,她抽搐。身旁的两个大人,倒也不很着急。一位是她的母亲,一位是她的父亲。父亲背负白底蓝纹的双肩包。一个背影。母亲从塑料饭盒中取出一枚削净的荸荠,送到女孩嘴里。女孩被父母架着,一步一步往陡阶上走。平静和睦的一家,三个背影。
接引殿前,再次与他们相遇。母亲点燃一炷香,递给女孩,女孩用混沌不清的声音喃喃,怎么能这样?身体往后退缩。母亲说,不怕,有妈妈在。女孩从簇新的羽绒服里伸一只手,小儿麻痹后遗症,留下的狰狞扭曲的一只手。母亲将香放在女儿手中,然后将女儿的手,小心含在自己掌里,她们向着殿里的菩萨作揖。
父亲终于展出一个笑容,上古寺大殿里的师父,迎迓出来,解栏,迎他们入殿。父亲将背包放在地上,白色塑料袋,发出窸窣的脆响,他取出一桶菜籽油,供于香案。女孩显然是认出师父来,她嗷嗷嚷,师父说,知道是你来了。他在女孩子手心写字。传递某种密码一般,他抚摸女孩的头,示范女孩礼佛。母亲臂弯里的女孩,乖乖地双手合十,齐额,身子无法自控,头翻仰过去了,母亲扶正女儿的头,女孩突然安静下来,眼底一丝清明,清亮的光。眉清目秀。
被父母架着出殿,母亲叮咛女儿,脚千万不能踏踩门槛哦,女孩哆哆嗦嗦,铆足劲提腿。父亲回头跟师父打了一躬,现在她(女儿)能走上山了,好多了。父亲所指的是,希望。
师父送走女孩一家人,合上栅门,继续雒诵经文。经毕,以古法唱诵“回向偈”之后,我听见他对着殿上的神明说,王杰龙的女儿生于2002年,请保佑这个女娃娃、天下父母众生,在2018年里,离苦得乐……
这一天。四川凤栖山中。2018年的第一天,元旦。
三、泡菜
安徽安庆市迎江寺振风塔的香案下。一个人影斜进来。迟疑、踱步、梭巡。母亲把他搂得更紧了。日本兵的靴声渐渐远去。那年少年九岁。
南京、上海、安南(越南)、昆明、贵阳、重庆,后来少年去了香港,台湾,美国。一条流亡路线,也是生于1928年的余光中那一代人的人世离乱地图。
在台湾,他居住的时间相对最长,长到花贩货郎已俨然亲人。他去楼下巷口的药店买药,老板娘在柜台后面招呼他。他问老板可好呀,“过身了——今年春天。”老板娘泫然泪下。慈母过世,他去药店买药。流泪的是他了。老板娘嘤嘤相慰。各自的乡音,都不是台湾话。
那年,与霜发满头的余先生在澳门渔人码头的新贾梅士餐厅共餐,长长的餐桌,先生与夫人范我存女士对坐。一道菜,烟三文角、虾仁、蟹柳、鸡蛋、菠萝,外加时令蔬菜做成的“烟三文鱼沙律”,师母用勺子深情款款一点点往先生的碟里送。专栏作家李昂开始聊美食,有人“揭发”李昂曾专程乘飞机,去法国品一道菜。那时,余夫人心中也有一道菜:
1938年,四川乐山,兵荒马乱。每个清晨,上学路上,她会经过一位老人的门前。老人老到牙都没了。他坐门前吃饭,一碗白米饭,一碗四川泡菜,老人一口饭,一口泡菜,一口饭,一口泡菜。就这么吃着……
“仿佛好吃得不得了。”说这话时,当年7岁,从南京转移至“大后方”乐山的少女已80多岁。
有的餐厅再远我们终可以抵达。而有的食物分明是一段光阴,怎样启程,如何前往?“外红、内白的那一种萝卜皮……”余夫人一口川音,转脸望向从四川去的我。
在美国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时,他确定自己的故乡在台北。在台北,他确定自己的故乡在大陆,而大陆那一边,又分明没有自己慈母慈父的慈骨与祖牌。如今余先生过世了,魂归何处?母亲长眠台湾圆通寺,不只是光阴、无边乡愁染白了须发睫毛的先生,在圆通寺,不知是否已与慈母,相遇?
四、经书
成都,一群修行人。因缘际会,你也被拉入这个“微信群”里。每个夜里,已习惯进去看看:
今日功课完成。回向给众生,回向给某某(自己或同修往生的亲人)。祈祷表情。
因故功课未完成,她(他)如实陈情,今日功课未完成。忏悔,回向给某某。祈祷表情。若遇天灾,回向内容则统统改为回向给灾区所有有情、无情的众生。
暴雨天,留言最是让人着急:
@某某某,你走到哪里了?
@所有人,有谁需要搭乘我车?
@所有人,请提前到的同修,止语。在经堂静候。
有人远足,“出台北机场,遇到一位师父,我双手合十行礼,一旁人也在给师父行礼。真好。”有人回应,“随喜一路参学,见闻觉知,精进用功。”
作业也会布置在群里,某一段,他们正学习《佛法概论》。
他们人中有护士、律师、会计、职员。也有寻常人。新加入者往往在群里怯生生地问:“我学识浅,请问寺外有残疾人行乞,要行布施吗?”
有同修回:“要。‘下心含笑,亲手遍布施。要起慈悲心,祛分别心。”
问者存疑:“会不会助长乞行?”
同修回:“行乞人,‘着了一个‘相。当‘对境显现时,我们的第一要义是要反观自己,是否生起慈悲心?”“财,是一种布施,念佛回向也是。悉心听他说说话,也是布施。这叫大悲心!”
“下心含笑”,你赶紧起身去查,语出《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品,佛告地藏菩萨:
“是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遍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慰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
下心,慈悲心,智慧心。纵九五之尊布施,“示现”佛境之笑,发正念布施(非施舍),才是“正”布施。
那个夜晚,灯下抚手中经文,莲花处处,八埏九垓,一派纯真。
五、路
成西(成都——西安)高铁。从西安上車,广播开始播报,前方到站阿房宫站,身旁的老师呢了一声,秦朝。列车当然无法载我们前往秦朝,但那时我手中,苏童版本的《武则天》,正翻到唐朝历史上的这一页:
“碧落黄泉,一了百了吧。好吧,现在就死。李贤说,我会让你如愿回宫交差的。
“丘神劫(大将军)听见了李贤抽解腰带的窸窣之声,听见了白绢跨过屋梁的沙沙的摩擦声,丘神劫伏在板墙的孔隙前,耐心地观望着李贤自缢前的每一个步骤,白绢容易滑脱,绢上可以打一个死结,丘神勣对着孔隙说,最后他听见了自缢者踢翻垫脚凳的响声……”
李贤。女皇的次子,也疑为女皇的姐姐与帝王的孩子,是不是一切将要水落石出?或者,太子李贤真有谋逆之心?贤被贬为庶民,放逐巴州(今四川)。女皇终究还是放心不下。贤不是女皇所弑的第一位亲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位。
那一瞬,我想知道的是,贤之死,是女皇写下《金刚经》前,那一段著名的发愿文——“开经偈”之前,还是之后?“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千年来,流传至今,据说唯有女皇。深得经义玄妙稀有。
记得那一年。邀请台湾作家张晓风老师来四川,她执意先飞西安,再转道火车而来。她要亲自翻越秦岭,那个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诗文的秦岭,当然也是29岁的李贤,单衣薄履,从长安出发,必经的“苍苔留虎迹,碧树障溪声”的秦岭。晓风老师那日乘慢车抵达成都,她说,夜黑,什么也没看见(她后悔没有搭乘汽车,走老路)。那日我乘高铁,清寒明丽的上午,同样,什么都没有看见。
其实,无关时速,无关昼夜,无关古道新路,同为母亲,或许有些世事,我们终归是看不懂而已。尽管千年之后,我们凑巧与李贤同行了一段路。从长安到四川,过秦岭。
六、烛
闹市之中,藏有一间不为人知的小寺?那日从德胜路往文武路方向驶,车向右,拐入草市街,红灯亮起,越过车窗,你看见一片旧厝青瓦之上,果然有庙影,孤帆似的几笔。
山门不大,抬头望,金沙庵。原来是一间女众寺院。山门殿后面,一方天井。再进去,略开阔一点的院坝。殿与殿之间、须弥座与后门的最逼仄处,仅一肩宽。总有一种误入深宅大院的错觉。服务生,多迟暮老人,她们捆围裙,戴袖套,踽踽行走。每一张香案前,有尼师正摆放供果,洗净的苹果,一枚一枚垒成一盘盘小山。
是不是因为是一间女众寺院,阶面、地上,满是柔情。香案上换下的黄菊、百合、紫罗兰、石竹养在藏经楼前阶上的各式器皿里,桂花、芭蕉、海棠、茶花、苏铁、昙花,种在大大小小的花盆中。一个女子,端一盆清水往花盆里浇,我们相视而笑。
她是义工。初来这里时,她记得,如同串门子,穿过一条街就到了。那时她刚离婚,婚姻是何模样,她不知,但一定不是现在的模样。走进来,从蒲团起身,尼师缄然,递过一粒冰糖,看着她慢慢含在嘴里。那年她二十九,女儿五岁。如今女儿也同样被一些“实相”所惑,移民国外。国外的生活到底该是何等模样呢?女儿在新西兰做油漆工,女儿女婿一道替人翻修房屋。还好,还好,如今,为母有大把的时间来到这里。来抄经文,或许只是来坐坐。一小时的公交车程。从城南的新家,远远赶来。
后来知道,翌日是今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旧历十五。女子问我,明天要不要来吃斋?
成都保留下来的这半爿老街,深宅似的古庵,那日人头攒动。我们背着对阳光烤太阳,蜡烛繁星一样燃在我们身后的案上。不时有老人认出她来,她转过身笑,“好多从前的街坊,老街拆了,都搬走了,但这一天,再远,都准回来。”是不是,这些老人们一如当年的她,起了心事又或者无事,几步路,串门子一样,一颗安静的心,走进来,走出去……
七、木屋
牙,略略内合,使她显得不胜娇羞、甜美,她用牙咬破指尖。蘸血写下:我愿意去云南建设兵团。那一年,女孩十六岁。她没有跟老师同学父母,任何人商量。
很多时候,上学路上,她在前面走,后面有人猛然拾一块石,砸向她,狗崽子。挣脱“旧军官”父亲阴影唯一的方式,是不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呢?那个“跌倒了可吃菠萝,躺下时可吃香蕉”的地方。热水瓶、脸盆、军用胶鞋,一一用网兜兜住,绑在行李被子上。母亲例外给她缝了一件碎花新衣。与两千多名学生一道,女孩登上了从成都开往云南的列车。
火车启动时,那个四月天。部队文工团的招兵信函,也同步抵达。此前,她去报考过部队文工团。父亲跟来人讲:“孩子刚去车站,没准能追上。”女孩收到父亲辗转而来的信时,已是一月之后。两月后,父亲读着女儿的回信,先是笑,继而哭,然后冲出门,沿着成昆铁路,向着云南方向跑。一周后。人们在四川峨眉山站的一个道班口,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这位出生地主家庭,学无线电。战争年代做过电台台长,后来投诚的普通人。1971年,那个夏日,女孩的父亲精神失常了。
糊涂时,不识女儿,清醒时,老人眼里总蓄满泪。老人育有六子,女孩最小。女孩一生给父亲写过许多信,唯第一封,至今想来,她望向天空,泪流不止,“第一年就考上了,我家庭成份不好。”于是女孩负气回信:“我们,命运多舛,都是因为你……”据说,老人是在女孩返城工作之后,兴奋过度,过世的。
做过许多工作。如今六十三岁的文姐一家人,在凤栖山下的古镇上,盘下一处旧院,开了一问清雅极简的水饺店。由儿子儿媳经营着这间,于小镇而言鹤立鸡群,童话般的静静的木屋小店。
八、露台
有鸟咕咕,有人嘎嘎。我站在卧室门口,远远看见露台上,他正与鸟说话,看你以后还来不来?鸟,扑棱扑棱挣扎着,在他手中。走过去,见另一只鸟,站在对面的屋顶,战栗着,羽翼半张半合,惊恐张望这边。
不是容不下一只鸟,不是没有想办法让鸟与菜,各自相安无事,只是,动物法则,田野法则,自然法则,原本这种鸟——斑鸠,种子、谷物、小菜苗等,就是它们的食物。曾经试着放一点米在露台,结果引来更多的鸟。菜苗所剩无几,买来专门的网,罩住菜地,阳光受限,菜不生长。
斗智斗勇最常见的一幕,是门“哗”的一声开了,人跺脚的笃笃声,鸟惊飞的噗噗声,人嘎嘎地驱赶声。万籁俱静。
地里荒了很长一段时间,鸟也不再来了,我们松了土,给地上沤上油枯,秋种最后的时间,驱车去远方的集市买回菜苗,青菜、棒菜、兒菜、莴笋、红油菜等等,打窝,下种,浇定根水,调试喷灌系统。菜苗孩子般从地里站立起来,婴儿一样的脸。鸟们又蠢蠢欲动,想回来了。
每一棵菜都是生命,隆冬了,如今所有生命、这些菜都长起来。今年小小的菜地,墒情好,那些菜,仿佛特别着急,还来不及生长,菜叶就皱缩成花骨朵一样,一个个打起叶浪子来。红油菜,总是泛出红酒一样流淌的光泽。
并不是鸟们听话了。某一天,我在家里找出几柄绢扇,薄如蝉翼的扇,绑它们在竹枝,在晒衣绳,在夏天留下的瓜架下,绢扇无风自舞。后来家家户户的露台,都学了我们。小鸟终究不比人聪明,它们以为那是人,不再来了。
那只鸟。是自己扑到玻璃护栏里,束手就擒的。被谈话之后,放了它。在这个只有高楼、绿树与人流的大都市,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小孩一样的那些鸟。不知还有什么可吃,它们最初从哪里来,又去哪里了。
九、窗
护栏上的木条被阳光照耀。藤条的转椅背窗而倚,假如转椅里的人不抬头,假如一只鸟从窗外向里看。它会看见,有木,有藤,于是它一头朝着我家的落地玻璃窗,俯冲过来。窗前人正阅读,吓得一惊,无辜地张望。玻璃上,出现了一只完整的鸟形,灰扑扑的隐约鸟形。
下楼找回那只大鸟,是斑鸠,头歪着,身体还温热。躺在我家阳台木地板上,颈部的鸟羽泛出金属一样的斑斓辉光,娇弱的一份贵气。我用手机去查斑鸠,搜出来,晚上怎样抓斑鸠?捉斑鸠哪种方法最好?斑鸠怎么做最补?家里飞来一只朱颈斑鸠,怎么养?《晚上怎样打斑鸠》一文这样介绍:
“如果你在一片林子里白天已经打了,尤其是天黑前,已经惊过了那片林子,晚上通常斑鸠不会再歇回林子了。在打斑鸠过程中,我发现斑鸠回林之前,都是先到其他林子旁边的地方观察,而不是直接回到它要停留的地方……斑鸠在夜里,用电筒一照,就吓傻了”。
再搜,斑鸠性羞怯。不易接近。
再搜,斑鸠是《诗经·关雎》里的雎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此,斑鸠是爱情忠贞不渝的象征。那样的爱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不对,去找书,三秦出版社的《诗经》注释:“雎鸠,一种水鸟,传说此种鸟雌雄终生相守不离。”有禀性急躁者沉不住气了,“不要争论了”,假定之后,于是引闻一多在《诗经通义》中话:“相传此鸟雌雄情志专一,其一或死,其一也就忧思不食,憔悴而死,极笃于伉俪之情。”莫衷一是,不一而足。不甘心,去找书架上的《尔雅》,这时,那个秋日,我们听见,我家的阳台上,一只斑鸠静静地躺着,少女熟睡一般,另一只,在阳台外,围着我家屋子,呜咽,“咕——咕,咕——咕”,整整一天。阳台于层林之上,鸟巢一般。斑鸠是不是雎鸠,真的不重要了。
十、苔
冬日的山径,那些失色的青苔,让人依旧不敢轻易落脚。地毯一样布满石阶的那些苔藓,你看不见原先的土地。山径的一侧,是一座寺院,另一侧,是一座书院。站在山径龙脊一样隆起的峰峦,你可觑见书院的一隅,一群黄鸡,正围盆啄食,大片的书院屋宇,静若虚空。而另一侧,那寺院,隐在丛林最深处。
书院里的女主人,原本是这凤栖山中那座寺院的居士。那时,庙不成庙,因缘具足了,她褪去红尘霓裳,换上了一袭灰布青衣。据说是一位作家将一笔巨资稿费慈悲相赠,居士修了一条从寺院通往山外的路。后来,寺院重建,居士与寺院,业已缘尽。
寺院仿佛自古以来,就是人世间最后的一条退路。譬如武则天之于感业寺,冯小青之于孤山“佛舍”,不论被动或是主动。寺外的几条山径,是理想的登山路,曾经误走误撞,我们撞到了书院。也是楠木参天,也是青苔荒阶,霎时间,一座“城”临空而现。高墙、深宅。我们轻轻叩门,闻犬吠。有门童样的女子探出头来。
院中有院。深院里,设佛堂、茶舍、客房。行廊与客房里,多有藏书。居士那晚留我们晚餐,厨房里,两只狗静静卧地,山中的女子,在厨房里无声忙碌。都是些书院菜地里种的小菜,饭间,某一瞬,居士嫣然一笑,要是你“伯伯”在,又该说我了,不会做饭。
居士所说的“伯伯”,仿佛刚刚放箸,下山沽酒去了。静好雍容的老居士那年七十二。一径之隔的普照寺里,将晚未晚时分,应还看得清那一通碑,碑的背面,“伯伯”致居士的诗,当年的当家居士。令工匠刻在了上面:
山外红尘,山中古寺,两不相扰,各行其志。
一九八六年仲秋流沙河
算来,这对曾经的至爱,文学夫妻,不相往来,已三十二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