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归桥,路归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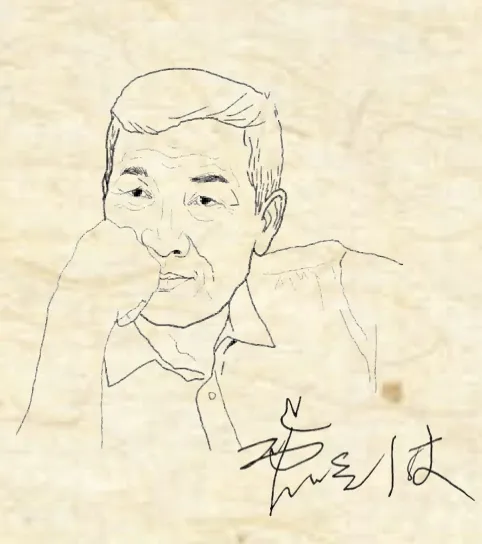
老杭城的地名,大多以街、巷、弄、桥、里、营、园、阁、庙、寺、湾、荡、井等为名。也有以某官署的方位命名,如行宫前、察院前、贡院前、三衙前。其实,民国以前,除了十大城门内的十大直街,以及四大营门的几条直街外,老杭州城内的“街”还真不多。当然,“路”也有,但在《武林坊巷志》中,“路”却只有一条,那就是清营跑马场边的“马路”。
《武林坊巷志》,清末名绅丁丙编辑,是以所收录的地名为“条目”,洋洋洒洒铺陈开的一部城市历史巨志。其中,以“巷”名为最多,所以,书名也称《武林坊巷志》。在这部巨作中,仅次于“巷”的地名,就是“弄”与“桥”。
“桥”是一个最独特的地名,《武林坊巷志》载有九十六个“条目”,仅次于巷、弄。但是,和巷、弄一样,“桥”,也有人事、掌故,也有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文字。可见,在地名中,“桥”不仅仅是一座桥,也有一条巷的人文历史承载。
以“桥”命名的“巷” “街”也有,譬如“李博士桥”与“李博士桥巷”,“仁和仓桥”与“仁和仓桥街”。各条目中的表述,也各有区分,也各有上千的文字。这一种时而将“桥”与“巷”“街”作为一体表述;时而又将“桥”与“巷” “街”分别表述的做法,应该就是杭州话“桥归桥,路归路”,互不搭界的最初源头。
在1914年以后逐年的城市建设中,杭州城内的“路”名也多了起来,譬如当年6月在旗营废墟上呈“井”字出现的四条路,其中三条分别横跨在井亭桥、八字桥、龙翔桥上。费解的是,只有湖滨路例外,其他三条,都以被推翻的满清营门为名:迎紫路(现解放路)、平海路、延龄路,而不是以传统的“桥”命名,似乎大违革命的初衷。
后来出现的各条“路”,也无一例外,虽然将曲里拐弯的小巷、小弄变成了整齐划一的宽路,依然忽略了横跨各条河流上的“桥”名。不少的路名还是带有满清的影子,如兴武路(现开元路)、惠兴路。当六七十年以后,不少河流被一一填埋,不少桥梁也就此拆毁,淹没无名。所以,在那些名噪一时的“路”上,所剩下的赫赫有名的桥名,往往也让人有“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的感觉,譬如龙翔桥、众安桥、井亭桥。看起来,老杭州人最初说的“桥归桥,路归路”,在后来的城市变迁中,似乎也在被逐渐验证:一条路名一旦与一座桥名脱离,还真会带来因缘两分,无从说起。
“东街”一例,尤其有趣。当民国初期,狭窄的石板路拓宽成了碎石路,命名居然是“街”与“路”的简单相加,不尴不尬叫了“东街路”(现建国北路、建国中路)。如果以此路的“横河桥” “银洞桥”为名,也就多了一份市河纵横的历史记忆。
“坐不改名,行不更姓”的桥名也有:1917年,安徽籍五大上将之一的“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主浙,仅仅带兵一个团来到杭州,就轻易摆平了督军吕公望与下属警察厅长夏超结下梁子的大乱,接任了浙江督军。那时的督军府在梅花碑,杨善德住板儿巷(现建国南路)147号,他每天要过斗富二桥那条小石桥连接的小街,小桥的石阶中有一条不宽的陡坡,只能供得独轮木车轱辘嘎吱上下。杨善德为自己带来的轿车行驶方便,改建了斗富二桥,连同一条宽宽的“斗富二街”。当然,“斗富一桥”与“斗富一街”,“斗富三桥”与“斗富三街”,前清时都有,不过是后来“宽”了。好在“宽”了以后,还是没有忘本,还是能看出桥的影子。
有人说,杭州人好“东西称‘街’,南北叫‘路’”。其实,街与路的命名也并非如此规范。譬如,在民国时期以十大名人作为命名的路中,静江路(以当时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命名,现北山路)、教仁路(以当时的法制院院长宋教仁命名,现邮电路)、中正路(以蒋介石的字中正命名,现解放路)、性存路(以当时省法院院长阮性存命名,现庆春西路),都是东西向的。只有中山路(以孙中山命名)、膺白路(以当时的外交部长黄膺白命名,现南山路),是南北走向。
不过,这其中有一条规例,似乎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那就是路中的桥名再怎么显赫,路名都不会因此借光,反倒是横空出世,响亮一时。也所以,老杭州人总喜欢用“桥归桥,路归路”来表达一种互不搭界的态度,而这一种说法,往往用在“丁是丁,卯是卯”的貌似坚强的口吻上,很有一点一言九鼎的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