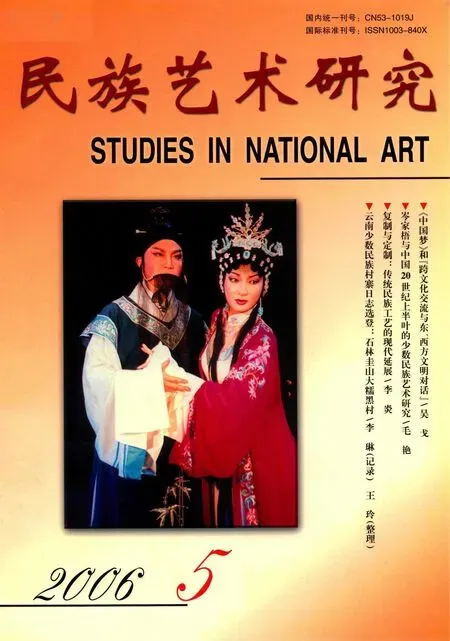祠高禖:从 “交天侑神”到 “令会男女”
于 平
关于 “高禖”之祠,在 《礼记·月令》如此记载:“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曰,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陈·注曰: “高禖,先禖之神也。高者,尊之之称。变媒言禖,神之也。占有禖氏拔除之祀,位在南郊;禋祀上帝,则安配祭之。故又谓之郊禖。”这段记载告诉我们:“祠高禖”是在 “仲春之月”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活动的地点 “位在南郊”;时间的 “仲春”和空间的 “南郊”,都意味着要顺应天地之 “暖意”,开启男女之 “人事”——如 《周礼·地官·媒氏》所言:“媒氏掌万民之判……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 “媒氏”之 “媒”, 《说文解字》释曰 “谋也。谋合二姓”;与其同部的“妁”,则被释曰 “酌也。斟酌二姓也”。从我国旧式婚姻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看,“媒氏”的工作就是撮合 “男女之事”的;而所谓 “祠高禖”,隐喻的便是 “男欢女爱”那点事——这在原始部族的生存发展中是极其神圣的。
一、从姜嫄 “履大人迹遂有孕”谈起
《诗经》中有一首最长的诗,全诗共九章一百二十句,是 “鲁颂”中的 《閟宫》。“閟”的音义皆同于 “袐”,是 “神”的意思;“閟宫”即 “神庙”,在此特指周代先祖后稷之母姜嫄之庙。该诗的第一章写道:“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①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译注道: “肃穆清静姜嫄庙,又高又大人稀到。姜嫄光明又伟大,品德纯正无疵瑕。上帝凭依在她身,无灾无害有妊娠。怀足十月没拖延,后稷诞生她分娩。上天赐她百种福:穈子高粱都丰足,豆麦先后播下土。后稷拥有普天下,教会百姓种庄稼。高粱小米长得好,还种黑黍和香稻。四海都归后稷有,继承大禹功业守。”平心而论,或许是为了凑齐 “七字句”,此 “诗”显得寡淡无味,但也让 “诗意”浅白易懂。这本是歌颂鲁僖公能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的诗,但却从中流露出与 “祠高禖”相关的、初民们部族繁衍的风俗。
关于 “仲春之月”的 “祠高禖”,其中“祠”的意思是特指 “春祭”,这个祭祀不用牛、羊、猪、鸡、鸭、鹅等 “牺牲”,只用“圭璧”及 “皮幣”——前者是 “美玉”而后者是 “锦服”。“高禖”之所以又称为 “郊禖”,在 “祠祭”之际也包括 “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 “野合”——传说中就记有简狄从帝 “祠郊禖”之时,吞玄鸟所衔之卵胸剖而生成汤;也记有姜嫄助祭 “郊禖”之时,见大人迹履之遂有孕而生后稷……而这些无从稽考的 “吞玄鸟卵” “履大人迹”便有孕在身,其实是 “野合”由隐秘而神秘、由神秘而神圣的一种 “托词”,是将 “奔者不禁”的 “令会男女”上升到 “交天侑神”的高度,而所谓的 “交天侑神”是女性自愿自觉的奉献——为着完成部族繁衍的神圣使命。
二、女娲 “欲人之生”而 “作 《充乐》”
《诗经·鲁颂·閟宫》一诗,反映出将“祠高禖”的对象具体到周之先祖姜嫄;而据有关史料,“高禖”之神最初当是女娲。《路史·后记》载:“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 (通 ‘婚’)姻。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高禖之神。”又载:“(女娲)作 《充乐》。用五弦之瑟于泽丘,动阴声,极其数而为五十弦,以交天侑神。听之悲不能克,乃破为二十五弦,以抑其情,具二均声。乐成而天下幽微无不得其理。”以上记载使我们得知,女娲是最早的 “女媒”,也即 “高禖之神”;女娲制作了 《充乐》,使 “天下幽微无不得其理”。我们知道,女娲亦称为“娲”,《说文解字》释为 “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何为 “化万物者”?据 《中华古今注》之 “问女娲笙簧”条载:“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娲,伏羲妹,人首蛇身,断鳌足而立四极,欲人之生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可以说,正因为女娲 “欲人之生而制其乐”,所以才有 “乐成而天下幽微无不得其理”——这其中的 “天下幽微”正是 “人之生”!
女娲 “欲人之生而制其乐”为何名之曰《充乐》呢?“充”,本为 “注入”之意——至今所谓充气、充电、充值等无不如是。《说文解字》释 “充”为 “长也,高也,从儿育省声”。这就是说,“充”其实是个上 “育”下 “儿”的会意字,省却了 “育”下的“月”,成了由 “儿”填补的 “充”字。中国古典美学有 “充实之为美”一说,从根源上来说,这 “美”与 “注入”相关,更与 “注入”的 “实”与 “满”相关。在此,顺带提一下伏羲的 “长离 (即 ‘风’)来翔,爰作《荒乐》。”②引自 《路史·后记》。《荒乐》之 “荒”,《说文解字》释为 “芜也……一曰草淹地也。” “草淹地”就农耕文明而言不是好现象,它意味着庄稼绝收,故曰 “荒芜”;但就游牧文明而言,“草淹地”却是大大的好事,是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兴旺景象。可以说,伏羲的 《荒乐》意味着食物的丰足,而女娲的 《充乐》意味着族群的繁盛。
三、不合时宜的 “烂漫之乐”与 “北里之舞”
明代朱国桢 《涌幢小品》载:“葛天氏始歌,阴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埙、箫,女娲作笙、竽;黄帝作钟磬鼓吹、铙角鞞钲、制律吕、立乐师;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鼗,桀作烂漫之乐,纣作北里之舞,周有四夷之乐,穆王有木寓 (偶)歌舞之伎;秦蒙恬作筝,汉田横客作挽歌,汉武帝立乐府,作角觝、鱼龙曼衍、吞刀吐火之戏,梁有高絙舞轮之伎;唐高宗置梨园作坊,玄宗置教坊、倡优杂伎,元人作传奇……”这段表述俨然一部演艺发生简史。关于人类的 “演艺发生”,库尔特·萨克斯在其《世界舞蹈史》指出:“在原始社会里,一般的舞蹈经常用歌声伴奏,一切歌曲都是为舞蹈编造的;事实上,除了舞蹈歌曲之外就没有别的歌曲了。”①库尔特·萨克斯:《世界舞蹈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鲁迅先生在 《汉文学史纲要》中亦指出:“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浸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祗畏以颂祝……复有巫觋,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kuàng,‘赐’之义)。”萨克斯所谓 “舞蹈经常用歌声伴奏”,鲁迅先生所谓 “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都指出了原始社会、原始之民 “歌、舞、乐”发生时的 “一体性”。
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 《涌幢小品》中所言的 “桀作烂漫之乐,纣作北里之舞”。所谓 “桀作烂漫之乐”,即 “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譟于端门,乐闻于三衢”②引自 《管子·轻重》。,也即 “(桀)广优猱戏奇伟作东哥,而操北里,大合桑林,骄溢妄行,于是群臣相持而唱于庭,靡靡之音。”③引自 《路史·后记》。;而所谓 “纣作北里之舞”,即 《史记·殷本纪》所载:“(帝纣)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很显然,无论是 “烂漫之乐”还是“北里之舞”,已与 “仲春之月”“位在南郊”的 “令会男女” “奔者不禁”无内在关联了——因为那个神秘而神圣的 “祠高禖”已经成了 “骄溢妄行”“大聚乐戏”的 “新淫声”了 (所谓 “淫者,过也”),已经需要按照“思无邪”“乐而不淫”的价值准则来 “移风易俗”了。这或许就是为何后世仍有巫之“求雨之祭”、傩之 “逐疫之祭”、蜡之 “祈丰之祭”,但却不见 “祠高禖”之 “欲人之生”之祭了。
四、“淫于声而害于德”的 “郑卫之音”
“桀作烂漫之乐”,自然是 (商)汤讨桀罪的内容之一;而 “纣作北里之舞”,也必然列入 (周)武王对纣讨伐的理由。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尚书·周书·泰誓下》亦言:“今商王受……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请注意,这里所言的 “变乱正声”“作奇技淫巧”,居然是为了 “悦妇人”——这当然是只重 “欢修夜之娱”而与 “欲人之生”无关了。
虽说周武王以此为理由 “作太誓”以伐纣,但至东周列国的 “春秋”时期,前述“新淫声”变身 “新乐” (如 “郑卫之音”)仍然被帝王作追捧。据 《礼记·乐记》载:“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礼记·乐记》的这段话分析得很透彻。所谓由 “新淫声”变身 “新乐”的“郑卫之音”,其实远不止 “郑卫”;将其从“祭祀”中逐出是因为它 “淫于色而害于德”。
五、郑卫之乐 “所以娱密坐,接欢欣”
我们知道,回答魏文侯提问的子夏,是孔大圣人的弟子。如果说,周公对于我国古代乐舞文化建设的功绩在于承 《云门》、续《箫韶》,使 “六代”之乐各用其 “祀”;那么孔子在这方面的功绩便在于 “从先进”“从周”,使 “八佾”之乐统于一 “礼”。历代先王 “功成作乐”的传统,至孔子之时需讲究 “制礼作乐”了。《论语·阳货》载孔子之言:“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可见对 “淫于色而害于德”的 “郑卫之音”深恶痛绝;他还格外强调要 “乐则 《韶舞》”,要 “放郑声,远佞人”。于是,在 《乐则韶舞》的 “礼乐”之外,被儒家学者认为 “淫于色而害于德”的 “新乐”另成一类,因其以 “悦妇人”为特征而被称为 “女乐”。
春秋战国时期, “女乐”往往被视为“侈乐”,如 《吕氏春秋·仲夏记·侈乐》就指出 “(桀)作为侈乐……以巨为美,以众为观。”因为 “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譟于端门,乐闻于三衢。”①引自 《管子·轻重》。至西汉时期,已发展到 “公卿列侯亲属近臣……设钟鼓,备女乐”②引自 《前汉书·成帝本纪》。;更有 “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③引自 《前汉书·礼乐志》。。当然,此时 “女乐”大多以此为业,技艺水准大大提高。据东汉傅毅 《舞赋》所述:“楚襄王既游云梦,使宋玉赋高唐之事,将置酒宴饮,谓宋玉曰:‘寡人欲觞群臣,何以娱之’玉曰: ‘臣闻歌以咏言,舞以尽意…… 《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噫!可以进乎?’王曰:‘如其 《郑》何?’玉曰: ‘……郑卫之乐,所以娱密坐、接欢欣也。余日怡荡,非以风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姁媮致态。貌嫽妙以妖蛊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涕而横波。珠翠的砾而炤耀兮,华袿飞髾而杂纤罗。顾形影,自整装,顺微风,挥若芳……形态和,神意协,从容得,志不劫。于是蹑节鼓陈,舒意自广;游心无垠,远思长想。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飞散,飒擖合并;鶣鷅燕居,拉楂鹄惊;绰约闲靡,机迅体轻。姿绝伦之妙态,怀慤素之洁清。修仪操以显志兮,独驰思乎杳冥……”④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由此可略见一斑了!
六、从曹植、白居易到李渔的 “女乐观”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女娲是最早的 “女媒”,是 “欲人之生而制乐”的最早的 “女乐”;但自 “桀作烂漫之乐,纣作北里之舞”以降,“女乐”使开始 “异化”—— “祠高禖”在后世不再成为 “礼乐”之构成,不再成为庄严肃穆的祭祀也说明了这一点。东汉时傅毅 《舞赋》借楚襄王宴饮而说事,其实正是本朝事象的呈观。细读曹植的 《洛神赋》,你都不用怀疑赋中的主角正是他理想中的 “女乐”,是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环资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是 “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是 “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是 “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休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①(三国魏)曹植:《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4页。……其实,只要读读曹植所写的 《妾薄命》,你就不会怀疑这一点,曰:“主人起舞娑盘,能者穴触别端……任意交属所欢,朱颜发外形兰。袖随礼容极情,妙舞仙仙体轻。裳解履遗绝缨,俯仰笑喧无呈。”②(三国魏)曹植:《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自 《前汉书·礼乐志》说时人 “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以来,后世呈未必 “与人主争”,但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蓄养 “女乐”——因为往往居家供人享乐而又称为 “家乐”。比如唐代文人白居易,在 《醉吟先生传》中就写到 “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箧。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 《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 《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 《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③(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85页。再比如清代文人李渔,在其 《闲情偶寄》中谈道:“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习声容也。欲其声音婉转,则必使之学歌;学歌既成,则随口发声,皆有燕语莺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体态轻盈,则必使之学舞;学舞既熟,则回身举步,悉带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古人立法,常有事在此而意在彼者。”④(清)李渔:《闲情偶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139页。这其实是指出,古人对 “女乐”以及“家乐”的欣赏,是讲究 “色艺俱佳”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讲究 “以艺添色”的。
七、“奔者不禁”即 “先野合而后俪”
我国文化传统素来看重 “礼失求诸野”,看重 “乐失亦求诸野”。从清代陆次云所作《炯溪纤志·苗人跳月记》来看,就颇有远古“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之遗风。文曰: “苗人之婚礼曰 ‘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载阳展候,杏花柳稊,庶蛰蠕蠕。箐处穴居者,蒸然蠢动。其父母各率子女,择佳地而为 ‘跳月’之会。父母群处于平原之上,子与子左,女与女右,分列于广隰之下。原之上,相宴乐,烧生兽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砸酒而饮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则椎髻当前,缠以苗悦。袄不迨腰,裈不迨膝,裈袄之际,锦带束焉。植鸡羽于髻巅,飘飘然当风而颤。执芦笙,笙六管,长二尺,盖有六律而无六同者焉。女亦植鸡羽于髻如男,尺簪寸环,衫襟袖领,悉锦为缘。其锦藻绘逊中国,而古纹异致,无近态焉。联珠以为缨,珠累累扰两鬟;缀贝以为络,贝摇摇翻两肩。裙细褶如蝶版。男反裈不裙,女反裙不裈,裙衫之际,亦锦带束焉。执绣笼,编竹为之,饰以绘,即彩球是焉。而妍与媸杂然于其中矣。”至此之际,基本上是背景的介绍和 “令会男女”们的着装描写,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很郑重的仪式。
接下来:“女并执笼,未歌也,原上者语之歌而无不歌;男并执笙,未吹也,原上者语以吹而不吹。其歌哀绝,每尽一韵三迭,曼音以缭绕之。而笙节参差,与为缥缈而相赴。吹且歌,手则翔矣,足则扬矣,睐转肢回,首旋神荡矣。初则欲接还离,少且酣飞畅舞,交驰迅速矣。是时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数女争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择者,有数男竞近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复相舍,相舍复相盼者。目许心成,笼来笙往,忽然挽结。于是妍者负妍者,媸者负媸者;媸与媸不为人负,不得已而后相互者;媸负见媸终无所,负涕洟以归,羞愧于得负者。彼负而去者,渡涧越溪,选幽而合;解锦带而互系焉,相携以还于跳月之所;各随父母以还,而尔议聘。聘以牛,牛必双;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后俪,反循蜚民之风。呜呼苗矣!”这里的 “野合而后俪”,其中 “俪”是 “成双成对”之意;而 “反循蜚民之风”的 “蜚民”,指的就是前述 “箐处穴居者”的初民。比较 “跳月”和 “祠高禖”,虽然前者已无后者的“以太牢祠于高禖”,但却具有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一致性。对于 《周礼·地官·媒氏》中所言 “奔者不禁”,陆次云 《跳月记》给了我们具体的描述,也即 “彼负而去者,渡涧越溪,选幽而合”——这种 “幽合”或者说 “野合”,也正是女娲 “作 《充乐》……乐成而天下幽微无不得理”之解。
八、要知道 “从哪里来”更要思考 “往何处去”
还想谈一谈新中国成立后,海南黎族同胞的 “三月三”。笔者曾在 《汤显祖诗文集》中读到一首 《黎女歌》,曰:“黎女豪家笄有岁,如期置酒属亲至。自持针笔向肌理,刺涅分明极微细。点侧虫蛾摺花卉,淡粟青纹绕余地。便坐纺织黎锦单,拆杂吴人彩丝致。珠崖嫁娶须八月,黎人春作踏歌戏。女儿竞戴小花笠,簪两银篦加雉翠。半锦短衫花襈裙,白足女奴绛包髻。少年男子竹弓弦,花幔缠头束腰际。藤帽斜珠双耳环,缬锦垂裙赤文臂。文臂郎君绣面女,并上秋千两摇曳。分头携手簇遨游,殷山沓地蛮声气。歌中答意自心知,但许昏家箭为誓。椎牛击鼓会金钗,为欢那复知年岁。”①(明)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36页。在这篇 《黎女歌》中,你看到的是一位黎女由 “待嫁”而 “出嫁”的全过程:到了 “及笄”之年,便要“置酒”属亲,然后要 “自持针笔”,以 “青纹”绣面;借春日 “踏歌”之际,戴花笠、着花裙、绛包髻、加雉翠;与如意郎君 “并上秋千”,答意对歌;一旦以箭誓婚,便 “椎牛击鼓”相庆——还特别强调 “春作踏歌戏”(相恋),“嫁娶须八月”。
由此,我想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扎根海南,创作了 《三月三》这种黎族舞蹈经典的陈翘先生。为了创作这个作品,陈翘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深入到美孚黎地区体验生活。管琼著 《陈翘传》写道: “五十年代……黎族同胞对于性爱很开放。他们小小年纪结婚,但在日后一次又一次的 ‘三月三’中,享受自由的情爱。在 ‘三月三’这一被当地黎胞视为法定的情人节里,已婚的落夫家和未落夫家的中青年合法地离开妻子丈夫去幽会或寻找自己的情人;年纪更小的则加进了大人的队伍中,四处凑热闹,为自己以后的 ‘三月三’积累经验。”②管琼:《陈翘传》,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陈翘创作的群舞 《三月三》表现的当然不是 “性爱很开放”而是 “男女很纯情”,但管琼在 《陈翘传》中写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政府曾经下发取缔黎族地区 ‘三月三’的通知,指出这一习俗是封建残余,并且造成性病泛滥。但多次行动都无法落实,只因为这一传统节日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情感的需要,它是黎族百姓几百年的生活习俗的传承。舞蹈 《三月三》很快在通什及下辖的乡村演出,所到之处掌声雷动好评如潮……乡里的干部半开玩笑地对陈翘和歌舞团的同志说:‘一场演出让我们多少工作都白做了’。”③管琼:《陈翘传》,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由远古的 “祠高禖”写到近世的 “三月三”,意在指出我们当下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统,的确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但显然,远古之时的 “令会男女” “奔者不禁”有其历史的 “现实性” (比如大家族中难以有独处的机会;比如狭小的社交圈不利于 “优生”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移风易俗是必然的,推陈出新也是必然的——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更应当要思考我们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