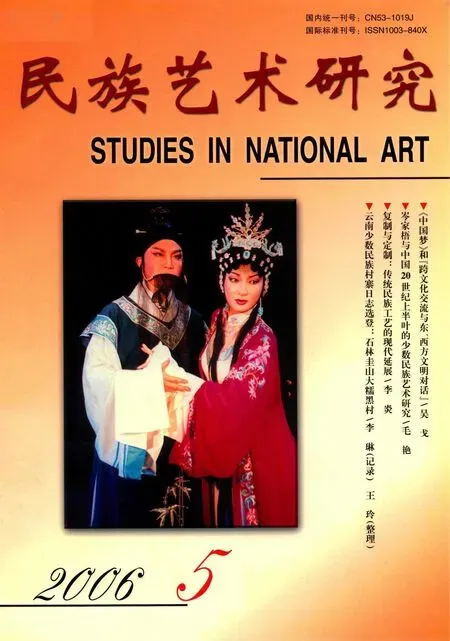哲学与艺术之间
——塑形于理性和感性之上的熊秉明
王洪伟
熊秉明 (1922—2002),祖籍云南弥勒县息宰村,生于南京。他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1943年抗战期间曾在滇南边境的军队中担任翻译,1944年从西南联大毕业。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 (1946),国民政府在全国九大城市进行统考,共录取了三百名公费留学欧美的学生。赴法留学的学生大约有40名左右,其中有学数学的吴文俊、学哲学的顾寿观和熊秉明、学绘画的吴冠中、学文学的王道乾等人。在这些留学生中,熊秉明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父亲熊庆来也曾留学欧洲学习数学专业,是中国数学界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更为特别的是,他最初选择的留学专业是哲学,而且是攻读博士学位的。但在留法的第二年 (1948),他出于对罗丹 (Rodin)和雕塑艺术的挚爱,决心放弃哲学转学雕塑,随后从巴黎大学转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熊秉明通过自己长期的实践与思考,不仅在雕塑的形式中发现了民族,在技艺的锤炼中触摸到了生活内涵的真实性,并基于自己的特殊经历与创作感悟,从哲学层面审视和反思了 “存在”的意义:即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在雕刻上表现了对“存在”的认识,无论雕塑的是神,是英雄,是女体,都反映这一个时代,这一个民族对“存在”所抱的理想。
一
熊秉明的很多思维底色都来自父亲熊庆来,尤其 “承继”了其父对理性的信仰和对感性的追求两种思维。熊庆来 (1893—1969)15岁时考入昆明英法文专修科,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19岁留学欧洲,先在比利时学习矿业,主要是想将来回到矿产丰富的家乡云南兴建矿业,实现科技实业救国的理想。欧洲战争爆发后,他经荷兰、英国转赴法国巴黎转学数学专业。经过八年艰苦的留学,熊庆来毅然回到了祖国,是近代中国第一代留法归来的科学家。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创办数学系,1936年又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西方不仅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深深地被西方科学成就背后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所感染,再加上其年少时在乡村私塾里学习的东方传统文化,使得他始终怀有对科学知识与乡土气息两种不同层面文化的爱。正如熊秉明所说,在父亲的平实诚笃中有深厚执着的爱:一是对科学真理,一是对祖国与乡土。而这两种高尚的品质,也在父亲日常所讲述的一些早年经历中流露出来,深深地影响着熊秉明。熊庆来有着良好的艺术素养平日诵诗赏菊,挥毫舞墨,最喜陶渊明之静洁与孤傲,与齐白石、徐悲鸿和胡小石等一些当时著名的书画家也相交甚好。他的书法字体开阔平稳, “没有外在规矩的拘束,也没有内在情绪的紧张。点画丰润,顿挫舒缓,给人以宽和端厚的感觉,一如他的性格”①熊秉明:《父亲之风》,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父亲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使熊秉明早在少年时期就能接触很多的中国古典文化艺术。作为著名数学家的儿子,熊秉明对其父的影响做过这样的描述:“我没有学数学,走了文艺哲学的道路。但我能感觉到父亲的数学是 ‘美’的。他常说 ‘优美的推导’‘洗练的数学语言’。而且也是 ‘善’的。我以为,在父亲那里,潜在着这样的道德力,但是我不愿称为 ‘道德力’。它绝非教条,它是尚未形成体系的信念,是一种存在的鲜活跳动的液体状态,生命的水。我以为父亲的道德力是这样一种浑噩的、基本的、来自历史长流的、难于命名的 ‘风’。在那里,理性和信仰的冲突,传统与革命的对立,中西文化的矛盾,玄学与反玄学的论战,生命的真实在这一切之上,或者之下,平实而诚笃,刚健而从容,谦逊而磅礴地进行。”②熊秉明:《父亲之风》,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熊秉明曾分别雕塑过 《父亲》 (1953)和 《母亲》(1979)两尊头像。母亲的头像亲切感人,素朴单纯,充满母性的慈爱;而父亲的头像,完美地传达出他所形容的那种平实而诚笃,刚健而从容,谦逊而磅礴的 “理”与 “情”交合的气质。
初到巴黎,熊秉明与一些同学住在大学城的比利时馆。当时,巴黎的艺术生活非常活跃,街头张贴的大多展览会、音乐会、戏剧、歌剧广告让中国留学生眼花缭乱,尤其是学音乐的同学整日忙得团团转。那个时期,大部分中国留法学生都有一股 “法国化”的外在追求,有人还经常引用蓝波的诗句 “绝对必须属于现代”来标榜自己。在巴黎留学半年之后,大约是1948年4月份左右,原本学哲学的熊秉明却突然有了改学雕塑的想法。这一方面是出于他对法国现代雕塑家罗丹的喜爱;另一方面,与生俱来的理性与感性两种思维的内在冲撞,使他内心产生了必须在“哲学和艺术之间选一个”的焦灼与困惑。对于自己最初接触罗丹的机缘,熊秉明在初到法国后撰写的 《里克尔的 〈罗丹〉》一文中回忆说:“1943年被征调做翻译官,一直在滇南边境上。军中生活相当枯索,周遭只见丛山峡谷,掩覆着密密厚厚的原始森林,觉得离文化遥远极了。有一天丕焯从昆明给我寄来了这本书:梁宗岱译的里克尔的 《罗丹》。那兴奋喜悦真是难以形容。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读过里克尔的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冯至译,受到很大的启发,好像忽然睁开了新的眼睛来看世界。这回见到里克尔的名字,又见到罗丹的名字,还没有翻开,便已经十分激动了,像触了电似的。书很小很薄,纸是当年物资缺乏下所用的一种粗糙而发黄的土纸,印刷很差,字迹模糊不清,有时简直得猜着读,但是文字与内容使人猛然记起还有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还有一个可以期待、可以向往的天地存在。这之后,辗转调动于军部、师部、团部工作的时候,一直珍藏在箱箧里,近乎一个护符,好像有了它在,我的生命也就有了安全。”③熊秉明,里克尔:《罗丹》,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通过里克尔对罗丹的描绘,熊秉明不仅初步了解了这位伟大西方雕塑家的内心情感,还懵懂地意识到雕塑的民族性格和内在气质。遗憾的是里克尔的 《罗丹》一书在去法国的途中已经遗失了,但熊秉明对这本印的 “寒伧可怜”,曾在战争时期给予他莫大安慰的小书,却久久不能忘怀。
熊秉明到达巴黎后不久,就一头扑进了罗丹的雕塑中,经常徘徊于他的各种展览和作品之间,并撰写了多篇解析罗丹和其雕塑作品的文章。如 《艾玛神父》 (1948年1月10日)、《加莱市 (义)民》(1948年3月7日)、《宗教和艺术》 (1948年4月21日)、《法兰西大教堂》(1948年5月4日)、《罗丹的美学》(1948年5月20日)、《青铜时代》(1948年10月19日)、《罗丹的性格》(1951年2月4日),等等 (这些文章后来被汇集成《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一书,曾获中国时报散文奖)。此时,熊秉明并没有简单地满足于对罗丹艺术的单纯喜爱,身体内部两种气质的纠缠与冲撞使他对所学专业开始产生了动摇。1948年4月21日,熊秉明在 《宗教和艺术》一文中借助罗丹和梵高年轻时在宗教与艺术之间二选其一的困惑矛盾来暗示自己当时在专业选择方面所面临的窘境:“罗丹在姐姐逝世之后,伤痛绝望,进入教会,想做一个修士。如果没有艾玛神父的力劝,他会不会就真的把一生献给了宗教信仰呢?在艾玛神父劝说时,他必有过苦痛的犹豫、彷徨吧。这时他二十二岁,正当生命道路的开始,他该怎样选择呢?在做决定之前,有过多少失眠发烧的夜?1883年,梵高在给弟弟的信里说他怎样被这个问题熬煎:‘我是画家?我不是画家?’这时他已三十岁。……哲学与艺术之间该怎样选择呢?我得在哲学和艺术之间选一个。我们今天似乎每个人只能做一桩事,做一项职业。学哲学,或者学艺术……游离子、两栖类,是不被容忍的。但是人的兴趣和工作能分得那么清楚么?”①熊秉明:《宗教和艺术》,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熊秉明虽然能从自己的文化传统联想到诗、书、画与哲学的不可分割性,但是他始终认为中国人尤其普通百姓,往往很难做到将宗教或者他们所理解的迷信活动,与艺术创作和审美情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时期,哲学理性与艺术感性两种思维之间的复杂关联交织在熊秉明的生活与学习中。他曾极力从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对理性与感情并存却又独立的论证—— “我们内部有两个人,一个是理性的。他要清除一切成见旧说,通过观察、实验和严格的推理来了解自然。一个是情感的。他为亲人的死亡而哭泣,他无法证明他能够或者不能够和逝者再见。然而他相信而且期盼。目前人类的知识尚太粗浅,理性和感情是截然不同的领域,两者相牵涉是不幸的”②熊秉明:《父亲之风》,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来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事实上,罗丹身上复杂的性格特点和艺术气质对熊秉明转换专业起到过莫大心理支持。在 《罗丹的性格》一文中,熊秉明对这位伟大的雕塑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首先,他认为罗丹的性格属于荣格划分的四类性格中的 “感性类”:罗丹细小而炯炯若炬的眼睛,尖而高的鼻子,都像敏锐的雷达那样的仪器,不断探测外界,细辨外物的特征,它们的交易和轨迹。他有空间组成和形体结构的敏感,他还有嗅觉的、触觉的敏感。如果他有哲学,那哲学直接根于感觉对象。他的嗅觉、触觉、视觉时时在发出信号,给他予生的欢喜的感动,让他在赞美中生活而且创造。这频频传来的新鲜强烈的信号不容他作耐心的推理,构筑抽象思维系统;他也不会感觉到推理与系统建立的必要,因为最能说服他的不是推理的巧妙严密,而是感官获取的资料的真实③熊秉明:《罗丹的性格》,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但熊秉明又进一步认为,感性元素不是罗丹性格的全部,因为他比一般的雕刻家更加深刻,不局限于感性层次,有着一种对哲学理性的内在需求。它来自一种虔诚热烈的宗教情操,对大自然、对人,保持着一种广袤而严肃的神秘感和崇敬心。这双重的性格,使得罗丹具有了艺术与哲学的混合气质,在其雕塑中,他既能表现人类灵魂的激荡与狂情,又能透彻骨髓地展示一切事物底层最本质的性格。而这种混合的性格气质,恰恰也是熊秉明本身所具有却要通过一种合适的手段去调和与释放的。一直困扰于理性与情感的有效沟通问题的熊秉明,逐渐从罗丹那里获得了一种榜样性的验证。通过罗丹的一些艺术随笔,熊秉明对理性与感情关系的认识也愈加深刻。他认为,西方雕塑家以严密的逻辑思想分析着生命 “存在”的本质,而他们在强调人的理性或单纯特征的时候,并没有取消其雕刻形象中鲜活的生命力和存在之本真。艺术家在雕塑中倾心于恬静的节奏,不自觉地缓和了的躯体起伏,使生命的动量表面看起来是如此的安稳和谐。这种外观却往往让中国人在理解西方人体雕塑方面存在很多误区。人们总愿意将西方哲学作为抽象的沉思高悬起来,隔离了其雕塑中的感官欲望,拒绝了其中蕴藏的人性与激情。但在罗丹的雕塑面前,人们总会以为“这是以吻和爱抚塑造出来的……触摸这石躯,人几乎要觉出温暖来的”。
熊秉明认为以往过于关注罗丹雕塑中最富哲学的内容、人生的意义,却忽视了对他在创作中抚摸生命之喜悦的发现,而这也启发了他对理性与情感关系问题的深思。面对罗丹的 《夏娃》,熊秉明每次都能获得新的震撼。因为,维纳斯和夏娃是西方艺术中两位永恒的女体,前者来自理性的希腊思想,但又代表着 “享世”,纯美而充满诱惑;后者来自基督教传统,是宗教中复杂的崇高感和恐惧感共同塑造出来的形象。夏娃在世间是被贬责的,肉体是要受难的。 《夏娃》那 “绝不优美,或者已经老丑,背部大块的肌肉蜿蜒如蟒蛇,如老树根”是典型的、带有生命力的女体和母体。她像一位母亲,更像一个有孕的妻子:“我愿在这个世间和她一同生活并且受苦……这件雕塑是一未完成的状态,许多地方都留着手指和泥块的痕迹,这粗糙的痕迹恰好更突出了多艰辛、多苦难的世间感来”①熊秉明:《维纳斯和夏娃》,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又如他评价罗丹的 《艾玛神父》——他干而瘦,硬而纯,平凡而坚定,严肃而仁慈,在世间属于 “盐”那样角色的人物。这种宗教感很深的性格,似乎专门赋予了那些走艰难坎坷道路而到人间来的人。他还从罗丹的 《法兰西大教堂》中体悟到罗丹对艺术与生活密切关系的理解——在大教堂里,所有的女人都是抒情诗神,她们的一举一动都趋向美,建筑把壮美的光辉投给她们,像感激的献品。
熊秉明充满强烈感性色彩地对罗丹雕塑中蕴藏的生命 “存在”与 “情感”的解读与赞颂,也是其内心中理性与激情的交流倾诉。渐渐地,他通过自己的思考与实践得出了一个答案:即一个艺术家通常情况下不能以理性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作品,但没有一个人不愿知道自己作品的意义,至少想从别人的客观批评中获得一点启示。从这种角度去说,一个人做到既是哲学家又是艺术家是一件很自然的要求,哲学分析与艺术感悟并不决然地相互冲突。基于以上深刻认识,熊秉明最终放弃了哲学专业转学雕塑艺术。
二
熊秉明转学雕塑的第一位老师,是擅长头像的法国雕塑家纪蒙 (Gimond)。纪蒙不仅在雕刻上有着很多独到见解,而且是一位藏品宏富、很有见识的收藏家,其主要收藏品是希腊、中国、埃及和黑人的 “首像”。熊秉明在纪蒙的工作室里断续地学习了两年的时间。纪蒙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雕塑手法和观念上,纪蒙对学生的要求是要表现出形体的 “面”,注意形体之间的分合关系,再由面来组织空间结构。他曾告诫学生们,一件失败的雕塑表现出的“软”“松弛”和 “站不起来”等现象,都是因为创作者没有处理好 “面”的问题。雕塑要想充分表现其存在的生命力,必须依赖明确的立体感,而立体感是由严密的 “面”所构成的,雕塑家一定要看到面与面的结构和深层的间架,这是雕塑的本质。纪蒙的这种雕塑观对熊秉明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道:“我决定进入纪蒙雕塑教室。我完全折服于他对古今雕刻评鉴的眼力,我想,在这样锐利、严格、高明的眼光下受锻炼是幸运的。纪蒙指导学生观察模特儿的方法和一般学院派很不一样,从出发点便有了分歧了。他从不要求学生摹仿肌肉、骨骼,他绝不谈解剖。他教学生把模特儿看作一个造型结构:一个有节奏、有均衡,组织精密,受光与影,占三度空间的造型体——这是纯粹雕塑家的要求。按这个原则做去,做写实的风格也好,做理想主义的风格也好,做非洲黑人面具也好,做阿波罗也好,做佛陀也好,都可以完成坚实卓立的作品。所以他的教授法极其严格,计较于毫厘,却又有很大的包容性。”①熊秉明:《雕刻的本质》,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在审美观念上,纪蒙丰富的藏品,也开拓了熊秉明的视野。在转学雕塑的第二年,熊秉明就带着自己深刻的哲学沉思和实践经验提出,观者如能排除本土文化在艺术鉴赏上长期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便渐能进入一个新的审美系统,并发现另一片艺术天地。进而,熊秉明对西方雕塑、黑人雕塑、东方佛像以及民族审美特征,做出了一系列专门的比较与思考。首先,在 《希腊雕刻》 (1949年10月21日)一文中,熊秉明对蔡元培提倡的 “以美育代宗教”的说法作了反思。他认为,蔡氏所说的艺术如何可以净化心灵,希腊艺术有纯净无邪的美的观点,是 “用了中国人的艺术观来解释西方人的艺术了”。因为,中国人自己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是希冀远离人间烟火,灭除一切情欲的。但是,若真的如司空图所说 “幽人空山”那样,人不但是静止的物质化了的山,而且是空寂的象征性的山。那么,无论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必须是蝉蜕了肉身的抽象的存在,这在东方的现实之中是难以成立的。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以为一经这种艺术的 “净化”——“女性的身体就像观音菩萨,像林泉丘壑一样,一尘不染,透明了,毫无危险地消毒了,却也是误会的”②熊秉明:《希腊雕刻》,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熊秉明不否认艺术有净化生命的作用,蔡元培所说的 “净化”,在美学上也是存在的,但 “净化”之后的生命,并不能或不必变成无生命,情欲也不会化为无欲。所以,希腊裸体雕塑绝对不是蔡氏所认为的 “有纯净无邪的美”。接着,熊秉明对希腊人体雕塑做了深入的解读:希腊的神虽然是完美的,但是在完美中仍然有肉感、有爱,并且有嫉妒、有仇恨、有争斗……他们的完美是肉身的健壮,强有力。古希腊人崇拜理想,蔑视肉体,以为肉体是庸俗卑下的,他们不肯把物质真实的千百种细节重现在作品中。希腊人以他们严密的逻辑思想,本能地强调本质的东西。他们强调人类的典型特征,可是决不取消生命的细节,并且在一切机会下狂热地表明对肉体的赞颂。说他们鄙视肉体简直是荒诞。希腊雕像那里,有生命在跳动,烘暖脉动的肌肉③熊秉明:《希腊雕刻》,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熊秉明指出,如果蔡元培读过舞蹈家邓肯自传中描述的她与罗丹相遇的那一段文字的话,必定对西方雕塑家在哲理与感性之间的调适会有新的认识。
那么,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欣赏西方裸体雕塑呢?熊秉明提供了自己的方法,欣赏者一定要在人的肉体上,“看见明丽灿烂,看见广阔无穷,也看见苦涩惨淡、苍茫沉郁,看见生也看见死,读出肉体的历史与神话,照见生命的底蕴和意义”④熊秉明:《肉体》,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这种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本质,是西方雕刻灵感的源泉,更是西方雕塑家能够将理性与感性、宗教与艺术统一在一起的基础。基于此,他认为罗丹的“夏娃”,不但不是处女,而且也不是少妇,身体不再丰腴,肌肉组织开始松弛,皮层组织老化,然而生命依旧在倔强斗争中展示着悲壮的场面。熊秉明还专门针对西方艺术中的 “女体”形象做过辨析,西方人潜意识里,甚至在意识里,对于女人,与其说是看作“女人”,不如说看作 “雌体”“兽体”。把这种感觉表现得最大胆最透彻的莫过于鲁本斯了。像那些赤裸的肥男子追逐搂抱赤裸的肥女子的大画,古中国人看到,必会骇怪并且愤怒:这简直是禽兽。罗丹也表现过这样的兽体,不过是美丽的兽。有一座 《半马半女像》,女人在挣扎,有人认为她要从马的躯体中摆脱开去。如此美的兽体,跳跃在林间、湖岸、海滨、丰收的葡萄园里,我们怎能不以另一只兽的伶俐、欢欣去和她游戏呢?①熊秉明:《兽体》,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5页。西方艺术家心怀强烈的宗教感,这使他们对生命、对艺术、对女体都看得非常严肃。艺术与生命、灵感与爱欲,都是不可分割的。艺术家们固然描写人与兽在一个个体中的冲突与斗争,但同时也正说明人与兽在同一个体中的并存—— “少女的躯体连接着幼驹的躯体,同属一片白洁滋润的生命,同在阳光和雨雾中滋长”。而中国人却很容易嘲笑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嘲笑他们给神赋予了人的形象,嘲笑他们的天使长着翅膀,神长着大胡子,女体的情欲暗示。其实本质上,西方人将人提高到神的层面与中国人赋予云烟和林泉以崇高神秘意义的做法,是一致的。由此,他也认为朱光潜提出的审美 “距离”之说,过于夸大了艺术与生活的间距,这也是中国人对艺术鉴赏的一种隔岸观火式的理解。
其次,熊秉明对黑人艺术的接触与理解,也是从欣赏纪蒙的收藏品开始的。1947年初到法国,他最早在人类博物馆里看到黑人的面具和木雕时,觉得莫名其妙。但这倒也并未给他带来特别的不安感受,仅仅认为这些是原始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在纪蒙的工作室里,熊秉明再次看到打磨得精细的黑人面具,安置在中国佛像和阿波罗头像中间,也同样散发着人性的光辉。由此,他逐渐放弃了自己既有的审美习惯,“开始换一种眼光来看黑人艺术”,并努力寻求另一套美学语言来欣赏它们。这也是他后来撰写《黑人艺术和我们》一文的诱因之一。但开始时,他也曾陷入过审美语言描述的困境:“在我开始能够接近黑人艺术的同时,我也就发现黑人和中国艺术距离之远。数千年来,中国的绘画与雕刻所走的道路是另一个方向,在欣赏上,塑造了另一套美学语言,用来描述黑人艺术便不免要觉得唇舌笨拙了。‘气韵生动’‘传神阿睹’‘栩栩如生’……都用不上;通常描写书法、绘画用的词汇像雄浑、苍劲、典丽、淡远……描写佛像所用的崇伟、庄严、慈悲、和祥之类也不相干。”②熊秉明:《黑人艺术和我们》,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87页。
事实上,不仅传统的审美范畴失效了,甚至连最具概括性和包容性的 “美”这个概念,也很难将黑人艺术容纳进来,甚至是相抵触的。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熊秉明认为,黑人艺术既非冷静观察,也非悠然关照,而是人与自然在理与情之外的热烈共舞。黑人艺术中的面具是舞蹈时使用的道具,他们的舞蹈是一种 “腾跳”。这是其躯体生存的基本律动,所配合的音乐是敲击,所配合的绘画是纹饰,所配合的雕刻是面具——这面具,并非写实的标本,它是兽的精灵的化身,这化身是一个象征,一个徽号。所有这些艺术都是以简单激烈的节奏为主要表现手段,而最原始的艺术就产生于这里。黑人的 “腾跳”是人与野兽的争斗和共舞,这里有紧张、凶残和酣畅、释放。与西方艺术的理性相比,黑人艺术是建筑在人性的 “本能”和 “冲动”之上的,他们生活在感性中,以嗅觉、味觉、节奏、颜色和形象直接去感受外物、接纳自然。他们活在对象中,对象也活在他们之中。黑人艺术与中国人的静观、守敬、禅定,恰好代表外向的粗犷和内向的含蓄两个极端。但黑人在跳跃中得到的酣畅战栗,与中国人在看云听水时得到的恬适虚静,同样是天人合一的神秘经验,都是艺术,也是哲学。
熊秉明在学习和阅读中发现,法国艺术史家弗尔 (E.Faure)提出的黑人艺术出于“本能”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即我们不要在黑人艺术中寻求别的什么,只应寻找一种尚未理性化,只遵从初级的节奏和对称的情操。本能在推动年轻的种族,使他们在手指之间所制造出来的生动的形体,具有含混的建筑感,带着稚拙而粗糙的对称性③熊秉明:《兽体》,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在此基础上,熊秉明归纳了三点:黑人面具既是宗教——它试着窥测这个世界的秘密和神明,但它没有凝聚出 “神”的抽象意念,也没有把此意念塑造为光辉的形象;也是哲学——面具对存在提出疑问,也给予了回答。它的形象是问题和答案揉捏在一起的大神秘;更能称得起是艺术——黑人工匠在操作工具时,并不自以为然在制作一件艺术品,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依照传统的程式打造一个神秘的面具。正是有着这样综合的特点,黑人面具的感染力、震撼力是巫术的,又是艺术的;精彩的面具必然是惹眼的,怪异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 “美”!他更进一步从 “物我交融”的角度认为,中国艺术乃是隐几而坐的“游目骋怀”,一种俯仰于 “两间”的移情关照;而黑人艺术是以自己的躯体全部投入外物之中,进入面目,灵与肉无间,与外物的合一而共舞。人的超越性、精神性就在肉体的呼喊中、震撼中、腾跳中酣畅淋漓地呈现出来!
第三,留法之后,熊秉明才逐渐意识到中国佛像雕塑的艺术价值。此前,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佛像雕塑会有什么艺术价值。“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二年级时转入哲学系,上希腊哲学史的那一年,和一个朋友一同沉醉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一面也沉醉于希腊的神殿和神像中。那许多阿波罗和维纳斯以矫健完美的体魄表现出猛毅的意志与灵敏的智慧,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撼。那才是雕刻。我们以为,西山华亭寺的佛像也算雕刻吗?我们怀疑?”①熊秉明:《佛像和我们》,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熊秉明认为这种肤浅认识的根源,一方面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这些雕刻艺术价值的长期禁锢与漠视;另一方面是 “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过分批判。而崇尚科学精神的父亲对古代佛像雕塑艺术价值的排斥,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直到留学初期,熊秉明对鲁迅所说的 “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地”的批判之语,也仍默记于心。
在晚年的 《佛像和我们》 (1988年11月)一文中,熊秉明谈及了留学期间自己是如何通过纪蒙和西方的汉学家发现中国古代佛像的艺术价值的。他认为留学之前一直觉得中国传统艺术仅仅限于书画之类,基本上是不包括雕塑的。古人的塑像,在中国人眼里似乎只是宗教膜拜或迷信的对象,求福祈愿的泥偶。它们只代表灵验与不灵验的问题,从未听说过关于造像本身艺术价值的说法。母亲所供奉的一座观音白瓷像,对于年幼的他而言,也只不过是家里的一件 “摆设”,当时并没有觉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中学时代,他虽曾游历过一些古寺名刹,但对于里面的佛像雕刻,“从未想到当做艺术作品去欣赏”。熊秉明说自己中学时期的艺术知识,主要来源是丰子恺的 《西方绘画史》、朱光潜的《谈美》和 《文艺心理学》、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 《名人传》、鲁迅翻译的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和厨川白村的 《出了象牙之塔》等书。这些书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是为求知欲很强的青年们提供了帮助,拓展了他们的视野。他在国内时也曾阅读过日本学者大村西崖 《中国美术史》一书,当时觉得书中虽然谈及中国雕塑的艺术价值,但内容却空洞异常,实在不能给人予真正的启示。
初到欧洲,熊秉明在一些古董商那里,也偶见到一些佛像或佛头,它们在当时却并没有引起他太大的兴趣,只认为那是中国恶劣奸商和西方冒险家串通起来盗运的古物,是为了满足西方富豪的好奇心和占有欲,“至于这些锈铜残石的真正价值实在是很可怀疑的”。然而,到了1949年,他的态度转变的既是如此的突然,却又流露着一股自然而然的热情。他回忆说:“(这种观点)到1949年才突然改变。这一年的一月三十一日我和同学随巴黎大学美学教授巴叶先生 (Bayer)去访问雕刻家纪蒙 (Gimond)。到了纪蒙的工作室,才知道他不但是雕刻家,而且是一个大鉴赏家和狂热的收藏家。玻璃橱窗里、木架上陈列着大大小小的埃及、希腊、巴比伦、欧洲中世纪……的石雕头像,也有北魏、隋唐的佛头。那是我不能忘却的一次访问,因为我受到了猛烈的一记棒喝。把这些古代神像从寺庙里、石窟里窃取出来,必是一种亵渎;又把不同宗教的诸神陈列在一起,大概是又一重亵渎。但是我们把它们放入艺术的殿堂,放在马尔荷所谓的 ‘想象的艺术馆’中,我们以一种眼光去凝视、去歌颂,我们得到另一种大觉大悟,我们懂得了什么是雕刻,什么是雕刻的极峰。”①熊秉明:《佛像和我们》,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可以说,在纪蒙的工作室里,熊秉明第一次用艺术的眼光接触中国佛像,第一次在那些巨制中辨认出精湛的技艺和高度的精神性,中国佛像弥散着另一种意趣的安详与智慧,中国古代的工匠也是民间的哲人。此时,熊秉明开始深深为自己是一个雕刻盲而羞愧自责。
除了纪蒙的影响外,熊秉明认为瑞典汉学家喜龙仁 (Siren)撰写的 《五世纪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 (1926)一书,帮助他进一步深入认识了佛像的艺术价值。喜龙仁认为中国佛像有时表现得坚定自信,有时安详幸福,有时流露愉悦、有时在眸间唇角带着微笑,有时好像浸入不可测度的沉思中,而无论外部表情如何,人们都能感觉到静穆和内在的和谐。喜龙仁将中国古代艺术推崇得如此之高,使熊秉明这些喊着 “到西方去,到巴黎去,到有雕刻和绘画的地方去”②熊秉明:《佛像和我们》,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的中国留学生们,不自禁地开始向故园回望,重新拾起曾经被遗弃的传统。熊秉明认为,在创作上要达到古代佛像的境界不容易,而欣赏和品鉴一尊佛像,对于那些抱有偏见的中国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千年来,因为文人艺术观的影响,雕塑被视为下层工匠的技艺,在中国关心佛教雕塑的年轻人是极少的。虽然有喜龙仁这样的西方艺术史家提示我们这些雕塑的艺术价值,但目前我们对于佛像的欣赏,有着比喜氏更加复杂的心情,其中即包含对自己古代传统新的正视、新的认同和新的反思。而在久别回归的激动中,我们还应该排除三种偏见:
一要排除宗教成见。对于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人们很难想象他可以从虔诚的礼拜情绪中抽身出来去欣赏佛像的艺术价值。而对一个反宗教的人来说,总是认为宗教是迷惑人民的 “鸦片”,反对将佛像转化为欣赏的对象。所以,“要欣赏佛像,我们必须忘掉与宗教牵连的许多偏见与联想,要把佛像从宗教的庙堂里窃取出来,放到艺术的庙堂里去。”③熊秉明:《佛像和我们》,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二要排出写实主义的艺术成见。熊秉明分析了中国人从最初看不惯油画的光影效果到矫枉过正地夸赞写实风格,批评中国绘画不合科学,再到现代主义传入,中国传统绘画及其意境又受到重新肯定的大致过程。然而,他深刻地感受到,无论与传统绘画还是传统京剧比较,我们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关于佛像的审美传统与更为丰富的描述语汇。对于古代雕塑的欣赏,也仅仅限于 “栩栩如生” “活泼生动” “呼之欲出”和 “有血有肉”等几个描绘词语。显然,这是以像不像真人的写实标准来衡量佛像雕塑了。若要表现出高贵的佛性,必须抛弃写实的手法与观念。
三要回到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因为 “佛”是雕塑的基础性内容,是最广义的神的观念的具体化。所以,如果不能了解“佛”的观念在人类心理上的意义,不能领会超越生死烦恼的一种终极追求,那么我们还是无法真正欣赏佛像的艺术价值。“佛像要在人的形象中扫除其人间性,而表现不生不灭,圆满自足的佛性。这是主体的自我肯定,自我肯定的纯粹形式。”④熊秉明:《佛像和我们》,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佛”的形象,是从人的形象转化来的,通过岩石与青铜为媒介使佛性弥漫于其中,使灵性侵入其中,从而使物质获得一个使命——作为佛像的金石在时间中暗示永恒,在空间中暗示 “真在”!那么,古代的那些无名的工匠们,又是本着怎样的一种虔诚之心来完成佛像的制作呢?他们或许怀着与西方雕塑家一样的宗教情绪,在佛像中见诸生命的存在。有了深入的理解之后,熊秉明也开始在自己的创作中追求着佛像的圆融境界:“我虽然不学塑佛像,但是佛像为我启示了雕刻的最高境界,同时启示了制作技艺的基本法则。我走着不同道路,但是最后必须把形体锤炼到佛像所具有的精粹、高明、凝聚、坚实。”⑤熊秉明:《佛像和我们》,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此外,喜龙仁的著作,还启发熊秉明对汉代石兽和梁代石狮这些墓葬雕塑,同样进行了新的审视。他认为,中国古代刻工在狮子形象的创造中,发挥了中华民族自己独特的想象力:“中国本没有狮,关于狮子的故事是通过西域传来,狮的形象当然也是辗转听来。但是正因为中国刻工没有见过实物,不受实物的牵绊,狮子成为与龙凤同类的神话角色,可以任他们的想象力去塑造。”①熊秉明:《梁代墓兽》(1951年3月16日),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梁代以前的狮子,是一匹咆哮迈行的怪兽,而梁代以后的狮子是蹲在宫阙门前的凶恶警卫,只有梁代的狮子是一个沉重庞然的大物,“长着短短的硬翅,四爪稳立在地,张开大口向天,挺圆了胸,勾卷了尾,凌然、巍然,浑囵浩瀚,变成一个迷离的玄学的符号”②熊秉明:《梁代墓兽》(1951年3月16日),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这样的思考,一方面引发熊秉明对中西艺术关系的反思,西方现代艺术想跳出写实的束缚,而中国艺术又想引进写实的手段,真正的文化一定是现实的、人间的。另一方面,熊秉明对于自己身处的艺术的国际主义语境的未来前景,也陷入了沉思,他似乎悟出了一些道理:“在埃及希腊雕刻之前,在罗丹、布尔代勒之前,我们不能不感动;但是见了汉代的石牛石马、北魏的佛、南朝的墓狮,我觉得灵魂受到另一种激荡,我的根究竟还在中国,那是我的故乡”③熊秉明:《梁代墓兽》(1951年3月16日),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此时,熊秉明对雕塑作品中所融合的个人意志与民族特征,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认为,雕塑首先是一个“存在”,或者说它争取一种存在,以它本身的三度空间,占据一个地方,而又不仅仅占据一个地方,它要争取自己存在的恒久性和生命的价值。所以,他肯定雕塑是艺术家表现个人或者群体生存意志的最好凭借。有史以来的雕塑,无不是追求生命 (存在)的强度和持久。这与哲学家们通过对知识和思维方法的探究而归宿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是非常一致的。
在转学雕塑的第三个年头,熊秉明的思想就显得更加成熟了,不仅有了自己深刻的艺术理念,同时羁旅海外的游子也开始怀乡了,在创作中追寻自己家乡 “马锅头”的痕迹了。这个时期熊秉明创作了不少头像,在做这些雕塑的时候,他时刻感觉到民族的面型特征深刻地支配着一个雕刻家手的触觉,再伟大的雕塑家都无法全面而深入地描绘其他民族的特征。如罗丹所做的日本舞女头像,虽然有着东方面型的特点,但没有真正把握住其内涵;布尔代勒所做的中国人的头像,也显示出了一些东方人的特征,但细观之下依旧是西方雕塑家的手笔,不吻合东方人面部的起伏节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再精湛的技艺也渗透不了其他民族的内在气质和文化特征,技艺离不开民族的生活。这恰好印证了罗丹所说的:“对于艺术家来说,一切都是美的,因为对于一切存在,一切事物,他的深刻的眼光都能把握 ‘特征’,也就是把握从形象透露出来的内在的真理”。熊秉明对民族 “特征”有着亲切的自我感知:“我塑中国人的时候,手指沿着额眼鼻颊唇的探索,好像抚摸着祖国的丘壑平原,地形是熟悉的,似乎不会迷失。塑一个西方人,我总游移,高一步、低一步,走不稳。尤其是巴黎地道里的人,那脆弱、困乏、虚伪、惶惑、匆忙,实在无法给我塑造的意欲”④熊秉明:《谈雕刻》,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在雕塑创作中,熊秉明逐渐把注意力集中于对象的文化 “特征”与 “气质”上,集中于自我民族之所以独特的标志上。他认为自己雕塑头像的理想是呈现家乡的 “马锅头”,这种头型类似于布尔代勒雕塑的东方化的阿波罗:“看到他的阿波罗,使我预感到塑造中国人面貌时的快乐,那面型我熟悉极了,那上面的起伏,是我从小徜徉游乐其间的山丘平野,我简直可以闭着眼睛在那里奔驰跳蹦,而不至于跌仆”,⑤熊秉明:《罗丹和布尔代勒》,载 《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更不必担心 “未得国能,又失其故步”了。熊秉明就是从家乡的 “马锅头”这种特殊的形象中找到了个性的美,又凭借着它们追溯到民族性格与内在气质的。
结 语
经过数十年的艰辛探索,雕塑对于熊秉明来说已经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方面,他在思维上始终追求着哲学理性与艺术感性之间的交融,这使他逐渐在雕刻技艺和形象的创造中领悟了如何以艺术的方式完善哲学思维对 “存在”意义的探究。虽然,他年轻时在哲学理性与艺术感性的思维牵制中矛盾困惑了很久,但通过罗丹 “从形象透露出来的内在真理”的启示,加上自己对形象表现与意义的追问思考,最终真正理解了两者之间的现实关系。其所说哲学追求一个存在的意义,而造型艺术要把这意义塑造成一个“存在”形象的话,就能极好地证明他真正懂得了一个充满哲思的雕塑家身上应该具备怎样的一种 “混合气质”;另一方面,在去国怀乡滞留海外的孤独生活中,熊秉明不断探问着自己艺术的创作意义与价值归宿,始终坚守着 “学成”之后一定要真诚地塑造中国人面貌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