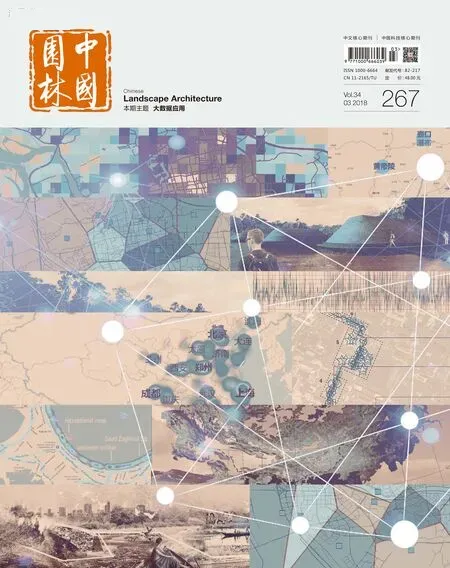春秋到两宋时期中国古代书院园林变迁营略
王 鹏
1 萌芽期——春秋到魏晋:私学兴与孔子自然山水观
1.1 私学之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设私学打破了极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的现象,把文化知识向更多人尤其是下层阶级开放,自此开启了中国古代私人讲学的传统,“竹帛下庶人”的私学是书院的早期雏形。所谓“菁莪造土,棫朴作人”,孔子深谙环境对于人的教育和影响作用,夫子教学的场地多选择远离市井嚣尘的数山廻抱,林木参差,有岩足涉,有川足泳的自然之地,如孔子曾经在春秋时鲁地的洙水和泗水之间开张业艺,讲道授业,后来著名的岳麓书院曾以“洙泗”自比,有“潇湘洙泗”的美誉。孔子曾明确指出理想的隐居求道之地是自然山水环境,“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1]”曾点从暮春美景中体会到了天理流行,孔子与曾点的志向相同,他真正向往的是那种能与环境共鸣的、天人合一的人居生境。可见,中国的古典哲学孕育于自然山水之中,思想家透过自然界的山容水色、草木禽兽的现象表层,发现了符合社会道德的精神美品质,从而产生审美的愉悦感,孔子的美学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思想,对于后世书院园林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
1.2 私学之禁与兴
秦代统一六国后,为了维护统治、控制思想,采用了极端之焚诗书、禁百家私学的政策,李斯认为“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立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抑制和冲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
汉初百废待兴,官学未兴,秦时被压抑的私学得以恢复发展,呈现再度兴盛的局面。汉代私学教育注重师承关系,教学方式以口传心授为主,讲学场所的公共性不强,建筑的讲学功能尚未明确,只是部分的承担着一定的讲学功能,主要情况分为2种:其一,学者讲学多在家中或者府邸里面设置绛帐授徒,如东汉时著名经学家马融(79—166)“为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善鼓琴好吹笛,…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2]。其二,“东汉以来,士大夫往往作精舍于郊外,所谓春夏读书,秋冬射猎者,即其所也”[3],即在自然环境优美处、创建精舍作为讲学读书之处。《国语》曰“明洁为精”“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4]。可见 “精舍”本为精神栖息之地,内心修习之空间。汉代精舍多为隐居教授之所,这些精舍的主人大多不愿做官,寻求的是避世隐居的生活,隐居授徒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精舍大多选择在远离阛阓红尘的山林泽畔之幽静地,如《后汉书·杨伦传》载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伦前后三征,皆以直谏不合。既归,闭门讲授,自绝人事”。
可见,精舍即是儒士读书、授业、清修、养生的居所,同时又是他们追求的清净玄远的精神圣地。精舍尚自然的选址和尚简易古拙的营建风格对于后世书院园林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追求精舍那种隐于尘世外的清淑之气,后世“书院”多有以“精舍”命名的做法,如朱熹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沧州精舍,陆九渊的象山精舍等,书院园林崇尚自然疏朴、野致的意态,建筑尚典雅、不施装饰,如以精舍命名的书院,一般就几间小屋,布局非常简单。另外,许多私人兴建的书院,建筑常常采用茅屋草堂的形式,如朱熹营建的晦庵云谷书院中就构有草堂,并且朱熹之号晦庵也得自于草堂的题额,再如岳麓书院门前南侧的风雩亭亦采用了草亭的形式,这种朴素的茅屋草堂不但与周边自然环境中的山楹、药圃、井泉、溪涧很好地融合,而且构造简易的草堂与自然充分融为一体。
1.3 私学之玄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春秋战国后又一军事混战的动荡时期,频繁的战乱使得短暂的政权无暇顾及教育,官学教育衰微,数量大大减少,官学为私学取代,私学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时兴时弱。这一时期佛老之学盛行,儒学微衰,儒、道、释、玄诸家争鸣,玄学的清谈之风与私人讲学相结合,使私学深受佛、玄的影响。从这时起,佛寺、道观、书院常常比邻而居,僧侣、道人和儒生常常一起谈论文章、交流思想,形成“儒以治世,佛以修心,道以养身”的“三教合一”的中国传统特色文化。佛道选择在山林名胜之处建立禅林精舍,从事坐禅和讲经,是由于依傍山林、环境清幽利于修行,佛寺的建筑选址、建筑组群布局、管理制度,如佛寺丛林的讲经说法、藏经和祭祀师祖的经验都对后世书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清华大学周维权先生《中国名山风景区》中曾指出书院“教育体制多借鉴佛教禅宗的丛林清规,建置地点也多仿效禅宗佛寺建在远离城市的风景秀丽之地,以利于生徒潜心学习”,书院作为古代重要的教育组织机构,他的营建受佛道的影响,历来也非常重视环境的选择。
2 生成期——隋唐五代:隐居求志 放旷自然
2.1 隋代山间授徒
隋代伴随私学制度化,书院教育制度得到确立,书院园林得以生成并发展。书院园林受到儒家山水观和佛道思想的影响,在选址上延续了魏晋隐逸之风,多选择在山林闲旷之地精心布置一两处草庐,作为修习儒学、讲业授徒之地。隋代教育家王通(584—617)弃官归乡后,曾在家乡的白牛溪畔聚徒讲学,先生将讲学处周边的山水儒学化,以“山”比作孔子教泽的尼邱,以“泉”比作孔子教泽的洙泗,“白牛溪里,岗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察俗刪诗,依经正史……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洙泗”[5]。其兄王绩(590—644)在《游北山赋》中记载了王通当年讲学的盛况“念昔日之良游,忆当时之君子,佩兰荫竹,诛茅席芷,树即环林,门成阙里,姚仲由之正色,薛庄周之言理,……北岗之上、东岩之前,讲堂犹在,碑书宛然,想闻道于中室,忆横经于下筵,坛场草树,院宇风烟”[5]。可见,王通的讲堂置于山水之间,周边景致瑰丽,讲学时弟子们佩戴兰竹香草,或是立于竹荫之下,或是坐于草席之上。课余闲暇时,先生将周边优美的自然山水作为第二课堂,弟子们“触石横肱,逢流洗耳。取乐经籍,忘怀忧喜,时挟策而驱羊,或投竿而钓鲤”[5],活动非常丰富。
2.2 唐代书斋园林
唐代一些书院成为士人隐居读书的地方,属于唐士人个人构屋读书的书斋和私塾性质的学馆,服务范围限于士人个人本身,成为私人肄业之所。如《四川通志》载“凤翔(南溪)书院在南溪县北半里,唐进士杨发读书处”,书院选址背负琴山,前处滨江,地势险阻,周边有杨发弹琴的琴台,杨发有诗描写南溪书院园林的景致曰“茅屋住来久,山深不置门。草生垂井口,花发接篱根。入院捋雏鸟,攀萝抱子猿。曾逢邑人说,风景似桃源”[6],从诗中的描述可见,南溪书院园林环境朴野雅致,以山为门,建筑采用茅屋的形式,周遭花草环护,园内还能见到野生的雏鸟和子猿,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又唐元和中,士人李宽中在湖南衡阳城北石鼓山创建李宽中秀才书院,石鼓山位于湘水和蒸水合流处,景致开阔,被称为“湖南第一胜地”,成为后世石鼓书院的前身。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洛阳人李渤和其仲兄李涉避战乱卜居南方,在距府城北十五里的庐山五老峰之阳隐居读书,他隐居读书的地方后来就被称作白鹿洞,长庆元年(821年)李渤出任江州刺史,遂在之前隐居之处杂植花木、环以流水、洞修台榭,使其成为庐山的一处胜迹。自此四方文人学子纷纷前往聚会读书,鲁公颜真卿(709—784)曾寄居郡之五里,其后裔孙颜翊曾经率子弟30余人受经洞中。唐代诗人杨嗣复在《题李处士山居》中提到了李渤在白鹿洞修建台榭的事“卧龙决起为时君,寂寞匡庐惟白云。今日仲容修故业,草堂焉敢更移文”[7];可见,唐代白鹿洞书院教学和园林环境包括了建筑、理水和植物景观。
2.3 五代书院园林
五代十国时期具有教育教学功能的书院数量上升,这预示着具有教育教学功能的书院将取代读书治学的书斋。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大乱,梁、唐、晋、汉、周五代割据,大量拥有丰富藏书的读书人以避乱的心态隐居山林。《南唐书·郑元素传》载“避乱南游,隐于庐山青牛谷,高卧四十余年,采薇食蕨,弦歌自若,枸剪茅,于舍后会集古书,殆至千余卷”,读书人选择在远离城市、自然环境优美、人烟稀少的山间,在与僧院、道观并立的风景绝佳处开荒建屋,修建庭院、楼阁,过着半隐半读,教授生徒的田园隐居生活,并聘请儒学大师在山间旷地讲学,于山间建造房舍贮存书籍,一个个独特的、远离市井的、从庸常的物质生活中独立出来的山间庭院拔地而起。读书人在庭院中过着自给自足的耕读生活,以居学为重,自学为主;这一时期的书院建筑还只是简单的几间藏书、读书的房舍,非常简单,以地方民间建筑为特色。可见,书院园林在远离城市的山间形成,重在陶冶情操,山水之于书院充当了天然背景的作用,主动性的、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并未多见,这股强大的文化势力在后来近千年的时间里一直不断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
3 兴盛期——两宋:自然为宗 四方纳景
3.1 择址

图2 江州濂溪书院(改绘自岳麓书院展览馆展板)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8]。两宋是书院园林发展的全盛期,如果说宋以前的士人是为了避乱读书山林,亦或是为金榜题名而苦读林下的终南捷径,那么到了宋代,士人已经不满足于在环境清幽之地读书陶冶性情,而是主动地将自然陶冶纳入书院的教育体系和园林体系中来了,书院将游历山川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成为化育人的途径,更富于积极的意义。宋理学大师多酷爱山泉林壑,书院在理学大师思想的影响下也与自然山水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一生嗜好山水,为官任职每到一处都不忘寻访胜迹,黄庭坚曾称周敦颐“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9]。庐山北麓莲花峰下有一条小溪从山洞蜿蜒流出,注入湓江,与周敦颐家乡的溪流(图1)非常相似,于是周子“濯缨而乐之,遂寓名以濂溪”,即以“濂溪”命名书堂(图2),并赞美园林景致曰“庐山我久爱,买田山之阴,田间有清水,清泚出山心,山心无尘土,白石磷磷沈,潺湲来数里,到此始澄深,有龙不可测,岸木寒森森。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倚梧或欹枕,风月楹中襟。或吟,或静默,或酒,或鸣琴,数十黄卷轴,圣贤谈无音。窗前即畴囿,囿外桑麻林……吾乐盖亦足,名溪以自箴”[10]。濂溪书堂是园林兴盛期第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品,在书院园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园林所体现的中正平和、尚雅自然、冲融和谐的风格成为后世书院园林审美标准和追求的境界。从濂溪书院开始,书院园林开启了从被动陶冶于自然到主动经营自然的阶段。
两宋书院择址注重周边山水和微气候环境的因素,更注重对于自然环境精神上的追求,园林选址倾向于“景致丰富、可跋可息”之地,为了追求出尘、幽邃的世外桃源不惮劳苦、跋山涉水。如朱熹之云谷书院“地高气寒,又多烈风,飞云所沾,器用、衣巾皆湿如沐,非志完神旺、气盛而骨强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缘崖壁,援萝葛,崎岖数里,非雅意林泉,不惮劳苦,则亦不能至也”[11]。可见,此地处于远离市井的深山之中,景色优美,谷深树茂,环境幽邃,谷中有充满生机野趣的自然山水,如曲折的南涧、斗绝的石瀑、层叠的危石,亦有桃蹊、竹坞、漆园、茶坡、池沼、田亩、井泉、云庄、东西寮等淳质清净的田园。但是,由于地高温低,风力和空气湿度都较大,只有对山水非常喜爱并不怕辛苦、不惧危险的人才能到达。其次,两宋书院选址重围合性,环境具有“内宽外密、远近环合”“巨狭为口、以限内外”的特征。如朱熹在《白鹿洞谍》中论白鹿洞书院选址“近因按视陂塘,亲到其处,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遯迹著书之所”[12]。
3.2 山水
《孟子·尽心上》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澜”即所谓的“大水广阔”之意,并且,书院观水将“大水”或泻而为瀑,或渟而为渊,或溅而为濑,或聚而为湖的形态与“道”联系在一起,水为书院师生营造了修身、养性、悟道的生境,成为沟通人道与天道的中介。如白鹿洞书院门前的贯道溪,水从凌云峰山顶跌下,流经书院门前,后汇入梅湖,最终汇入鄱阳湖,经历一路瀑、涧、溪、湖的形态变迁,这川流不息的生生景观成为书院精神的典型观照;嵩阳书院园林水景类型丰富,水体呈现涧、瀑、渊、濑、溪、泉等不同的形态,多种水体组合在一起相互映衬变换,形成襟带之趣;书院东北的叠石溪,发源于谷北高登岩,一路奔腾澎湃,动态水景丰富,后汇入书院前的双溪河,再后注入以平静广阔的静态水景见长的颍河,溪涧花草四时有色,可谓动静对比之趣的胜境,即“嵩下之水皆约束于陡峡峭壁,喷薄春激,独此(颍水)平阔广衍、一望浩淼”[13];岳麓书院的清风峡,峡内兰涧石濑景色清幽,小气候宜人,为书院观景的佳处。
朱熹认为山石林泉之间的优游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他说“远游以广其见闻,精思以开其胸臆”[14]。两宋时期书院园林的山水理法以围绕自然山水进行园林化处理为主要手段,审美主题倾向于欣赏山石和水体的自然状态,崇尚自由生气的人文精神。嵩阳书院有著名的“三公石”和“甘拜下风石”,三公石是3块体量巨大的天然山石,最大者高约8m,最小者高约6.5m,3块巨石均可供人攀登其上,最大的一块可供10人在其上排坐,北宋枢密使张升常与人踞石上饮酒消遣,可见石体量之巨大;三公石不但形色独特,还被赋予浓厚的人伦色彩,清人耿介曾经用“五色灿烂,具五行之性,兼备五德”来形容三公石的灵性,并将三公石与太师、太傅、太保相媲美。杭州敷文书院有一处“天然的大假山”即书院西侧一片天然的石林,据说清乾隆年间书院的山长次风先生(1703—1768)非常醉心于这片云涌波幻的奇石林,常常晨夕相对,细细观赏(图3)。

图3 敷文书院山石景观(作者摄)
可见,这一时期的书院园林重视书院周围自然环境的园林化,通过对自然山水文人化的赋诗、题名或者借景、点景等空间的安排经营,突破空间尺度上的限制、冲出围墙的阻隔,变自然环境为园林景观,使周围自然环境空间成为园林化的观赏空间,悬崖、山谷、峰巅等自然景致成为书院园林的构景要素和审美对象,从而满足士人讲学、悟道、修养身心的需求。
3.3 建筑
两宋书院园林建筑布置灵活多变,一切皆因自然造化。书院建筑朝向并非都禁锢于南北方向,而是随着自然条件的不同因地制宜,建筑随着自然山体地貌条件调整方向,或是居于崖畔,或是隐于山麓,建筑充分利用自然条件自由布局,高低错落、层层叠叠,与外部自然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自然山水是一种先天的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理学大师走进山林,从人文景观的角度于自然山水中点染建筑,弘扬文化信仰与自由精神,如朱熹时期的白鹿洞书院园林营建主要围绕贯道溪展开,包括建桥、修亭和题刻3种形式。建筑布局不强调轴线对位,无墙垣的束缚,注重与周边环境的整体气质,重视有景可观,具有放啸山林、饮吸山川的空间意识,即不仅仅满足于建筑窗前寸石半枝的小景,而是要求周边要有丰富的山川、溪涧可游可观,注重身体力行的实际体验。
3.4 植物
两宋书院园林中最常出现的植物景观单元就是植物与自然景致组合形成的自然山水植物小景,如岳麓书院清风峡内著名的自然山水植物小景兰涧与石濑。兰涧为岳麓书院后山沿游步道的一条险沟,因两岸峭壁上长满兰花而得名。兰花生活在深涧溪边或林木茂盛的地方,就像古代为了“志于道”的理想隐逸山林的士人一样,自古被中国文人所喜爱。孔子曾经对兰抚琴,吟诵“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15]感叹人生抱负不能实现;石濑是藏于兰涧中的石潭或者指水流碰触涧中石块形成的激流,朱熹在《石濑》中吟道“疏此竹下渠,濑彼涧中石,暮馆绕寒声,秋空动澄碧”[16],石濑象征自然界的天籁声像、荡涤尘埃,与孔子“洙泗浮磬”中水中石块经流水冲刷发出美妙声响之境有异曲同工之妙,站在清风峡的清风桥上望兰涧、石濑,水石相驳激,声色俱丽,借以抒发人物的情感和志向。
植物儒学化之风较盛,如梅花的百折不凋和富于骨干,兰花的幽静典雅,竹子的谦虚品质,都富涵伦理色彩和理学之精神,深受古代读书人的喜爱,广泛应用于书院学斋、讲堂附近的庭院中,成为烘托书院气氛、调节园林情趣的重要元素。桂树是象征书院功能的特色植物,由于古代科举考试在秋季进行,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所以人们用“折桂”比喻高中状元,书院庭院中植桂的习俗代表了对参与科举考试的士人的美好祝福,如朱熹非常喜爱桂树,在白鹿洞办学期间,曾经亲手植丹桂2株,现在先贤书院丹桂亭前竖有“紫阳手植丹桂”的石碑;松柏类常绿植物多用于书院祭祀建筑的周围,象征着长寿与永恒,用以烘托庄严肃穆的气氛。
两宋书院园林植物景观具有自然疏朴的风貌,植物观赏强调“观生意”的审美观。程颐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人与天地一物也”[17];朱熹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灵万物都自然而然地融入宇宙,充满自由与生机,“那个满山青黄碧绿,无非天地之化,流行发见”[18]。理学家通过园林中的草木、花畦、蔬圃等景致观天地万物的生意,从中体会到宇宙本体的无处不在,体会到园林景物融入宇宙而具有的永恒和谐的宇宙韵律和无限境界。“观生意”成为理学的园林审美方法,自此,园林中的一草一木与天地人凝为一体,实现了物我的交融,将园林审美向写意的方向更推进了一步,致使之后书院园林环境中出现了许多以“观生意”为主题的景物。
3.5 景题
宋代理学思想发达,书院园林中的景物开始出现景致命名。理学家常常把寓意理学义理的词汇和园林景物命名相结合,使园林中的山水、草木、建筑等都成为理学思想的代言,如取义儒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以为为学之要”[19]的朱子紫阳楼内的“敬斋”和“义斋”,喻义“仁善”思想的武夷精舍中的“仁智堂”和“观善斋”,其他的还略如诚意堂、正心堂、志道堂、道源堂、明道堂、求志堂、学古堂、行恕塾、春风楼、仁石、泽物泉、尊贤坊、静观亭,寄情以物,寓理于景,达到吟咏书院园林美景、劝学励志、阐发儒家义理的目的,对园林景物起到了藻绘点染的升华作用,是周敦颐“文以载道”的文艺美学观最直接的表现。
4 结语
书院是在古代聚徒讲学的私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继承了古代私学的教育思想和学术精神,是私学发展到后期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化的新形式。书院园林随着书院的发展变迁而发生变化,是一种读书环境的营造,亦是一种带有强烈理学审美色彩、儒学化的特殊园林类型。书院园林最初产生于山间,作为书院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重要部分,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发挥着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净心情的重要作用。从春秋到两宋时期是书院园林由萌芽到兴盛的重要阶段,是最能代表书院端士习、伸士气、揆文教、振文风之精神的儒学化园林;两宋以后,书院园林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精神气质和营建形式。春秋到两宋时期书院园林的研究对于书院园林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