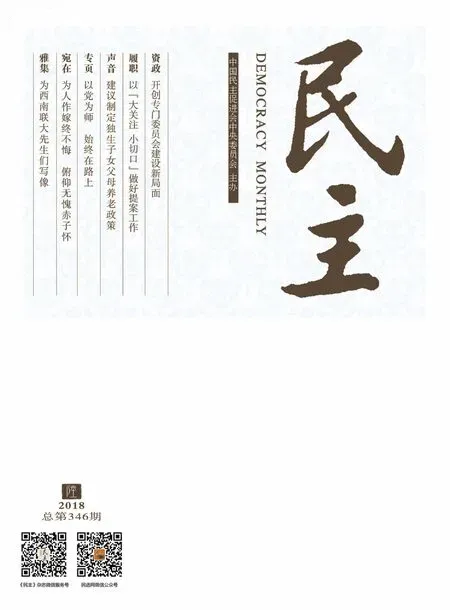为人作嫁终不悔 俯仰无愧赤子怀


纪念我们的父亲叶至善先生
叶小沫 叶永和
4月24日,是我们的父亲叶至善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父亲的一生是为编辑的一生。1986年,父亲写了《编辑工作的回忆》,文中说:“我生长在一个编辑的家庭里。我的父亲叶圣陶,大家都说他是文学家,是教育家,是语文学家,其实他当编辑的时间比干什么都长,花在编辑工作上的心力比干什么都多,就是没有人说他是编辑家。如果从中学时代编油印刊物算起,他连头带尾,一共做了73年的编辑工作。”他又说:“我的母亲胡墨林也是当编辑的,虽然过世得早,算起来也做了28年编辑。”接下来他说:“抗日战争后期,开明书店在内地成立了编辑部……父亲的几位朋友看他实在忙不过来,知道我文字还清通,懂的东西比较杂,撺掇我辞掉了教员,帮我父亲编辑新创办的《开明少年》月刊。那是1945年8月,我27岁……从1945年8月到现在,足足41个年头了,我还没有放下编编写写的工作。”父亲是在写了这篇文章的20年后过世的,这样算起来,他做编辑也有60余年。像爷爷一样,他当编辑工作的时间比干什么都长,花在编辑工作上的心力比干什么都多。他热爱编辑工作,说自己有编辑瘾,老也干不够。
父亲当编辑,新中国成立前在开明书店,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这两家出版社面对的读者都是青少年。父亲编辑了许多优秀的青少年期刊和图书,那时候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件事情上。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二十几年里,父亲把收集、整理和编辑爷爷的著作当成了自己最主要的工作,编辑爷爷的各种图书多达数十种。从1986年起,父亲花了八年的时间编辑了《叶圣陶集》的二十五卷本。从2001年起,他又花了五年的时间对《叶圣陶集》做了重新的修订和再版,并撰写了第二十六卷,34万字的长篇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
写《父亲长长的一生》的那一年,父亲已经84岁了。他身体虚弱,重病缠身,走路要人搀扶,起居要人招呼。但是他鼓励自己说:时不我待,传记等着发排,我只好再贾余勇,投入对我来说肯定是规模空前,而且必然是绝后的一次大练笔了。就这样,父亲凭借着对爷爷的热爱,凭借着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拼尽了全身的力气,以每天千字左右的速度,写完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也是最后的一部作品。父亲用他独有的散文笔法,记录了爷爷少年时的睿智好学,青年时的血气方刚,中年时的爱国情怀,老年时的孜孜不倦;记录了爷爷在各个时期的成长历程,和他全身心投入的许多项工作;记录了爷爷参加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交结的各方各面的亲朋好友;记录了爷爷在家里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的为人。在对爷爷一生的描述背后,是爷爷经历的那些不平静的年代,那些不平静的事件,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写《父亲长长的一生》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顾不上越来越糟糕的身体,抛弃了身边所有的琐事,没日没夜地赶稿子,等他把写好的文章交给出版社的时候,唇下那浓密的雪白的胡须竟有一尺多长。这时候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可就像气球一下子泄了气,他再也起不来了。父亲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从此没能离开医院一步。2004年末,父亲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看到了新出版的《父亲长长的一生》。他把书送给曾为他和爷爷动过手术的老院长吴蔚然。他说:“我父亲对我的关心和教育使我受益终身,我应该写一本书来纪念他。”这饱含深情的话道出了他的心愿:写一本书献给亲爱的父亲。
七百多万字,二十六卷本的《叶圣陶集》的出版和再版,应该算得上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从收集、抄写、分卷、编辑、写前言、写编后、为每一卷配照片、为每一张照片写说明,从书籍的排版到封面的装帧设计,到后期大量的校对工作,所有这些编辑事务放在一个人身上,工作量真是大到难以想象,但是有着丰厚的编辑经验的父亲,坚持每一件事情都亲自动手,独揽了做这套书的每一个环节,在责任编辑缪咏禾先生的倾力协助下,最终完成了全书的出版。
缪咏禾先生写文章评价说:“这本书是至善先生晚年创作的一个高峰。它叙写了上个世纪中一个中国文人的心路历程和道德风貌,展示了叶圣陶先生和国家、社会、事业、家庭等众多人际间的丰富关联和互动,书中叙写的种种人和事,既是对历史的记述,又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传承意义。”父亲过世后,有关部门在为他写的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话:叶至善同志的一生几乎都在用语言、用笔墨、用实践在编写、在解读、在传承父亲叶圣陶先生的教育思想,编辑思想和文艺创作思想,为后人研究叶圣陶留下了翔实可靠的资料。我们以为,给父亲做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是符合事实的。
就这样,为了青少年读者,为了爷爷,父亲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为别人作嫁衣裳,为此放弃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想写的书,而今留下来的一些文字,是父亲在做这些工作的空隙,见缝插针完成的,真的是少之又少。为了纪念父亲,我们把他的文字收集起来进行整理,出版了《叶至善集》的六卷本。尽管只有六卷,也足以反映父亲对于编辑和写作的热爱,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熟谙;也足以看出父亲涉猎的方面众多,兴趣爱好非常广泛。父亲爱动别人没有动过的心思,爱尝试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他总是不断地求新求好。读者在认真看过父亲的作品之后,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兴味的人。
珍贵的瞬间总会留在头脑里,成为抹不去的记忆。1987年4月24日,在父亲70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摆满酒菜的圆桌前,准备举杯祝寿,这个时候爷爷站了起来。他说:“今天是至善的70岁生日,我要说几句话。”爷爷的举动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热闹的席间顿时鸦雀无声。爷爷善于演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论大会小会,他都可以站起来就讲,不用讲稿,意思却能说得清清楚楚。但是在家里,爷爷从来没有这样郑重其事地讲过话,在我们的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而且看得出来,这些话爷爷想了有些天了。那一年爷爷已经93岁了,说话的声音依然洪亮,条理依然清楚。可惜的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爷爷要讲话,没有能把他的话记下来。时隔多年,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我们已经记不清了,大概的意思却没有忘。爷爷夸奖父亲,说父亲做编辑很努力、很认真,他兴趣广、肯钻研,做了许多很有创意的尝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他,做得比他要好,还举了一些例子。最后他说:“对于这个儿子,我感到很满意。我说这些话,也有要大家向他学习的意思。”爷爷的讲话,让这次家庭寿宴显得有些庄重。大家鼓掌举杯,向两位老人表示敬意。父亲的脸上是得意时才会有的充满童真的顽皮的笑。70岁的儿子得到93岁的父亲的肯定和夸赞,世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儿吗?20世纪30年代,爷爷写过一篇《做了父亲》,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节他说:“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在那一刻,爷爷有没有想起五十多年前自己写下的心愿?
十个月后,爷爷过世了。
人们常用父爱如山、父子情深来形容父子之间的爱,而这远远不能描摹爷爷和父亲间的情感。父亲和爷爷生活了七十年,一起经历了所有的家事国事。在生活上他们俩是父子,爷爷爱儿子,小时候教他歌谣,给他讲故事,少年时辅导他学习作文,中年时教他做编辑。直到九十多岁自己住进了医院,每次父亲去看他,走的时候他还会嘱咐父亲路上多加小心。父亲孝敬爷爷,帮他料理家事国事,分担他的喜怒哀乐,爷爷老年的时候,他更是形影不离、无微不至照顾左右。在学习上他们俩是师生,爷爷这个老师从学步到做人做事,事事诲人不倦;父亲这个学生从学作文到学做人,事事学而不厌,一辈子都像学生那样,把自己写好的稿子拿给爷爷批改,认真琢磨改动的缘由。六七十岁的时候,他还像小学生那样,向爷爷学习怎样写古诗词。在工作上他们俩是同事,一起编辑书刊,一同讨论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平日里他们俩是朋友,喝酒聊天相知相伴。我们常常会为爷爷和父亲间的情义感动,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话来表述这对父子间的爱。现在想想还是父亲自己说得好。他说:直到父亲过世,我才突然感觉到失去了倚傍——七十年来受到的关心和教育从此中断了。父亲的关心和教育似乎是无形的,像空气一样。我无时无刻不在呼吸,可是从没有想到,自己生活在空气的海洋里。
今天是父亲叶至善先生的纪念会,我们却说了好些爷爷和父亲的往事,因为说到父亲,实在离不开把父亲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人的爷爷,纪念父亲就是纪念爷爷。更巧的是,今年刚好是爷爷过世30周年,在这个日子里,就让我们一起来缅怀和纪念这两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家吧。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了。每当交响乐在耳边响起我们就会想起父亲,是他最早让我们听到了莫扎特小夜曲和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每当欣赏油画作品我们就会想起父亲,是他让我们认识了米勒和他的《晚钟》,梵高和他的《向日葵》;每当仰望星空我们就会想起父亲,是他教我们认识了银河系,认识了牛郎星和织女星;每当看到了花草我们就会想起父亲,是他告诉我们那是乔木,那是灌木,那是豆科植物,那是蔷薇科植物;每当看到墙上挂着的爷爷写的“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对联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父亲,他做的这副对子是他一生的写照,更是留给我们、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父亲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一直在伴着我们生活,伴着我们前行!
父亲,我们想您!父亲,我们爱您!
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 听其言也厉
商金林

至善先生(左)与本文作者合影。
我与至善先生的交往将近30年。第一次见到至善先生,是1976年的冬天。承蒙他的关爱,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得到他精神的熏陶。最后一次见至善先生是2006年2月22日,因为要去韩国讲学,特地到医院与他作别,一周后至善先生离开了我们,那是2006年3月4日。
在我的记忆中,至善先生是个极其认真的人,每做一件事总想做得十分好,生怕有一点不周到,即便是给朋友写封短信,也得先打草稿,逐字逐句斟酌,觉得妥帖了才恭恭敬敬地誊抄到信纸上。做事比写东西更认真,万一有做得不够完美的地方,他会一直记在心里。
圣陶先生有个短篇小说《春联儿》,写他抗战期间暂居成都郊外(西门外罗家碾王家冈)期间,出城回家常坐鸡公车(木制的独轮车),车夫中最熟悉的是老俞,老俞年纪与圣陶先生相仿。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军队当排长,在前线“打国仗”(抗战),小儿子在家也推鸡公车,不料因病让医生开刀给开死了。老俞很坚强,写信嘱托大儿子好好“打国仗”,“把东洋鬼子赶了出去”,“赶紧就回来”。过年的时候,他请圣陶先生写副对联,“洗刷洗刷晦气”。圣陶先生给拟的一联是:“有子荷戈庶无愧 为人推毂亦复佳。”老俞看了很高兴,说这正是他想说的话。20世纪60年代初,至善先生到成都视察,打听到老俞还健在,特地去看望他,见他的生活很苦,就给了他40元钱。回来告诉圣陶先生。圣陶先生问:“钱,他要了?”至善先生说:“要了。”圣陶先生叹了一口气,说:“你不该这样做。”至善先生说他事后也懊悔,觉得这样做有点“施舍”的味道,会伤害到老俞的自尊和尊严,应该想得更周到些。连做善事都得讲究方式方法,可见至善先生是个多么认真,多么尊重人、体贴人的人。
去过叶家的人都知道,他家住的是四合院,要走进至善先生正房的客厅,得要经过“正门”和“中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门”和“二门”。平时,他家的“大门”和“二门”总有一扇是敞着或是虚掩着的,轻轻一推就开了。有记者好奇地说过,在北京像圣陶先生这个级别而不关门的只有圣陶先生这一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学术研究重新步入正轨并日益繁荣。由于研究资料匮乏,一时间走访名家成了寻找资料的一条路径,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也骤然急增。又因为联系起来不方便,别说没有手机,就连公用电话也少之又少,来者大多是不速之客。为了减少干扰,人们大多在大门上装了“猫眼”,听到敲门声,悄悄地从里往外瞧,看清了是何方来客再决定是否开门相迎。叶府的“大门”和“二门”是敞着或虚掩着的,跨过第二道门槛,透过明亮的玻璃窗,远远地便能看到至善先生就坐在北屋书房里看稿或写稿。客人来了,他就把手头的工作停下来,起身相迎。那些年,叶家真是门庭若市。我是事前预约好了才去的,常常刚坐下,新一拨客人又来了。遇到这种情况,至善先生就把我让到他的书房,让夫人夏满子陪我聊天。他先接见来访的客人,圣陶先生得空也出来一同接见。来访的客人大多是有备而来,请教这样那样的问题,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至善先生对来访者说“是否可结束了”,“哎呀,怎么把我们当字典用啊!”希望访问的时间不要拉得太长。圣陶先生毕竟年事已高,话说多了就吃力。他不愿意让来访者感到难堪,类似“挡驾”的话只好由至善先生来说。有一位老朋友当着我的面奉劝至善先生说:你那么忙,事前没有约好的客人有的可以不见呀,你到别的房间,就说不在家不行吗?至善先生断然回绝。他说:“不能这么做,宁可把客人骂走,也不能躲着不见。”他对人就是这么实在和真诚。
1979年,中共中央公开了在民主党派工作的一批共产党员,胡愈之先生的秘密党员身份亦随之公开,一时舆论哗然。要是心胸狭窄,用怀疑的心态看胡愈之先生,最郁闷该首推圣陶先生。圣陶先生和胡愈之先生早在1921年就相识了,在商务印书馆共事多年,又一起策划过开明书店。1945年5月,圣陶先生听到胡愈之先生在南洋某地病逝的传言,当即约请茅盾、傅彬然、宋云彬、曹伯韩、胡子婴等好友著文悼念,汇编成“纪念胡愈之先生的特辑”,在他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圣陶先生写的是《胡愈之先生的长处》,盛赞胡愈之先生的“自学精神”“组织能力”“博爱思想”和对朋友的“友爱情谊”。当时,有人悄悄对圣陶先生说:“万一这消息是误传,怎么办呢?”圣陶先生回答:万一是误传,我们有幸运与他重行晤面,“这个特辑便是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也颇有意义”。这个消息果真是“误传”,胡愈之也成了唯一一个能够在生前读到追悼自己的文章的人。
新中国一成立,胡愈之先生成了出版总署署长,圣陶先生是副署长,另一位副署长是周建人先生。当时,文化人中郭沫若是政务院副总理,正部级的只有茅盾和胡愈之。有人纳闷,胡愈之怎么当了那么大的官,排名在圣陶先生之上?而圣陶先生则很高兴,对胡愈之十分尊重,精诚团结,共同开创和规划新中国的出版蓝图。“文化大革命”期间,周建人当上了中央委员,圣陶先生这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到胡愈之中共党员的身份公开后,圣陶先生这才知道他在出版总署时,排在他前面的署长胡愈之是中共党员,排在他后面的副署长周建人也是中共党员。圣陶先生是怎样的感受呢?这我完全可以从至善先生的谈话中体悟到。至善先生多次和我谈这件事。他对周建人先生总是那么敬重,对胡愈之先生则赞不绝口。他说到1979年,父亲与胡愈老的交往已有五十多年,两人是再要好不过的朋友,父亲竟然不知道胡愈老是党员,胡愈老真称得上是“守口如瓶”。又说胡愈老对党交待的事情“守口如瓶”,对朋友之间说的话也一定会“守口如瓶”,他“绝对不会出卖朋友”。又说现当代文化人中最值得写传记的是胡愈老,他为什么要入党、入党的经过、为党做了哪些工作,这些极其珍贵的史料胡愈老生前没有说,别人也不知道,不能流传下来,太可惜了。可见至善先生的襟怀是多么宽广。
《论语》上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至善先生正是这样的君子:他严谨、严格、严肃,似乎总让人感到有几分敬畏,但他的内心特别善良,体贴人,关心人,处处让人感到很温暖。他思维敏捷,评论问题常常发别人所未发,见解精辟,话说得都很庄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上说的“君子”这“三变”,正是至善先生真实的写照,也是至善先生崇高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