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母去郑州
◎王自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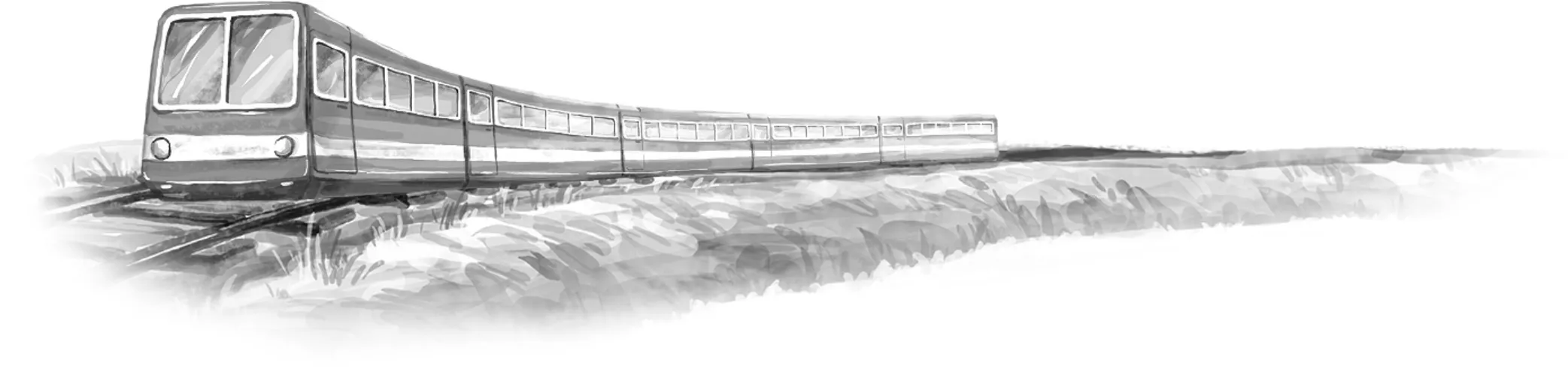
周日,终于挤出点时间去郑州,侄子住院,我和父亲去看他,顺便送母亲。母亲昨天刚到家,今天又要去看着了。收拾好了东西,我提了包,走出小院。街面清冷,太阳虽然很亮,但穿不透这层霾。雾蒙蒙的天气,让人烦闷。自从进入了冬日,似乎就没有蓝天了。
等公交,上车,我照顾着他们,他们虽然才六十多岁,可步伐已经明显迟缓了很多。到了车站,我排队买票。父亲还要买,他总是这样,什么事都是自己干。我说你歇吧。上了车,车子要十多分钟,母亲就急,说咋这么慢。问我票价多少,我说五十。她又懊恼,说不如在路边等车了,在路边要便宜一些。
车子很慢,走走停停,到郑州时天已黑了。车辆加油的间隙,母亲下车给父亲买了个饼夹菜。她说,你爸来的慌,早上都没有吃饭。终于到了车站,夜色昏沉,凉风飒飒,像蛇能一直钻进人的骨子里。周围的建筑如一群高山巨兽,让人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就像在深深的峡谷。父亲急躁了,说赶快打的去,晚了。有辆车停在路边,他一问,马上就缩回了头。要三十五,上次只十元呢。我说,那是早上,现在可是周日晚高峰。
父亲咬咬呀,走吧,坐三轮吧,不能再耽误了。我安慰他,别慌,不差这一会了。
好在问了人,坐了公交。相比其他路的闹嚷,这辆通向医学院的人并不多,坐在车上,外面灯火迷离,人影幢幢,大城市在夜色中展示着它的魅惑与华彩。但我知道父母的心思,他们听着报站,看着时间,恨不得飞到医院呢。车子走到路口,停了。父亲就
在后面急:咋又停了,咋回事呢?旁边人看看他。我没有吭声。他忘了,有红绿灯啊!
终于到了医院,看到了孙子,父亲却沉默了。坐在一边,看着输液的孩子,并没有了什么话。孩子说痒,父亲就坐在旁边,为他挠痒,孩子闭了眼,一定很舒服。我就想起小时候,父亲常用手捏捏我们的脸蛋,摸摸我们的额头,那手暖暖的,很软,很柔。而每到了夏日,父亲最大的享受,就是晚饭后,一家人聚在一起,父亲光了膀子,让我用小手给他挠脊背。他背上有很多疙瘩。坑坑洼洼,像是雨后的河滩。可是,父亲闭着眼,垂了头,不住地说:“上一点,下一点。用力,好。”挠不几下,就慌着说,好了,好了,歇会吧。他爱我们,做什么都生怕累着我们。有时候母亲看不惯,要我们扫扫地。父亲就慌的夺笤帚,去玩吧,我来。大家都说父亲惯孩子,父亲并不说什么。只是一个中秋节,我们赏月。父亲忽然动情地说,你们弟兄仨,都是我的宝呀,一个有点啥,这日子就没法过。当时小,并没有觉得什么,现在想想,从沉默寡言、性格内敛的父亲口里出来,这话的分量有多重!
呆了一会,就要走了,赶火车。孩子睡着了,父亲又轻轻地在他脸上捏了一下,俯下身仔细看了看。走出大楼,父亲把母亲的衣服递给我,说你披上吧。寒冷的街头,没有几个人。二弟停下来,买了三串关东煮。爷仨边走边吃边聊着。所有的郁闷似乎这一刻都忘掉了,就像以前父亲领着我们弟兄出来玩一样。——云淡风清,岁月静好。无忧无虑,连天空都是橘红色。
走到火车站西广场,天灰蒙蒙的,灯光下,雾霾遮天盖地,而旁边的空地上,有些人排成一队,顺了音乐的节奏,扭动身体,红红绿绿的衣服,像一团火。上了车,找到位置,父亲很快就睡着了。脑袋低垂着,像一个硕大的谷粒。二弟也睡了,他这几天守着,熬得太困了。忽然手机响了,是母亲,问我们到哪了。二弟问孩子,母亲说又烧了。话语很轻,父亲却醒了,问,又烧了。眉头凝着。
窗外,是一片苍茫的夜色,几星灯光,像是泪眼。忽然撞过来的一辆车,怒吼着,像是一道银色的闪电,又像一个光芒灼灼,一身银袍的怪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