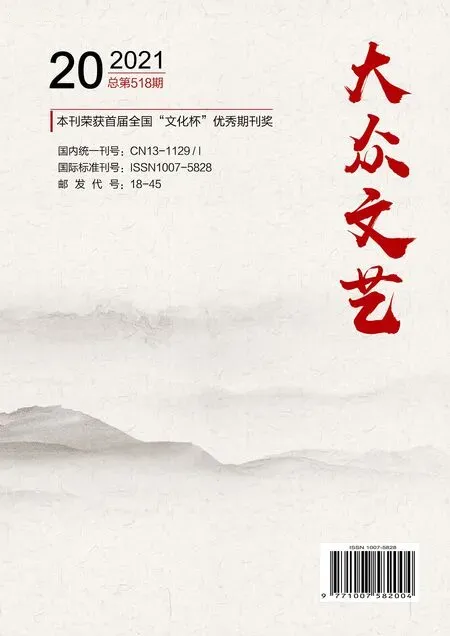大数据时代下的美术史研究转向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50000)
所谓大数据时代,指的是信息时代下海量数据的集合。哈佛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著作《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思维的大变革》中最早将大数据概念系统化,他认为大数据时代开启了一次全新的时代转型。他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大数据时代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12013年11月10日,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WE大会”上,做了题为“通向互联网未来的七个路标”的演讲,也着重指出大数据时代下的数字化与新媒体技术将会成为一种重要社会资源。
正如海德格尔就此提出技术并非以自我为本质,“技术是一种去蔽之道。在揭示和无蔽发生的领域,在去蔽、真理发生的领域,技术趋于到场。”2美术史作为一门研究美术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也在大数据时代下积极的获取数据与新的研究范围与技术。美术史学科研究由此出现新的可能。可以说,新的视觉文化要求美术史研究观念与方法不断更新。
一、由“概念”到“数据”的美术史范式
首先,美术史的研究与发展已逐步与技术相结合。美术史作为历史发展信息载体的一种,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数字化的结合必然是大势所趋。早在1994年立项的“美国记忆工程”曾将美国图书馆的艺术图片等历史档案资料全部数字化。此后,各个国家的美术馆与博物馆也陆续加入数字化建设的行列,“数字美术馆”进而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潮流。所谓“数字美术馆”,是现代科学技术及艺术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组织美术史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其指的是运用虚拟现实(Visual Reality )技术、三维甚至四维成像技术以及特殊视觉效应等技术,将现实存在的实体物象以等样的形式呈现于数字空间,使观者以及研究者便利的接触与学习到更加丰富的艺术资源。
巫鸿先生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实体”的美术馆已开始逐渐脱离美术史,建立独立的社会、经济、文化地位,其纯粹的学术性也逐渐递减,而作为“概念”的美术史也指向了学科的独立化、知识化,欲与美术馆相脱离。3然而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美术史的一个独特之处也正是在于其与公共美术馆(Public Art Museum)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以往的传统美术史研究与教学在实践方法上十分局限,如何跨越时空的障碍一直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的美术史研究与学科发展试图摆脱以艺术家、艺术品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并且转至大环境中交换思维,由“概念性”到“数字化”的转向便在所难免。在互联网发达和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下,通过与类似“数字美术馆”等数字化技术的结合,充分利用全球共享的艺术资源数据,以数字化和新媒体技术为传统的美术史学科带来新的机遇,传统“概念”的美术史开始逐渐向“数据”的美术史转向,便势必是美术史研究与学科发展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新趋向。
其次,旧的静态图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对于美术史全方位了解的需求。在数字化与新媒体技术的吸收下,仍然以艺术品为中心的美术史研究如今也迎来了新的传递形式,例如艺术作品的全景式再现,予研究者、观者以沉浸式的体验等等途径,现都已被广泛应用。这些有别于传统研究方法的新途径实现了获取艺术作品的全方位信息这一目的。虚拟现实再现了“真实”的美术历史发展,美术史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甚至是研究目的得以推陈出新。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下,数字化与新媒体技术确已使美术史研究脱离传统的“概念性”研究范式,并转向到“数字化”的分析与收集。
二、由溯源过去到前瞻未来的美术史观
笔者认为,对于美术史的研究,应该从古今、远近、宏观、微观多种角度引出对其的思考及想象。除却以艺术作品、艺术家为中心,其具体研究内容也应该在时间、地域甚至是社会层次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历史是全体的、人类的历史,美术史同样也是全体的、人类的美术史。美术史的研究范围应该是广阔的,具有“全面性”甚至是“全人类性”的。作为特定时期的发明,具体的美术史应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特定语境相密切联系。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为案例,笔者发现,魏晋以前的艺术品或是被分类为关于艺术的制品,大都是为礼仪、实用目的而制作,这源于当时封建社会的重礼仪倾向以及落后社会普遍强调的实用性,而非纯碎欣赏。我们所看到的其商业价值、美术价值均为后世的附加和转化。而到了魏晋时期,礼仪和实用渐渐不被人们所需,就开始逐渐转向为观赏或为政教而制作。此外,由于当时人类思想依旧落后,宗教影响十分强大,有一部分艺术家或工匠进行艺术创造,仅仅是为了以创造的过程来实现精神上的某种崇拜。再到晚一些的文人画时期,观赏和崇拜的目的也弱了,艺术创作甚至成为仅仅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所以说“美术史”需在时代变化中把握。
21世纪初,巫鸿先生曾提出“开”与“合”的概念,他认为“合”即以时间轴进行的美术史研究方法,这是一条遵循线性与地域空间的脉络,其纵向性的研究属宏观角度,指向美术史与政治、文化、宗教的内在联系;而横向性的研究则属微观,指向地域特征。言外之意,“合”的美术史即闭合的美术史。而“开”则代表美术史研究打破前者注重的线性与地域空间的局限,指向比较视域下的不同地域之间、不同时代之间的考察与分析。言外之意,“开”的美术史即开放的美术史。美术史由原有的线性的、地域的时空逐渐向复杂的、多样的时空转变。而无论是闭合的美术史,甚至是注重不同时代比较的开放的美术史,其显现的美术史观都强调对过去的“追根溯源”。
而大数据时代蕴含着和人类历史、当下及未来相关的混杂性海量数据,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人类在历史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数据化程度不断提高,也为基于大数据思维模式下的美术史观的转向创造了可能。传统美术史研究观念主要基于实物或原物研究,因而更侧重于理解过去,而在大数据时代下的,美术史研究思维的革新之处则是在于让历史成为未来的数据,以此探寻我们所处的当下以及未知的未来。故而传统的美术史观便逐渐无法跟上时代的需要。
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与方法,更是一种前进的方式,以此,人类便能够知解一些既往所无从下手的前瞻性问题。大数据的思维要义也在于重新审视和构造历史认知的时空,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融入新鲜血液。毫无疑问,大数据时代下的数字化、集成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使当代美术史研究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美术史研究也指向对理解未来提供洞见,就此而言,前瞻未来的美术史观也与大数据时代不谋而合。美术史不再限于实体的“馆”,也不再囿于枯槁、晦涩的“概念性”形式,而是在于大数据之中转向为“数字化”,美术史自身发展的未来密码同样也隐藏其中,伴随着数字化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在历史规律的探寻与透视下对未来的前瞻,可以说美术史研究的转向也是大数据时代本身的一个必然选择。
总而言之,在大数据时代下,全球共享的艺术资源数据,以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形式为美术史研究及教学带来新的转向。统的研究格局被打破,美术史的价值与外延也不断被重新定义,任何与作品本身有关的现象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的研究对象。从相对积极的角度考虑,一种全新学科的概念得以建立——不基于严格的材料划分和专业分析方法,而是以“视觉形象”为中心、以数字化与新媒体技术为途径的各种学术兴趣和实践的交汇。同时,美术史学科归根结底也是一个人文学科,“人”和“文”在其中的作用自然不言而喻,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大数据与美术史研究契合的必然性。
注释:
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著 盛杨燕 周涛译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德]海德格尔著 郜元宝译 人,诗意地安居[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巫鸿 美术史十议[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