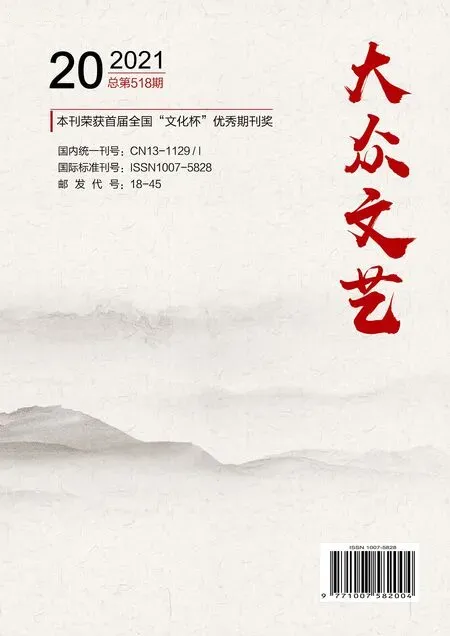彼得·汉德克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中的语言异化研究
(武汉大学文学院430000)
一、语言失效下孤立的存在
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不能依靠其本身而成为人的,‘自我存在’只有与另一个‘自我存在’相交通时才是实在的。当我孤独时,我便陷入阴沉的孤立状态——只有在与他人相处时,‘我’才能在相互发现的活动中被显示出来。”在《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中,主人公布洛赫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交通的困难是作者着力描写的,而相互交通的困难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由于语言的失效。这种失效首先表现为语词的沉默。小说开头,安装工布洛赫来到建筑工地,工人们对他冷漠相向不发一言,忽略了他的存在,他和工人们没有交流,在语词的沉默当中,布洛赫将他们的形体的冷漠当作一种表达——他被解雇了。他的这种理解是放大的,解雇没有得到求证,这或者是一种无端的猜想,可是似乎这些对他都不重要,走或者留对他来说没有差别,在此地他感受不到意义。“然后他就离开了”——他离开的决定是荒诞的。离开建筑工地后,布洛赫开始在市区漫无目的地游荡。布洛赫在漫游中“狩猎”,勾搭上一个女人,和她一起坐上一辆公共汽车,在狭小空间中,两个人的肉体直接照面,但是精神却无法交流。她感到不自在,开始玩弄手提袋里的各种东西。为了缓解这种尴尬,布洛赫突兀地说:“我忘了留张纸条给你。”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想用“留”和“纸条”表达什么。语言在此已经徒具声音和形式,而没有了实际表达的内容。语言的空洞慢慢让布洛赫丧失信心。
有效回应的缺失导致沟通的不能进一步加重了布洛赫对语言的怀疑。布洛赫在一个旅馆中和一个女服务员有一段交流:
你回家的路上需要手电筒吗?布洛赫问。“我有男朋友。”姑娘回答说,红着脸站起来。旅馆里有没有两扇门的房间?布洛赫问。“我男朋友是木匠。”姑娘回答说。他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个小偷在酒店被关在了两扇门之间,布洛赫说。“我们这儿从来都没有丢过东西!”姑娘说。
在这段对话中,布洛赫和女服务员的交流互相缺乏合符逻辑的连贯性,似乎总在一问一答之间陡然跳跃,他们都不能理解对方语言所真正指向的意义,最终是显现为各自诉说着各自的事情,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交流。在语词的沉默和有效回应缺失导致的沟通的不能下,语言开始变形。它首先表现为语言被理解成玩笑。布洛赫在火车站碰到一个熟人,这个人说自己正要坐车去郊区给一场比赛当裁判,布洛赫在沟通不能的情况下,丧失了对语言的信心,把认真的语言当成玩笑。他也跟着开起“玩笑”,说自己也可以去做个边裁。当那人打开自己的背包,给他看了里面的裁判服时,他还是不相信这个信息的真实性,他觉得这裁判服也是开玩笑的道具。
语言变形的另一个表现是,布洛赫开始觉得他人的话语是一种文字游戏,在这种体验当中,布洛赫逐渐对语言产生了厌恶感和憎恨感,似乎语言在对他进行着嘲弄。“在他看来,邮递员关于那个吉卜赛人的讲述就是拙劣的双关语,就是笨拙的影射……似乎他们都在对我眨眼,在给我信号!”此时的语言被布洛赫接收到了,但是这种接收是一种扭曲的接收,他带着自己的愤怒和偏见,开始对语言进行曲解。在他人的语言之中,他不但体会不到交流和沟通的意图,反而更多的是敌意。
有效语言的缺失和语言的变形,导致了人与人存在的不能交通,而在这种语言失效的原因,在于小说世界中人物对存在的忘却,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不是为寻求一种内在的契合,他们在一种茫然失措的状态之中浮游于语词空缺,在一种浑然不觉中沉迷于语词表面的游戏,语词的真正的目的被忘却了,它已经不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全体显示之不断迫切的需要”,而“仅仅是语言上的交接……友好与和气。”
语言失效不但带来人存在的孤立,在这种存在孤立的状况下,极端的后果是死亡,布洛赫隐匿的边境小镇有一个哑巴学生失踪了,哑巴学生在这里无疑是一个隐喻,哑巴是无法有效使用语言的彻底化,语言在此不是有效性的问题,而是能否的问题。在发生危险的时候,他无法把信息通过语言传达出去。最终布洛赫在一条河流中发现了哑巴学生的尸体——他的失语和孤立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二、语言突围失败后的恶心体验
语言的失效情境下,语言已经丧失了它本身应该具有的交通功能,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异化的存在,如果继续遵循异化的语言的游戏规则,那么人无异于生活于一个语言的囚笼之中。布洛赫也感觉到了这种异化的语言对自我的限制,他有意无意地对此进行了一些突围的尝试。
首先他开始尝试不去接收他人从口中说出的语言,而去观察他人形体和表情中传递出来的信息,但是形体和表情的信息常常是模糊不清和暧昧不明的,在这种沉默的观察之下,布洛赫的行动常常是错误的。此外,他不断借助各种现代媒介保持对世界的观察,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几乎都首先去商店买一份报纸,当他和他人的沟通出现阻碍的时候,他也想要买一份报纸来缓解沟通不能下的焦虑,似乎在报纸之中,他能感受到信息和交流的稳定与可靠。他借助的另外一个现代媒介则是电话,在小说中,布洛赫不断给各种他认识的人打电话,但是他在电话之中的交流大多是失败的,他的孩子一接他电话就开始背“妈妈不在家”。前女友跟他聊了半天,才知道他是谁。
除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不能之外,在布洛赫自我与外部有形世界之间,语言也是失效的,这导致布洛赫对世界命名的失败,世界呈现为一个毫无秩序碎片化的存在。
布洛赫面对这种困境,也曾做出反抗。布洛赫在边境小镇的餐厅遇到一位关税官员,这个关税官员对待世界的方式是把它们“价格化”,“当他看到一个物件,比如说一台洗衣机时,他立刻就询问价格。当他再次见到那个物件,他不会从外在标志认得出来,而是从价格上来辨认。而没有什么交换价值的物件,他根本就不打什么交道。”这种把世界事物安排为一个个数字的方法,似乎可以带给布洛赫很多秩序感和安全感,他学会了这种把世界价格化的方式,他也开始一见事物就问价格,但是当他自己在路边捡的一块石头,他无法对它定价,而类似的石头又到处存在时,他感到这种把碎片世界秩序化的努力也是不完全有效的。
到此处,语言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使世界秩序化上都无能为力了,语言对存在的掩蔽开始逐渐剥离,这个无序而混乱的世界的原貌,这个虚无空洞的存在,开始在布洛赫面前赤裸裸地显露。彻底失望的布洛赫遗弃了语言,世界也揭开了它的面纱。无序混乱世界的原貌开始显现,这在他面前是咄咄逼人的。一切细节被无限放大了,似乎要强行吞噬它们所代表的整体。它们“似乎在污染和彻底扭曲着它们所属的人物和环境。”物的世界在没有语言赋予秩序和意义的情况下,开始显露出其凶神恶煞的面目,显得充满压迫感。“在被突然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布洛赫开始与其生活离异,演员开始与其背景分离。
失去了语言赋予意义的世界,万物开始显现出它们的本来面目,物显现为其所是。它们不再为语言符号所代替。布洛赫在旅馆的房间里看到的事物,已经不能再用名字来指称,它们一个个都变成了无法命名的形状。
他开始慢慢感到“羞耻和恶心”,他无法使用语言对事物进行命名,他想回忆,但是回忆中已经没有了语词,只剩下感受和感觉,这种感觉是“羞耻和恶心”:“他整个身体都因此开始发痒。”“他开始觉得一切都很相似;所有的物件都让他想起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来。”事物不再被语言的分析所切割,存在开始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在他眼前,但是这个存在是虚无,“事物完全是它显现的样子,在它后面……什么也没有。”
三、存在困境下选择的晕眩
在小说的结尾,布洛赫在报纸上发现警察已经获得破案线索。警察据线索追踪,在报纸上登了他的画像。布洛赫知晓后又漫无目的地在边境小镇游荡,最终他来到一座足球场。那里正在进行一场足球比赛。布洛赫与一位正在看比赛的销售员攀谈起来。他表达了他独特的观看比赛的视角:一直盯着守门员看而不盯着球看,也就是说,代入守门员的个人视角。
从文学的角度看,守门员很好地象征了人类存在的困境,在球队中,守门员既不可或缺,又可有可无,他存在的意义是非常不确定的,当本队压制对方,本方球门基本没有被进攻的危险时,守门员是场上隐形的存在;但是当本队被对方压制狂攻时,守门员此时则将经历严峻考验,或者成为球队的英雄,或者成为被羞辱的对象。再则,守门员在球队中,和其他十位队员的职责差异巨大,作为一个“特异”的存在,守门员似乎与其他队员有些格格不入,更像是整支球队的“局外人”。
而在面临点球时,守门员的选择又更加是生死判然的考验。一般来说,面对专业足球运动员射出的点球,由于球速过快,守门员无法在看到球朝某一个方向射出之后再做出扑救动作,他必须在看到球射出之前做出预判,并提前做出扑救动作。而在这种情况下,守门员就必须猜测罚球队员可能的罚球方向。一般来说罚球队员会有一个惯常的罚球方向,但是罚球队员此时也在猜测守门员的扑救选择,他可能会出其不意,也可能将计就计。在各种选择的结局都无法做出预测的境况下,守门员可能会在不断的猜测与反猜测中陷入选择的疑难和晕眩。
这是守门员面临的存在困境,也是我们人类存在困境的象征。布洛赫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象征,面临着的是“上帝死了”之后人的外在意义的失落,千年以来的深刻宗教体验在现代瓦解,让人茫然失措,“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许的,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此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之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人开始像守门员面对点球一样陡然直面存在,但是他发现这个存在是难以捉摸的,人猜测存在,但是存在的路向却千变万化,在各种可能性之中人找不到一种确定性的选择。人此时常常堕入庸常的生活琐事之中,沉沦于世内存在者的世界,以逃避无所依凭下的茫然失措,但是这些都不是本真的存在,外在的确定性本质已然消失,人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困境,只有开始自由选择,用行动去创造自己的本质,才可以走出人存在的困境。
在比赛中的点球时刻,布洛赫望着守门员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了中路,而足球——这个存在的象征——也朝中路飞来,守门员稳稳地把它接在怀里。在注视之中,守门员做出了他的选择。但是布洛赫,这个前著名守门员,他的选择会是如何?在他命运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刻,在他曾经犯下的罪恶面前,他会选择直面自我,还是继续逃避?这一切选择仍然没有人能够代替他进行,他必须在猜疑和晕眩中坚定地走出自己的一步,并最终承担起这选择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