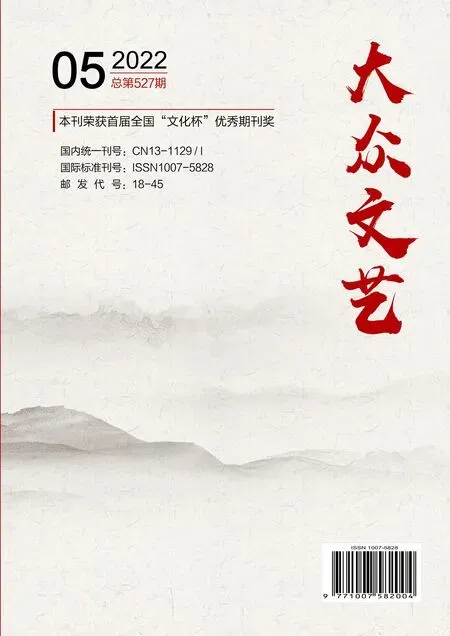浅论钱钟书的比较文学观
刘锦芳 (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文艺学 221000)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公认的贯通中西的文学批评大家,他有着广博的西方文化视野和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积淀,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钱钟书先生从未认为自己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大家,但他所阐发的理论和提出的观点中却流露着比较文学鲜明的特性。读钱钟书的著作,感觉往往是这样的,当你觉得这东西只有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与观点时,他却可以从西方论著中找出一堆类似的例证说明其共性。他能在西方著作中找到众多与中国古代文论《文心雕龙》阐述的观点不谋而合的理论来,他也能从中国的传统文论中给你找出许多证据反驳西方自以为独特的理论观点。很多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在共性中找到差异,在差异中找到共性。但钱钟书先生的比较文学表面上看也是如此,根本上却倾向于文学之间的“打通”与“求同”。
一、“打通”的比较思想
钱钟书先生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提到:“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词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皆‘打通’而拈出新意。”。他认为“比较”作为论证方法中的一种,根本上是将研究对象进行对比,进而找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打通”则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归纳,继而找到研究对象中普遍存在的具有规律的东西,是一种更深层次或者更高意义上的“比较”,钱钟书先生正是在“打通”的思维模式中实现了中西方跨文化的文学比较。这种思维模式是由较为稳固的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支撑起来的,不仅体现在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方面,还体现在不同学科、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互证互释方面。
在《诗可以怨》一文中,钱钟书先生提出:“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钱先生所述观点体现了人文学科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特征,也是钱钟书“打通”思想的体现。所谓“打通”不是狭隘的在不同中苛求共性,而是体现在古今“打通”、中西“打通”,哲学与文学、诗与音乐、书与画“打通”等方方面面。在“打通”的过程中,钱钟书先生尝试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联系,发掘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艺术规律。“打通”地域文化时,他既不崇洋媚外,又不固步自封;“打通”时代文化时,他提倡古为今用、但不厚古薄今、厚今薄古;“打通”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时,他注意挖掘文学的本体意义,努力把文学批评提升到科学高度。钱钟书从文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论述了人们对“诗可以怨”这个观点的误解,用古今中外的例子论证“诗可以怨”观点的由来,对司马迁认为“诗只可以怨”提出了质疑。他让钟嵘同李渔对话,让钟嵘与弗洛伊德对话,还说“有时韩愈与司马迁也会说不到一处去”。然后运用比喻妙言反讽钟嵘、司马迁。作者从两个方面一边比喻,一边点题,语言幽默、诙谐,嘲讽揶揄,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又不失犀利的文学批评。《诗可以怨》这篇文学批评文章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在论及中国传统文艺观念的时候,往往以西方相关例子以资佐证;其二,拆解结构,即它侧重于“怨”的内容,怨是什么,为什么怨,以及怨的功用和怨的后果等。此外,这篇文艺批评的著作对探讨不同艺术门类的规律和创造价值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钟书比较文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实践途径,就是以西方诗学话语为中国诗文中的某些特殊现象或表现手法命名,将西方文学理论作为灯来“照亮”中国文论话语。他能够从历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实践中,拈出无数精彩运用的例子反驳西方人自恃独一无二的“通感”手法。 “通感”一词是西方心理学上的术语,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视觉、听觉、等器官感受往往可以彼此打通,也就是从这一感官向另一种感官的挪移。《荷马史诗》中令很多翻译者搔首搁笔的诗——像知了坐在森林中一棵树上,倾泻下百合花也似的声音,就是“通感”手法的具体应用。然而,中国古诗中也有这种手法的应用,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风吹梅蕊闹”,“水南梅闹雪千堆”这几首诗里面的“闹”字,把事物的无声描绘成有声音的波动。通过中西文化典籍的比照,不仅使某些被人忽视或模糊不清的诗学话语更加清晰,还使得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诗学话语蕴藉得以彰显。钱先生以博通中外的学识、融合中西的文化精神,用大量的事实材料作为论证,使通感这一修辞成为中外文学著作中被广泛接受的文学理论。
二、“求同”的比较思想
世界文学史表明,中西文学常有巧合,无论是宏纲要旨抑或细微末节,常有很多不谋而合的思想观点。在进行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时,到底是重在求同还是重在存异,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思路。但大多学者强调差异性而忽视了彼此间的共同点,而钱钟书更倾向于寻找中西方的相同或相似点。正因为如此,《谈艺录》与《管锥编》在大量征引西方典籍时,主要选取的是那些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能够相容相通、互证互释甚至完全吻合的材料。分析钱钟书著作中的旁征博引,很容易得出即使没有相互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艺术家仍能创造出内容、情节等相似的作品。由此看来,各国的艺术家之间确实存在着共同、共通的“文心”与“诗心”。
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一文中,用大量例子证明中西方文人都认为最动人的往往不是喜剧而是表现哀伤或痛苦的作品。他先是历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刘勰的“蚌病成珠”,乃至欧阳修的“诗必穷而后工”等观点,后又陈述西方诗人和理论家的看法与之呼应。这些与中国文人观点相似的比如福楼拜认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海涅认为“诗之于人,是否像珠子之于可怜的牡砺,是使它苦痛的病料”。最后说明作者的文笔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尽管中西方语言与文化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依旧能在诗歌比喻上存在如此惊人的大量巧合。使我们不得不惊叹于中西方诗人在文学心理上的契合。钱钟书更将不同语言文学中以珍珠作比喻的文献资料逐一细细过目、分类,进而提出一切震撼人心的诗歌,在创作之初诗人必定是如同“蚌病成珠”一般经历过无数的痛苦和煎熬,其广博的中西学识让人钦佩。当钱钟书向读者列举大量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之时,我们对孔子《论语》所言,对刘勰的珍珠之譬,都突然间具有了新的审视目光,将中西方文化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在中西方,无论是对于文学创作,还是对于文学鉴赏,“蚌病成珠”这一批评话语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由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根据不同的社会生活创作出来,虽然发展程度与速度参差不齐,但感受和经历却有众多相似之处,因此中西方文人在一些方面有共同的“文心”是顺理成章的。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变形记》,被视为荒诞派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比它早一千年之久的《续玄怪录》所载薛伟化鱼一事,却也是荒诞之极的作品,二者相比,背景虽不同但文心却在一定程度上相似。对于西方论述戏剧的理论,中国文学作品中甚至可以用七个字概括,即“先学无情后学戏”。中西方文学思想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即有相似的“文心”存在,而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的“文心”是可以相通的。很多永恒不变的主题被反复书写,比如爱情、死亡、惩恶扬善,还有一些写作手法、艺术技巧被中西方文人沿用,或许会稍加修改、有所变化,很明显是历代承袭而来的。中国神话小说《女仙外史》提到的“一口难说两家话”,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观点。中国用“话分两头”的表达方法描写某一时刻,某人正读书,某处火车正过铁桥,某屠肆之猪正呜叫。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名利场》中的场景描写多有涉及此类手法。
钱钟书的比较文学主要体现在探寻文学理论的普遍规律上,它使我们了解到中西的“文心。钱钟书所指的共同的“文心”“诗心”并不是“同声一致”,“艺之为术,理以一贯,艺之为事,分有万殊。”他欣赏的是“和而不同,谐而不一”。每个民族不是泯灭自身的特色去应和其他文化,而是用自己的特色去融入其他民族的特色。其他重点研究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学者不同,钱钟书秉信古今中外,乃至不同文化、不同话语、不同学科之间,都有可能殊途同归,存在着共同的诗心、文心。
三、钱钟书及其比较思想的地位
钱钟书在青年时代就已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著名学者吴宓曾感叹“国内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年轻一辈中则要推钱钟书”。钱钟书写于四十年代的诗话著作《谈艺录》与完成于七十年代的四卷本巨著《管锥编》最为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治学风格,集中反映了其学术成就,出版后不仅广受好评,一版再版,而且被奉为中西比较诗学的经典之作,出现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文章及其著作。
中西诗学的诞生是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碰撞、冲突与融合后的产物。钱先生通过引进他山之玉与借邻壁之光,阐明中国文学的实际问题。钱钟书曾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基本规律。”他在《谈艺录》中明确表达了“比较”与“求同”的意识,而且将中西方异质文化比较中常用的引证法发挥到极致,其引证材料跨地域、跨时间、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其广泛程度超过了我国当时任何一部诗学著作。同时,钱钟书在《谈艺录》、《七缀集》、《管锥编》等著作中中始终坚持了中国诗学的主体性立场,其立论的出发点与最后归宿均植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对“五四”以来出现的盲目追随西方文化的倾向是一种矫正。
钱钟书的著作中有无数例子说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里的 “心理攸同”指的就是共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体制形式。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确认其学术的研究格局,是因为他自身有着一个坚定的学术观念,那就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古代或是现代,作品都具有共同的“诗心”和“文心”。在深层的人性和艺术的本性方面,中西方学者文人之间都具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可以对话和沟通。钱钟书文论诗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是自觉融中西为一体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其学术的基本研究范式就是要“取资异国”,“颇采二西之书”,通过互参互照,“以供三隅之反”。钱钟书先生对人类“诗心”和“文心”沟通的研究,这正是比较文学的价值目标的体现。
钱钟书具有一种独立不倚、绝不随波逐流的学术品格,其著作也处处彰显了他超凡的理论勇气与自由精神。他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采取了极为融通的立场,既广采博取、欣然接纳其他文化之所长,力图打破一切不同文化之间的壁垒和界限,又不盲目追随、崇拜西方。他的著作中既流露出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豪,又有着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以及反思能力。钱钟书能够将中国文化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精神归宿,理智地对自身文化存在的弊端进行尖锐地批判与冷静地剖析。正是因为这种通达包容的学术立场以及广博的中西方文化视野,钱钟书的著作不仅成为比较诗学的经典文本,更是成为其它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范本。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史》.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
[2]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蔡宗齐.《比较诗学结构:中西文论研究的三种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陆文虎.《打通而拈出新意——论钱钟书的学术贡献》.《人民日报》,2011年第7期.
[6]钱钟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7]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杨乃桥. 《比较诗学读本》,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9]张隆溪.《钱钟书论比较文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