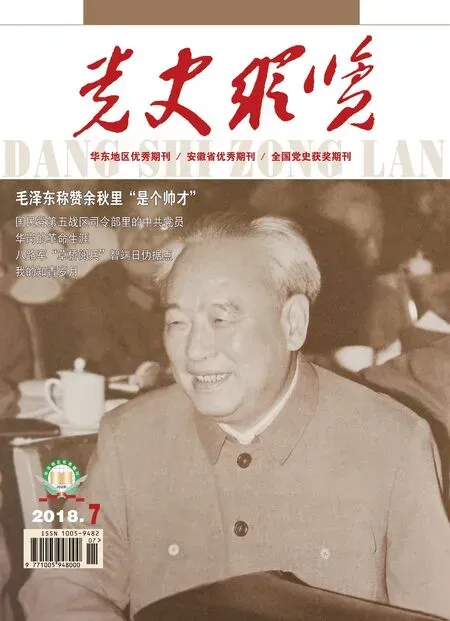改革开放解放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的人生
○秦九凤(江苏)
我原本是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席桥镇三里村第二居民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成分是下中农。
我家祖祖辈辈中没有一个人识字,我一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读了点书,直至上了初中。1960年暑后,我被淮安农业大学录取,被分配在农学专业六〇一班学习,学制5年。那时候我发奋苦读,以期毕业后能当好新中国的农业科技人员。可天有不测风云,1961年,因为天灾人祸,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淮安农业大学被停办。我原来憧憬当农业科技人员的梦想破灭了,只能回到老家当上一名普通的农民——那时叫人民公社社员。我从初识几个字起,就爱写点小东西,新闻、小故事、田头说说唱唱什么的都喜欢写。为此,1957年我还在读小学时,就开始在当地报纸《淮安报》上发表新闻作品,1963年就当上了《新华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但是,组织上内部掌握我社会关系不好的阴影却总罩在我的心头。当年学校停办后,档案没人管问,便交由本人带回。而当我将密封着的档案袋带回家后,送到哪里也没人收——一个公社社员还要什么档案?最后我自己拆开来看时,发现学校给我的最后评语是:“该生学习认真,思想进步,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且屡打入党申请报告;但该生社会关系不好,政治上基础不纯,应有选择地控制使用。”
这袋个人档案在我家里放了约1年之后,被我所在的席桥人民公社派人来拿走了。不久,中共淮安县委组织部下文任命我为席桥公社三里大队会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就被群众批斗了。社会上的造反派说我是“臭老九”,有“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然,“不纯”的社会关系也是导致我被批斗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造反派们也直接说了,批我“臭老九”的理由是因为我喜欢写写画画,目的是为自己扬名(报上刊用)、得利(拿稿费);还有一条就是我戴近视眼镜,那是1960年我初中快毕业时因学习成绩较好,眼睛却近视得看不清黑板字,于是,学校免除我一个学期的学费共计4块半,让我配了一副眼镜。可是那些造反派们可不管这些,他们在贴大字报和批斗我时都是十分尖锐地批判说:“大家看,我们贫下中农有几个年轻人就戴眼镜的?”“这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弄得我啼笑皆非而无可奈何。
当时我心想,作为一个“政治基础不纯”的人,在那样一个极“左”政治环境笼罩下的社会是什么希望也没有了。但我唯一“死不悔改”的是,仍一如既往坚持写作。尽管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稿不让署自己姓名,也无分文稿费。相反,我还曾因为将写好的稿件拿去县里和公社相关部门审阅而“旷工”被罚过工分。此后,我当过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前后当了2年半,学生家长、同行、学生都说我授课认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教学能力,但由于前边说的种种原因,结果又遭“下岗”。后来,我又当过铺路工、治水工(那时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水利战士”),不过这些都是些临时活,忙乎几个月还得回归到“一亩三分地”上。
虽然我不怕种地,能干我们那里所有的庄稼活,但一家人生活总是很艰难,而且我家比当时的同龄人家庭还要苦一倍。为啥?因为我在外读书,结婚时间比同龄人晚了一两年。也就是说,我是1963年元旦结婚的,而当时是生产队集体所有制,上边规定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划分时间是1962年12月31日,这样我妻子就分不了自留地。加之结婚后我们又陆续生了3个孩子,这样一个五口之家却只有我一份自留地,盖上三间两厨的住房后,连种一棵蔬菜的地方也没有,更别说种粮食作物了。而那时又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自留地丈量后,30年内不准改变。因此,我再勤劳,再节俭也无济于事。
记得1973年秋初的一天,当民办教师的妻子下课回到家后,我也从地里干完农活回家了,而家中却什么充饥的糠菜都没有,3个幼小的孩子睁大着眼睛,用期待的目光盯着我们。无奈的我只好让妻子去庄上找邻居借粮,让大女儿找生产队长到集体社场上预支麦芒衍子,到正式分配时再扣除。我自己则从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伤病员断粮后去阳澄湖上找鸡头米(即芡实)充饥这件事得到启发,握着一把割草刀跳到水沟里,寻找那些野生的鸡头,把鸡头的茎秆割下来,再剥掉外皮充饥。
鸡头浑身(茎、秆、叶)都长着尖锐锋利的芒刺,割鸡头秆时,我满身都遭到芒刺,连脸部也不能幸免,全身痛痒、胀痛,完全是个“如芒刺背”的感觉。我原来打算,如果妻子借不到粮食,女儿又支不来烧火草时,全家就只能以剥掉皮的鸡头杆充饥了。所幸的是,那天借到了一点点粮食,也支来了一点麦芒衍子,这样,用一点米和剥掉皮的鸡头杆搅拌在一起整整煮了一大锅稀粥,一家人才充了几天饥。类似这样的生活困难,恐怕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也是那个时代我们国家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吧。
1975年,邓小平复出抓整顿,我感觉到全国城乡形势在悄悄变化,心中暗暗高兴。这时,机会果然来了!公社电影队缺一名放映员,放电影总得要有点文化知识才行嘛,而当时在我们公社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学历是打灯笼也找不到几个的。于是,我被通知到公社电影队上班了。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晚上放电影,白天写报道,每月从放电影的报酬中拿24元钱工资。我知道这是公社党委的“巧妙”安排:既不能名正言顺地给我一个公社党委新闻报道员的身份,却能利用我擅长文字的这点特长。然而,我进入电影队还不到半年,邓小平就又被批判了。我又听到公社大院里有人议论,说什么使用秦九凤是犯了立场、路线上的错误等等,使得我见了人都不敢抬头。但酷爱写作的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还是一边放电影一边没日没夜地写作。我的用稿越来越多,用稿范围也越来越大,终于没被辞退回家。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心中也日益感到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左冰”即将溶化,政治上也在逐步觉醒。当时,有一篇报道稿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文化大革命”后期,极“左”思潮在集市贸易上推行东北黑龙江“哈尔套大集”的经验:农民赶集也要“革命化”,大家排起方队,敲起锣鼓,还要朗诵毛主席语录……而且为了彻底杜绝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明令一个公社只能有一个集市。偏偏我所在的席桥公社当时有两个集:席桥和马厂(南马厂乡是1986年才划设的)。于是,席桥公社的马厂集便被列入了封禁之列。这样,每到马厂的逢集日,席桥公社党委都要派负责人带上一帮村组干部和民兵,抢先上集赶走那些赶集的群众。对此,农民群众十分反感,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们巧妙地强行“簇拥”着公社去指挥封集的领导人,一直把他“拥”到街边水塘里,弄得那位领导一身泥一身水的,特别狼狈难堪。就这样,公社每集都去“封”马厂集,群众逢集却照样还去赶,而且有时在古十字街,有时又转移到堆堤上,像捉迷藏似的,把封集的人搞得焦头烂额,最后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见此状况,我以为公社领导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了,就写了一篇通讯——《百年老集又开放了》。稿件写好后,我请公社党委书记审稿,他一看就说:“这样的稿子我怎么能同意你发?群众赶马厂集是违背江苏省革委会通告的。现在我们没去封,是我们公社人手不够,只是暂时的,具体还要等上边的文件呢!”我没有灰心,又跑到淮安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当时的报道组组长陶溶看了稿子说,这篇通讯写得不错啊,根据目前“气候”,我看可以发。他随即让宣传部秘书王伯文盖章并签上“同意发稿”的字样,那是1978年11月间的事。就在我忐忑不安地等待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读了公报,我十分高兴,因为不管这篇稿件用不用,在政治上我被批斗、被迫害的事是不可能再出现了,也就不会给同意发稿的领导带来麻烦了。1979年1月23日,《新华日报》二版用较大号的字体刊用了这篇通讯,还让画家胡博琮配了插图。当地群众见到报纸后,反映很强烈,特别是马厂集上的人,他们拿着报纸奔走相告,有的人还放了鞭炮,敲起了锣鼓。当时集上一位90多岁的朱二先生对笔者说,这是马厂开集一百多年来最热闹的一集,这是民心啊!


作者所获荣誉证书
打那以后,我就被县委宣传部、县文教局等单位长期抽用了,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无论是采访还是写作,我几乎都是没日没夜地干。在刘少奇没有被平反前,我写作的《加强青年的社会公德修养》一文刊登于1979年4月19日《新华日报》的头版上。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被批为“黑修养”,道德修养这类话题就没有人敢再提了。所以当时有人看了报纸,一边夸我“写得好”,一边又说“秦九凤的胆子忒大了”!
当然,我不会满足,而是趁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继续前进。不仅写新闻稿,还与朋友、同事们合作写书。1984年到1987年先后在河北人民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承恩的传说》《关天培的传说》和《周恩来童年在淮安》等书。1985年,我44周岁时居然被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人才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所以现在我常常想,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我思想的解放,而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也改变了我一个普通农民的命运。这40年来,我已在海内外的《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党的文献》《百年潮》《党史纵览》《世纪风采》和美国《侨报》、加拿大《华侨新报》、新加坡《南华早报》、香港《大公报》等四五百家报纸、杂志上用稿4600多篇(次),在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出版了20多本书,先后被人们称为“新闻专业户”、地方史研究专家和研究周恩来的专家等等。省市区有关部门先后授予我自学成才奖,优秀知识分子、科教兴区排头兵称号。2012年,72岁的我还获得了江苏省委宣传部表彰的“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称号,2013年又被评为淮安市委、市政府“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2016年获淮安区十佳魅力老人(博学)等等光荣称号。2001年我就退休了,现在还担任着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理事、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的常务理事、江苏省委老干部局老干部党校的兼职教师,淮安市政协特约文史委员等20多个社会职务,为省内外机关、大中小学、企事业单位和工厂、农场以及驻军等作学习周恩来精神的报告近800场,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和听众的热烈欢迎。我的这些成绩和荣誉不正是我们党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给我带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