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的开始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陈独秀《敬告青年》
一九二八年,现代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小说的叙事起始于一段旅途:年轻的主人公在黎明时分起身离家,沿着吴淞江泛舟而下,前往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这段旅途掀开了他人生中一个新篇章。虽然他乘坐的小船笼罩在漆黑的夜色中,他却感觉自己正沐浴在光明之中。他感叹:“新生活从此开幕了!”此时此刻,他幻想着一切行将发生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富有寓意的时刻。旅途和梦想、热忱和允诺、希望和未来,这些元素组成了有关青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主线的基础。
《倪焕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展现现代青年成长经历的重要长篇小说。在此,我强调倪焕之人生旅途的开端,为的是试图召唤作家叶圣陶以及此前此后几代中国作家寄予“青年”的丰富含义:在二十世纪中国,作为重要象喻的“青年”,与国家和现代的观念紧密联系。我致力于研究青年的象征意义的话语构造,以及探索这些意义如何塑造有关青年个人成长的现代中国小说叙事。我的工作是文化史和小说分析的结合,接下来,我将在中国不断变化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下,探讨“新青年”和“少年中国”这些理想形象在小说中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读解他们在小说形式中呈现的多姿多彩、难以简单归纳的丰富内涵。

叶圣陶《倪焕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倪焕之》的故事情节大抵是基于叶圣陶早期在新式学校当老师的个人经历(叶圣陶做教师的早年生活,请见其子叶至善所著《父亲长长的一生》)。主人公也是一个年轻的教师,努力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他的远大理想是通过教育将其学生(以及自己)塑造成为一代“新青年”。最终,他希望发起一场全面社会变革,通过引进新思想、启蒙群众,组织变革甚至煽动革命。在旅途的开始,倪焕之激情澎湃,充满抱负,在心中构想远大前程。他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小船中,被自己内在的活力鼓舞着。这样的开端,借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语句,构成了“一个思想框架、一种工作、一种态度和一种意识”,从而成为“最为重要的活动”(萨义德《开端》)。至此,倪焕之对于自己正处在人生新开端的自我意识,成为他心理成长中最具有革命性的部分:对传统感到幻灭,渴望改变,他期待着一个从本质上不同于过去的未来。
通过将倪焕之的热忱与其旅伴兼好友金树伯的精明做一个对比,倪焕之的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个性被进一步凸显。两个朋友多年不见,在旅途中展开一段愉快的对话。然而在某个瞬间,我们的青年主人公突然发现他的朋友金树伯已然成为一个“中年人”:“老练,精明,世俗,完全在眉宇之间刻划出来。”(叶圣陶《倪焕之》)我们在小说早先部分得知,倪焕之比金树伯“年轻”,但是对于后者明显变“老”了的发现,其实还有更深的意义,因为比起生理上的老化,树伯态度上的老态更多反映出其思维方式的狭隘。这两个朋友对于“理想”的意义,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倪焕之在说出这个字眼时,“眼里透出热望的光”,而金树伯却将理想的意义简化为“弄着玩”。倪焕之对于“弄着玩”三个字颇为不满,他“想树伯家居四五年,不干什么,竟养成玩世不恭的态度了”。也正是在此刻,倪焕之的内心涌入一种异样的情感:树伯变“老”了。在倪焕之的脑海中,青春与热情和理想密不可分,年轻人应当在自己的生活,以及为国家变革而进行的斗争中,时刻准备着打破传统并拥抱新的开始。因此,对于作者叶圣陶,他是利用自己笔下人物来为新青年一代的精神发声,青年不仅是一种年龄上的类别,而是体现了一系列崇高理念的象征:新颖、进步、国族重获青春。
只要将倪焕之的人生故事和叶圣陶的生活经历略做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倪焕之的这段旅途,大概发生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中期。也就在这个时候,《新青年》杂志开始在知识读者中发生一定的影响。《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期刊,对中国传统发动的全面文化战争,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等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变革,都在这本期刊上发生(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这本由陈独秀于一九一五年创办的杂志,使得“青年”成为流行的文化形象,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中流砥柱,同时也在启蒙知识分子中创造了一种青年崇拜,他们将对中国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正是这本杂志以及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中国青年的新身份—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的开篇《敬告青年》中就大声疾呼(本文开篇所引段落),青年时期不仅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更是改变社会的新鲜力量,“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有趣的是,陳独秀把新青年比作细胞的隐喻,暗示了一种有关重获青春的科学见解;强调为了国族的文化改革必要性,仿佛这就如同身体的新陈代谢自然而然的必要过程(罗鹏[Carlos Rojas]《经典与吃人》)。

《新青年》封面,作者拍摄
以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青年具有代表性意义这一点,无论就科学还是政治而言,都是反传统的,正如舒衡哲所述:“在中国这样以年龄作为智慧根源的环境下,把青年当作最珍贵的社会创造力的源泉,便意味着要推翻传统。”(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通过“新青年”的崇高形象,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向传统宣战,开创了一场文化革命,这场革命由于对于国族青春的活泼想象而蓬勃发展。国族青春的想象第一次出现在晚清改革派的政治思想中,此后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中占据中心地位,并且在中国几次现代转型中不断演变。
《倪焕之》的发表时间(1928),距离凝聚在“新青年”形象中辉煌的新文化运动过去已经十年:青年男女们听从启蒙的律令,拥抱西方化的科学思想和民主理念,力求将理想付诸直接行动。倪焕之这个形象是新青年的典范,他“试图在他人生中教育、爱情和政治这三个舞台都注入新的活力,但每次结果都差强人意”(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他梦想过、斗争过、胜利过,小说的后半部分又呈现他的怀疑、妥协,最终失败,继而悲惨死去。小说结构包含着希望与幻灭、理想与行动、渴望与绝望的轮回。情节展开为主人公实现其理想的过程,继之又被挫折、失败和致命危机所袭扰。这样的情节设计,在讲述青年心理发展的现代中国小说中将一直持续下去。《倪焕之》追述了主人公一生的旅途,但最为美妙的时刻仍是故事的开始,那时的倪焕之忘我于青春的魔力,受到青春的诱惑,要在这世上找寻自己独一无二的道路。在小说后面的部分,倪焕之不停地试图在人生不同阶段重新发现这样的新开端,或者简言之,他的奋斗是在延长那“伟大开端”蕴含的能量。
这样一部小说,对旅途的开端投注非同寻常的意义,好似歌德笔下威廉·麦斯特的离家出走,巴尔扎克描绘外省青年前往巴黎追逐梦想,以及狄更斯那些想要成长为绅士的年轻人所怀有的远大前程;亦或借用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话来说,这一系列的小说构成一个传统,描写那些“从一开始就对于生活有着巨大要求,并对生活的复杂性、未来的期许充满惊奇感”的青年经历成长、精神发展(特里林《卡萨玛西玛公主》)。这是一种被称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特别类型的小说,叙事聚焦于青年的心理发展—对于自我的教养、个性的塑造以及在历史运动的背景下寻求自我理想的实现。对于许多哲学家和文学家来说,成长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现代小说的基本形式:巴赫金(M. M. Bakhtin)将其看作现实主义小说最新、最高级别的发展(巴赫金《成长小说及其意义》)。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在其中看到黑格尔式主体自我实现的情节展开,并且以此为例来说明现代小说叙事的内在形式(卢卡奇《小说理论》)。而弗朗克·莫雷蒂(Franco Moretti)则从文化史的角度,将其定义为现代性的“象征形式”(莫雷蒂《世界之道》)。
作为一部成长小说,《倪焕之》通过一个试图改变自身生活和国家命运的新青年的旅途,表现个体发展和社会改革的现代构想。倪焕之仅仅是现代中国小说中诸多青年主人公最早的一个。现代中国小说兴起于五四运动之后,将新青年一代的生活置于为国家未来而斗争的舞台中央。在倪焕之的背后,还有一系列中国作家创造的青年主人公,最著名的例子包括梅行素(《虹》)、高觉慧(《家》)、蒋纯祖(《财主底儿女们》)以及林道静(《青春之歌》)。倪焕之青年形象的背后,闪耀着“少年中国”灿烂、崇高的光辉。少年中国是现代中国国族主义话语的核心象征符号,表达了对于国族青春孜孜不倦的渴求。这也是中国二十世纪许多改革和革命的总体目标。
《少年中国》从一个青年在黎明踏上旅途作为开头,进入到一个“青春”的世界。青春(green spring,youth,young),这个一度充满了中国传统意味的词汇,继而在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宏伟的象征符号,始终占据在塑造了中国现代性的文学形式和知识话语的中心地位。《少年中国》一书追溯青春话语在现代中国的起源及发展,探讨将个人成长融入国族青春的现代小说,以及其中的青年形象。这是一个航向美丽新世界的旅途,寄托了希望和未知,这也是一个关于少年中国的故事,包括它的闪亮与阴影。
在这本书里,我将讲述许多旅途的故事,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每一章都以一个历史人物,或虚构人物的旅途开始,就像叶圣陶前往甪直的旅行,以及他在小说中描写倪焕之对于新生活的巨大期待。《少年中国》的书页里,延续着进入中国“青春”世界的旅途,而在中国从古老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中,我们探询在话语、文化以及小说的层面上青年形象如何被构筑。《少年中国》总共七个章节,每一章各自聚焦于自清末到民初,直至当代的青春话语及其小说形象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面向。
第一章是对现代中国青春话语的一个总体介绍,也同时对中国成长小说的文化分析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在这一章中,我首先对现代中国青年話语做一个总体描述,探究核心词语的语义学内涵。我的分析特别着重于少年中国话语源于“重获青春”(返老还童)这一独特的观念:返老还童,这想象先使晚清作家们迷恋不已,此后使得对传统的重新评估,以及青年对现代性的象征,都变得意义更为幽深。我以历史和文化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成长小说,这个叙事类型既能体现,也能解构各个时期青年身上的文化和政治象征意义。正如《倪焕之》所展现的那样,这种文学类型通过在历史中实现理想,来探询青年的意义。其情节是为了让誓言成真,但却时常伴随着自我与社会、理想与行动、对青年的规训与其难以驯服的活力之间的冲突。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 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第二章将“老少年”作为一个关键形象,以及概括晚清青春话语复杂、多义的内涵。在这章中,我讨论晚清知识界试图将古老传统改写为现代思想,特别分析了梁启超有关“少年中国”的话语与他对复兴中国传统的复杂思考之间的关联。吴趼人《新石头记》(1908)中“老少年”的形象是文本分析的核心。“老少年”作为话语和文化重构的产物,是一个突出的象喻,他反映出晚清传统与现代难以轻易协调的文化征候。“老少年”首先体现中国传统的重获活力,就像吴趼人小说中建立在中国传统美德之上的未来中国的乌托邦景观。但是,“老少年”仍有一个微妙且暧昧的意义,这特别体现在《新石头记》中复活的贾宝玉身上。作为古典文学中的青年偶像,贾宝玉从传统家庭中被移植到未来世界:他渴望思想进步,这一点使得吴研人的小说有了成长小说的动力。然而讽刺的是,贾宝玉的成长,在他遇到小说里那些已经复活传统、建立了儒家新中国的老少年后就中断了。假如贾宝玉也被视为“老少年”,成长小说就变得问题重重,贾宝玉的青春是没有时间性的,但正因为它并不是历史进步的一部分,所以它也毫无意义。在小说中,他是没有归宿的人物,深陷于传统和现代之间。贾宝玉所揭示的这第二个层面的“老少年”的悲哀、空虚、失落,指向了晚清时期正在兴起的青春话语文化的不确定性。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三章探讨新青年一代的成长经历如何构筑中国成长小说,例如叶圣陶的《倪焕之》那样。本章中,我通过对于《新青年》杂志所建构的青春话语的历史研究,来分析启蒙理想的文化表现。我阐释“新青年”作为启蒙文化的传递者,启发知识青年进行自我塑造。《倪焕之》以回顾的方式叙写新青年的个体发展心灵史,建立现代中国成长小说的经典情节,主人公逐渐投入现实行动,预期实现其崇高的理想,然而,这一情节却总是被打断,一系列的历史坎坷使青年的理想暗淡下去,陷入希望与幻灭的无限轮回。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政治气候的转变,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左翼化为标志。受到启蒙的“新青年”被更加激进的“革命青年”所替代,成为这个时期文学想象的核心形象。第四章主要聚焦于茅盾的早期小说《蚀》三部曲(1927-1928)以及《虹》(1930)。作为对《倪焕之》中诸种问题的回应,这两部小说力图对新青年一代成长小说做出一种意识形态矫正,在青年成长叙事中加入目的论修辞法(teleological rhetorics),从而使叙事朝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发展。这一章首先分析了《蚀》三部曲中的叙述模式和美感模式,接着讨论茅盾在其文学想象中用来将时间“历史化”的北欧女神神话,这最终使他在《虹》中建立一个线性成长故事,以此唤起历史进步的意义。我对这部性别化的革命成长小说的分析,特别关注叙事中的个体自觉、性感以及目的论问题中那些复杂与晦涩的方面。
巴金有可能是五四时代之后对青年人最有责任感的代言人。第五章聚焦于他早期的无政府主义小说,试图阐明其小说中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和青年崇拜之间在思想、伦理以及审美上的关联。巴金运用“情节剧”的方式,将青年的牺牲转化为“生命开花”的审美过程。这个美学意象标志了巴金终极道德观的建立,并且孕育了其大部分早期青年小说的基本情节,包括《灭亡》(1928)、《新生》(1932)以及《爱情的三部曲》(1931-1933),还有他最著名的小说《家》(1931)。这并不是一种发展式情节,而是指向某种需要无条件自我奉献的道德启示的瞬间。因此,巴金创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成长小说,其高潮在于充满青春活力的主人公自我牺牲的那一刻,也从而中止了青年的发展,抑或实现了以彻底消亡而完成自我转变的目标。
在一九三七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青年的旅途转向一个截然不同的时空体中。他们在战时的旅途是一种放逐,是强制的迁移:他们不再走向五四时期被誉为启蒙胜地和现代文化殿堂的大都市,而是开始在地理和思想上都反向而行。第六章描写了青年走向内部的旅途。路翎《财主底儿女们》(1945-1948)和鹿桥的《未央歌》,都将青年的旅途导向内心,因而尽显个体主观性的复杂与矛盾的方面。他们走向内部的旅途,不仅是在地理上通向中国大后方的蛮荒秘境,更是在精神上走向那充满了矛盾的个体的焦躁不安的内心。
第七章通过阅读两部中国当代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和王蒙的《青春万岁》(1979),试图理解当时的青年文化政治。《青春之歌》可以說是一部社会主义成长小说,即用一种特殊的叙述成规去引导年轻读者去进行自我塑造,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成长小说。而《青春万岁》则并未追溯英雄人物的完整人生历程,而是描绘了青年无法安顿、狂喜不已的情感,从而打破了有关青年按部就班的成长叙述。

〔清〕吴趼人《新石头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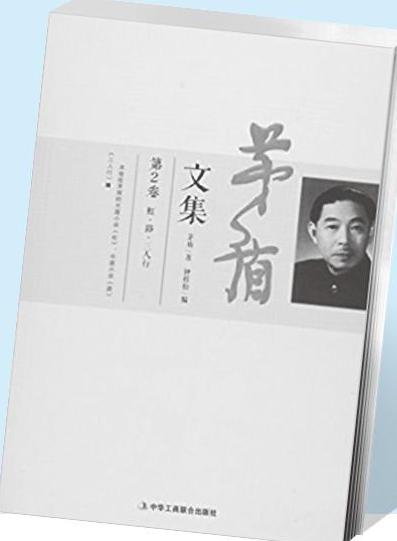
《茅盾文集》第二卷(《虹》《路》《三人行》)中国工商联合会出版社2015年版
在结语中,我就当代中国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做了简短的讨论。从二十世纪末到新世纪,少年中国的梦想依然活跃。然而,梁启超的梦已经被新人类的想象替代了。当代青春小说告别历史,描绘享乐主义的生活,沉溺于小世界的虚华,追求另类现实的自由。这或许是以偏概全的说法,但或许揭示出当代青年的美丽新世界。倪焕之在其旅途开端所迷恋的那光彩夺目的青春景象,或许仍然闪亮在新千年的青年心中,只是成长小说中那难以承受的沉重,所有的悲伤和痛苦,都在重新调整的通往虚拟世界的旅途中被遗忘和抹平了。
《少年中国:国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宋明炜著,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