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宗教徒的“朝圣”之旅
郁隽
一、“说走就走”还是“不得不走”?
如今,我们崇尚所谓“说走就走”,但这本身就是禁锢的产物。绝大部分人并不能说走就走,而几乎都是不得不走。

电影《朝圣之路》海报,2010
汤姆是一位做事谨慎的牙科医生,他生活在美国的一个小城镇里。由于职业收入优渥,经济状况不错。除了看门诊之外,汤姆喜欢和朋友打打高尔夫,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了一个噩耗—儿子丹尼尔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上的比利牛斯山遇到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不幸罹难。哀痛之余,汤姆要去法国取回儿子的遗物。后来他才知道,丹尼尔生前正在走一条“圣雅各之路”(El Camino de Santiago / Way of St. James,又被称为“圣地亚哥之路”)—从法国南部一直到西班牙西北部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这是美国电影《朝圣之路》(The Way,2010)中的情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汤姆的影子—随遇而安、按部就班,虽然我们很少意识到,消磨人的绝非是什么大风大浪、大起大落,而恰是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

朝圣之路上的汤姆(电影《朝圣之路》剧照)
汤姆曾经对丹尼尔说过一句大实话:“你知道,大多数人不可能那么潇洒,背起包就把一切抛在脑后。”直到有一天,生活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汤姆在认领了儿子的遗体和遗物之后,突然想,不如去走一下丹尼尔想走的圣雅各之路。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汤姆虽然是一个名义上的天主教徒,但并不是一个有宗教感的人。在动身前往欧洲之前,他来到家乡的教堂,临别时,神父出于安慰而问他:你愿意和我一起祈祷吗?汤姆回答说:为什么?
即便是为了拒绝,人终究还要问“为什么”。
二、圣雅各之路
汤姆是一个理智极为强大的人,他对宗教、信仰、朝圣之类的事物似乎天然地有所抵触。他习惯于对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进行计划和规划。神父邀请他一起祈祷,在他看来就是那种“无意义”的小举动。我在汤姆身上再度看到了现代人的尴尬—他们总是将自己的生活切割为一小段一小段的碎片。对每个碎片都采取锱铢必较的态度,试图达到某种“最优”状态;然而,对于自己人生的整体,却极少思考其意义或价值。很多最优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并不能构成一个有意义或有价值的人生。就此而言,我们不就是微观战术极高明、而宏观战略极昏庸的人吗?
圣雅各之路来源于天主教历史上的一段故事:传说公元四十四年,十二使徒之一圣雅各(St. Jacob / James,西庇太之子、使徒约翰的哥哥)在耶路撒冷被希律王所杀,成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个殉道的使徒。他死后,他的追随者们用船载着他的遗体,准备去往今天叫作圣地亚哥的地方埋葬。结果船到西班牙海岸时,突然遭遇风暴,船覆人亡。圣雅各的尸体也沉入大海。但是不久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圣雅各的尸体被海浪冲上了岸,包裹在一堆扇贝中间,而且居然完好无损。从公元九世纪开始,圣地亚哥就逐渐成为了天主教世界除了耶路撒冷、罗马之外的第三大朝圣目的地。圣雅各也被视为西班牙的守护神。如今,这条路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严格来讲,圣雅各之路并不是一条路,而是很多条路线的集合。不过它们的终点都是位于圣地亚哥的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其中最有名的一条线路是从法国南部,翻过比利牛斯山,然后沿着西班牙北部大西洋海岸线一路向西,全程有八百多公里。
很多人为了走这段圣雅各之路,要提前几年作计划,规划路线,准备行囊等等。于是很有可能,圣雅各之路再次成了人生中那一小段极度合理化、精心雕琢的“行程”。
圣雅各之路上,每到一处都有“庇护所”,也就是供朝圣者过夜的小客栈。庇护所的设施很简单—大房间里放着好几个上下铺,非常类似欧洲各地的青年旅社。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现代的青年旅社系统在历史上演变自朝圣者的庇护所。朝圣者需要凭着自己的朝圣手册,才能入住庇护所,而且通常不允许在一个地方连续住两个晚上。这似乎暗示着,朝圣者必须“赶路”,不得停留,好似时间一样无情。

电影《朝圣之路》剧照
三、只有宗教徒才“朝圣”?
只有宗教徒才朝圣吗?只有宗教徒才追求人生的意义吗?只有通过朝圣,才能獲得人生的意义吗?观看影片时,心头不免生出不少问题。
一开始,汤姆一个人孤独地走路,但走着走着,他遇到了几个一同走路的人:尧斯特来自荷兰。他是一个率真乐天的大叔,但老婆嫌弃他吃太多、太胖,所以让他来走路减肥。一路上,他依然管不住自己的嘴。萨拉来自加拿大,她沉默少语,一有机会就拼命般地抽烟。后来汤姆才了解到,她在家中遭到丈夫的家暴,还经历了堕胎,出来走路是一种逃离。据萨拉自己说,走圣雅各之路是为了戒烟。杰克来自爱尔兰,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最近遇到了瓶颈,什么都写不出来。他自己说,年轻时想成为叶芝和乔伊斯,但毕业后写了二十年的旅行杂志文章。虽然赚了不少钱,但感觉没有意思。他来走朝圣之路,还带着手机,出版商每天都打电话来催他交稿。他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希望旅途能够打破创作的魔咒,有一天忽然茅塞顿开,可以填满这个笔记本,写出稿子完成出版合同……似乎,每个人来走路的目的都不单纯。
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来朝圣的。这四个人都处在人生的转折点,或是处在一种非常状态、一场危机当中。当他们走完了一段旅程之后,他们还是原来的自己吗?这不是一个忒修斯之船式的问题,而是问,他们还会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吗?
四、现代人的鸡汤刚需
“心灵鸡汤”是这个时代人们的刚需。“心灵鸡汤”让喝的人感觉到某种暂时的愉悦,但是喝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依然一无所获。“说走就走”似乎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无所畏惧的人生态度,但其实内容空洞,什么都没有表达。
然而,也要承认,之所以心灵鸡汤盛行,恰是因为思想市场上缺乏必要的供给。在现有的大学系科分类中,并没有“人生哲学”这个项目。这并不是说,哲学不可以给人生以一定的启迪和指导,而是说,哲学并不首先承诺确保对人生困境作出有效的回应。换言之,每个人应当为自己的人生问题寻找答案,而并不一定存在一致的应对方式。这里倒也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一个人的人生与另一个人的人生是否具有可比性和可通约性?倘若没有,那么你试图拷贝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来获取自己的幸福,大概就是在缘木求鱼了。反过来,很多心灵鸡汤大师在售卖他们的鸡汤时,都在反复暗示,人生难题存在统一的解决方案。其实,他們并不知道你是谁、你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他们无非是在售卖一副号称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已。你是否相信,参差多样乃幸福之源?甚至可以再进一步问:人生最终的目的,仅仅是追求幸福吗?
人最不容易对谁保持诚实呢?是自己。很多人都在扮演若干个“人设”—学生、职员、老板、儿女、父母……这些都是社会预设的功能性角色,但很少有人可以直面“自己”。或者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独一无二。对很多人而言,定义自己成了生命中无法承担的重负。有些人宁可选择一种“量产”的人生轨迹,或者让别人给他一个“现成”的生活—一套成功与幸福的模板。

《文化和价值》[英]维特根斯坦著黄正东 唐少杰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有人觉得他解决了人生的问题,并且想要告诉自己,一切现在都变得简单了,那么他只要想一想自己过去没有发现这个‘答案的时候,便会意识到自己错了;而那时候也照样生活,现在发现的人生答案就过去的生活来看似乎是偶然的。”(《文化与价值》)人生的意义并不是一颗药丸,一个装备,或者一套外挂,一旦拥有就一成不变了。似乎它是伴随人生全过程的一种追问。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被笑称为门卫的经典三问。而大家并不情愿把它们变成第一人称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错讹:好像每个人都对外部世界拥有海量的信息和知识—每天的家长里短、人情世故、股市走向、国际局势……对自己却没有充分的了解—缺乏自知。学术研究和传媒仅仅关心前者,而并不在乎后者。学术与人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五、永不停止的陀螺
“也许,我过去生活得不对头吧?”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这个想法。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又为什么不对头呢,我做什么都是兢兢业业的呀?”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便立刻把这唯一能够解决生死之谜的想法当作完全不可能的事,从自己的脑海里驱逐掉了。
现代人每天的生活就像陀螺一样。他需要保持不断地旋转,才能保持平衡不倒。但是,陀螺旋转的动力并不来自于它自身,而是来自于外界—考核、收入、福利、升职、虚荣、攀比等等。但人是一个有意识的陀螺,即便是在不由自主地旋转时,仍会时不时地问一下:我为何而旋转?

《伊凡·伊里奇之死》[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许海燕译 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
电影中,汤姆问一个当地的老妇人:你走过朝圣之路吗?她回答说:从来没有。年轻的时候总是太忙,而现在,我又太老了,太累了。如果没有受到外部的干扰,每个陀螺都会平稳地旋转下去。但是,有的陀螺在空前的无聊感中,在那种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中,感到无助、疲劳、心累……一阵清风吹来,陀螺踉跄一下,继续旋转。或是更为严峻的挑战、痛苦、虚无随时都可能降临。面对各种各样的机缘,人生就被撕裂了,或说是被打开了。最柔软和薄弱的地方暴露了出来。突然之间,以往所有的人生经验和规划都没有用了。
一道闪电击中了陀螺,激活了人心。
影片的主人公汤姆是一个标准的“好人”。或者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表达,是一个标准的“常人”(das Man)—几乎不会去打破陈规,追问本真的意义问题,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享受“沉沦”。他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在儿子丹尼尔意外去世之前,汤姆的生活全都在他的规划之中,一切井井有条,毫无意外。
然而,丹尼尔死了。“好人”汤姆遭到了当头棒喝。
如果不是因为儿子的意外,汤姆是绝无可能去走圣雅各之路的。即便是在途中,他依然是那么循规蹈矩、克己复礼。唯独有一次,因为看不惯爱尔兰作家杰克,汤姆在酒后和他大吵了一架。只有酒精可以让他放松自我。
六、生活不是“照单点菜”
汤姆在开始行程之初,身上带着浓重的“美国气质”—对世界大致了解一点,但却都是按照美国人自己的方式来裁剪世界。凭借着对西班牙饮食的有限知识,他想在餐厅点一份tapas—西班牙常见的前餐小食,通常是在烤面包片上面加一点蔬菜、火腿、酸奶酪等。这是一种他自以为绝对安全、不会出错的点菜方式,然而女招待却告诉他,tapas是西班牙南部的食物,这里没有。
一个人不出门的话,就会永远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那里应有尽有,唯独没有意外。真正想要敞开自己,拥抱世界,绝不可能是享用自己已经熟知的食物,而是放开胆子点一份à la carte,也就是厨师按照自己特长和本地特产而定制的当日例菜。生活并没有给你预备好一份循规蹈矩的菜单—开胃菜、主食、甜点和饮料。生活需要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坦然。
影片一再让人重新思考这种“照单点菜”的生活态度。途中在一个城市里,一个小孩偷了汤姆的包。汤姆本来已经作好准备,放弃一切找回包的企图了。不料,小孩的父亲把汤姆的旅行包送了回来,还邀请一行人一起到他们家里做客。“旅人”和“小偷”的定式被打破了。
七、未来之不确定
在圣雅各之路上,有很多“贝壳路标”。因为传说中,圣雅各的尸体是被贝壳包裹着冲上海岸的,所以贝壳成为了这一旅程的圣物,也是标志。每个城镇的庇护所门外,都有非常醒目的贝壳路标,给朝圣者指示方向,以免他们迷路。一些“驴友”回忆,甚至在远离终点两千多公里的地方,也有类似的路标。
有人发现,贝壳展开的纹路和圣雅各之路的线路非常相似:贝壳的纹路都归拢起来,而圣雅各之路最终都匯聚到圣地亚哥。在朝圣之路上的人不用作选择,向着贝壳指示的方向走,无需多想。唯一的问题是,继续走还是不走。

给朝圣者指示方向的青铜扇贝
圣雅各之路是一段方向明确的路,而人生并非如此。人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即未来的不确定性。人类使用了整个物种的力量—宗教、科学、技术等等来对抗这种不确定性,试图给未来带来某种确定的回报或者确定的轨迹,以杜绝出现“意外”。但即便如此,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占据什么社会地位,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无法彻底消除的。
我们个人也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安排”生活,即通过精确的计算。譬如有的人可以精准地安排每天坐哪一班地铁,几点几分从哪一个车厢上车,到站后步行几分钟可以抵达办公室。人们总是在寻求一个“最优解”或是“捷径”。然而,人终究不是神明,无法做到尽知。
对生活局部百分之百的理性态度,恰恰是对于生活之整体的非理性。有些人需要目标,而有些人则需要迷失。
八、底色亢奋,略带悲凉
人生有意义吗?回答是两可的—有或者没有,也可以说既有也没有,就是薛定谔的状态。每个人都欠自己一个回答: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早已经洞穿了世上的各种人生态度:“生活就像奥林匹克赛会;聚到这里来的人们通常抱有三种目的:有些人摩拳擦掌以折桂,有些人做买卖以赢利,但还有一些人只是单纯做旁观者,冷眼静观这一切。”有些人以荣誉为目标,有些人以盈利为目标,还有些人喜欢冷眼旁观。
《朝圣之路》中,萨拉问走得飞快的汤姆:这又不是一场比赛,为什么不停下来看看?而尧斯特说:他们可以骑车,那我们为什么要走?太荒谬了!杰克出于职业习惯,对遇到的朝圣者进行调查:有百分之十五的人,是为了健康而来朝圣的。
“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斯多葛主义者塞内加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并未预见到自己后来被暴君尼禄赐死的结局。在科西嘉岛流放的时候,他是一个彻底清醒的悲观主义哲学家,而不是那种怨天尤人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眼中,人生整体的悲剧性,并不在于每个具体事件的悲惨性。然而,当他离开科西嘉返回罗马的时候,他把自己哲学家的灵魂留在了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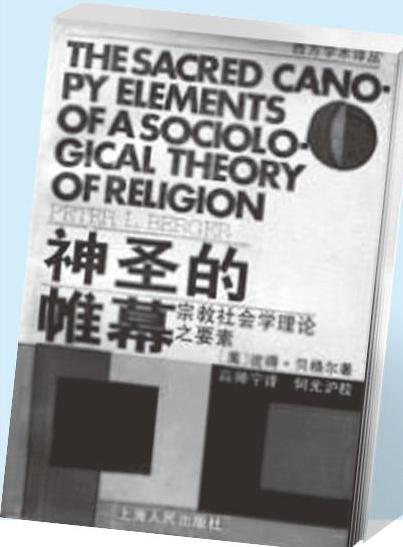
《神圣的帷幕》[美]彼德·贝格尔著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说:“人是这个世界上奇怪的公民:他拒绝现存世界,却又不愿离开它,反而为不能更多地占有它而痛苦。”德国作家黑塞在《荒原狼》中对人生的表述,略带东方的禅意:
人是由千百层皮组成的葱头,由无数线条组成的织物,古代亚洲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了解得十分详尽,佛教的瑜伽还发明了精确的办法,来揭露人性中的妄念。人类的游戏真是有趣得很,花样多得很:印度人千百年来致力于揭露这种妄念,而西方人却花了同样的力气来支持并加强这种妄念。
然而,如今时代的基本面是物质主义、快乐主义、享乐主义。出世的各种人生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矫正原则,而无法单独成为建构性原则。换言之,出世态度是无法单独存在的。极少有人想当“苦行僧”。恰是因为时代的底色亢奋,那些许素淡之色才能够显露出来。
在圣雅各之路上,大部分人在走,一些人会选择骑自行车,还有些人直到今日还会骑马或骑驴去。这些都是被官方认可的朝圣方式。一般认为,如果选择步行的话,每天走二十到三十公里是比较合适的距离。不过也有人一天走四五十公里。没有人在比赛,每个人走自己的路而已。
九、破裂的帷幕
著名的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Peter L. Berger,又译为伯格)在他的《神圣的帷幕》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把人的世界(即我们今天称为文化和社会的一切)理解为是镶嵌在包含整个世界的宇宙秩序之中的。这种秩序不仅未在经验实在中的人的领域与非人的(即“自然的”)领域之间作出现代这种截然的划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假定了在经验的东西与超经验的东西之间,在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假定人间的时间与渗透宇宙的神圣力量之间有一种不间断的联系,它一次又一次地在宗教仪式中得以实现……
这段话可以为解释现代人的无意义感,提供一点线索。现代人的仪式感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朝圣是一种典型的宗教仪式。在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看来,朝圣具有一项明确的社会功能,即恢复和确认人与神圣力量之间的联系。这并不仅仅对宗教人是有意义的。贝格尔认为,现代人和古代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那种“宇宙秩序”被打破了—神圣的帷幕破裂了。人的生活的整体性没有了—原本的个体被镶嵌在家庭、宗族中,宗族嵌入在民族中,民族则是镶嵌在他们所相信的神明的计划,或者整个宇宙进程当中的。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的生活方式,把人甩出来了。人从那个世界观的帷幕中被剥离了出来。不仅如此,在机械的宇宙论中,人不再需要那种周期性的“恢复”机制。于是,人们似乎也就不需要任何具有超自然意涵的仪式了。然而,其实非宗教的日常生活也至少需要一点仪式感,才能帮助人们重建意义。非宗教徒如何理解宗教徒的朝圣之旅呢?朝圣使得人从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当中抽身而出,反观自己。非宗教徒需要这样一种“抽身而出”吗?
十、活出人生
影片中有一段回忆。汤姆和丹尼尔在车上有一段对话。汤姆说:“我的人生可能和你的不一样,但这是我选择的人生。”丹尼尔回答说:“老爸,你并不选择人生,而是要活出人生。”(You don?t choose a life, you live one.)
那么,人生是选择出来的,还是活出来的呢?我们并不想陷入一场辞藻之争。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写道:
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觉到自己在这样做。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而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或者一棵花椰菜。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连理性的天堂里也没有他;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
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原本是一个很抽象的哲学命题,但在上面这段文字里生动起来。“下定义”和“自我筹划”或许既包含了选择,也包含了行动。对萨特而言,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要自主地作出选择,并承担该选择的所有后果。即便是随波逐流,也是一种态度,也要承担起后果。即便不作选择,人生还是继续在前行。很多人一边时刻抱怨自己的生活,另一边却不愿作出任何改变。这也就是自欺。

朝圣手册(credencial),又被称为朝圣护照
你有不自欺的勇氣吗?
十一、人生之旅不是一份遗愿清单
人们总是习惯用旅途来比喻人生,然而这极具误导性。人生并不是一场练级打怪的电脑游戏,里面设定好了形形色色的任务。
圣雅各之旅中每个人有一本朝圣手册(credencial,又被称为朝圣护照)。每到一个城镇,你就可以到那里的教堂或庇护所里盖一个图章。等你最后抵达圣地亚哥大教堂的时候,手册上就会盖满了章,凭此可以换取一份朝圣证书。如今,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吸引游客的绝佳手法。这和欧美年轻人中流行所谓的“遗愿清单”(bucket list)极为相似。遗愿清单在本质上带有一种征服世界的心理,至少表达了一种占有心态。
然而,人生之旅并没有这样一本朝圣手册,也没有什么现成的人生指南。我们最终也不需要换取一份人生的朝圣证书。人不就是自己生命的朝圣者吗?
十二、哲思常在路上
哲学读物中有一部类似《朝圣之路》的作品—《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此书把哲思和行走结合起来,好像行走中的人会自觉地哲思,于是哲思成了行走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一部行走“在路上”的哲学书,或者说是一部哲思中的公路片。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美]罗伯特·M.波西格著张国辰译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
该书的作者罗伯特·M.波西格是一个不折不扣、表里合一的“神经病”。他身上充满了二战之后的嬉皮与朋克气质,又浸透了禅宗式的舍得与放下。他曾经是一个少年天才,学习过化学与哲学,当过修辞学教授,后精神崩溃,接受了二十八次休克疗法,与妻子离婚,痊愈后成为电脑技术员……
有一天,他突然决定和儿子骑摩托车横穿美国,行程近万里。这是一段说走就走、说停就停的旅程,没有丝毫自我标榜与矫揉造作。在途中,他用心看大自然,用车轮和双脚丈量大地。他虽然不是职业的哲学工作者,但东西方哲学在他的头脑中激荡交融,产生出了一些毫无学院陈腐气味的独特洞见。西方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源。而波西格则离经叛道地提出了“良质”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quality)。如果在学院里,他可能根本轮不到被批判,因为这样的文章根本不可能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而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它曾被一百多家出版社拒绝过。
波西格说:“日子就是这样随意,忘掉时间,没有人会催促你,也不会担心浪费时间。”大概,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需要这样一段旅程—不是逃离,而是作为一种内观和自我诊疗。人生的意义或许始终在路上。
绝大部分朝圣者的旅程在圣地亚哥大教堂就结束了。而在电影《朝圣之旅》的结尾处,汤姆和同行的三个人再向前走了一段,来到了海边上的菲尼斯特雷海角(Cape Finisterre)。“菲尼斯特雷”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的finis terrae,意思是“世界的尽头”。据说,那里才是圣雅各身体被冲上岸的地方。汤姆把儿子的骨灰撒入大西洋的波涛中。即便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人生还在途中。有些朝圣者要在菲尼斯特雷海角烧掉自己的衣物和鞋子,表示路程正式结束,开始打道回府。作家杰克计划要写一本朝圣之旅的小说;萨拉明白了自己根本就不是为了戒烟而来的;尧斯特减肥失败,决定回家买一套新西装;汤姆爱上了行走,开始了其他的壮游。
如果你将《朝圣之路》当作一部“公路片”来看的话,就会遭遇所有公路片的失落感—再美好的旅程总要结束。在抵达旅途终点的时候,一种虚无就会袭上心头。有的人害怕回到庸常的生活中去,有的人则是担心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世界。不过好在你也可以放宽眼界来看待它—在影片结束的地方,生活才刚刚开始。
Buen Camino(一路走好)!路漫漫其修远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