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儿童摄影?
藏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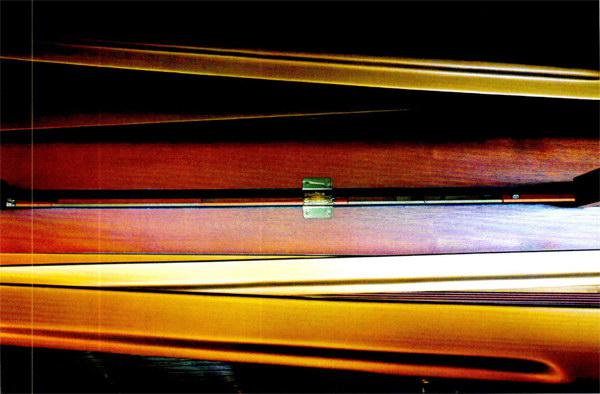
在研究摄影理论的过程中,我逐渐总结提炼出“元影像理论”,这一学说在刚刚创立的时候,思路还远不如现在清晰。那时候我只想到了三个比较笼统的理念,即回归艺术本体、回归本心本性与回归东方智慧。
一种理论的提出,当然需要用实践来加以检验。我们对于“回归本心本性”这一理念所做的第一个影像实验,就是当年的“隐没地”影像实验。我们把最简单易用的卡片相机交给从未接触过摄影的当地村民,让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自由拍摄。与此同时,入驻村民家中的摄影师则用各自的专业器材自由拍摄。晚上,大家围坐在村民家的炕头上,把白天拍摄的影像用投影仪播放。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很多村民拍摄的照片,竟然比一些著名摄影师的精彩许多!感触最深的是解海龙,他当即表示:以往的那些技术和经验都不再管用了,必须要“归零”。果然,当这些拍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资深摄影师,抛弃了以往的各种套路之后,也纷纷拍出了他们更满意的照片。可以说,在“隐没地”影像实验中,不是摄影师教会了村民如何拍照,而是村民教会了摄影师怎样“发现”。
在参加拍摄的村民中,就有好几个年龄不满10岁的儿童,在村民影像中,这些孩子的作品尤其精彩。“元影像理论”中有关儿童摄影的实验,其实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天真之眼?
那么作为理论家,该如何解释其中的原理呢?我当时所能意识到的,也只是人类固有的视觉天性以及视觉“俗套”对视觉天性的遮蔽等。然而这种解释其实是很粗浅的,真的会有所谓“天真之眼”吗?
在“元影像理论”后续的影像实验中,来自天津滨海的摄影师陆心海加入了我们的团队,他从元影像的“心灵能指理论”以及自身的影像探索中,悟出了一番视觉修养方面的道理。
2015年3月的一天,陆心海和我说了准备进行儿童摄影实验的想法,我听了非常高兴,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接下来他的项目进展得很快,沒过多长时间就有了第一批小学员。他教孩子的方法,完全符合元影像理论的基本理念——即不从相机操作及拍摄技术入手,而是从培养孩子们对色彩、线条以及图形的感受与观看入手。不久,孩子们就拍出了各自的精彩作品,一名当时只有5岁的张曦墨小朋友的作品尤其精彩。这些儿童摄影项目的成果在当地图书馆展出后,社会反响很大,家长们也非常满意,认为这种通过摄影方式对儿童视觉的开发,比社会上那些只注重技能技巧的培训有意义得多。最有意思的是,陆心海还组织了儿童摄影作品的拍卖活动,让孩子们从小就有了对艺术品及艺术市场的亲身体验。
元影像陕北团队的朋友们看到了这些儿童摄影作品后,便邀请我和陆心海到陕北甘泉的第一小学来推广这个项目,于是“元影像理论”的儿童摄影实验项目,又移植到了小学教育之中。
何为童心?
2017年,我先后在大理国际影会与丽水国际摄影节上,为陆心海的“元·禾下儿童摄影项目”进行策展。影展得到了国内外摄影界人士的广泛关注,陆心海和他的儿童摄影实验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特别强调了如下几点:
首先,元影像的儿童摄影实验,与其他的儿童摄影教育、培训之类完全不同。我们根本就不是以培养什么“小摄影家”“小记者”为目的,也不像那些教乐器教英语之类的课外辅导班是为了教孩子某种技能。我们的目的在于开发儿童的视觉想象能力以及艺术的创造力,至于孩子们长大后会不会成为摄影家,根本不重要。因为儿童最宝贵的,是他们的“童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童心”反而会逐渐地被遮蔽。而在儿童时期对孩子们的“童心”加以开发的话,就会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一颗会自由想象、自由思考的种子,将来无论他们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自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会伴随他们的一生。摄影只不过是让孩子们学会观看和想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已,摄影只是路径而并不是目的。



第二,儿童摄影实验本身,也是“元影像理论”对于自身学术与理论建设的一个实验项目。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儿童摄影的视觉实验,来丰富理论探索的更多维度,寻找摄影的更多可能性。从角度上说,其实我们是在向孩子们学习,向人类的“童心”学习。
第三,从某种意义上看,儿童摄影实验项目本身,也可以视为是一个关于艺术本身的思考与行为,是陆心海以摄影教育的方式所进行的一个具有持续性的艺术行为。
“直接”的奥秘
那么就元影像理论而言,儿童摄影实验项目又为我们提供哪些灵感呢?我从多年前的“隐没地”项目开始,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从未接触过摄影的村民会比摄影家拍得好?为什么儿童的影像作品往往会让成人摄影家惊叹?如果说村民与儿童影像最打动人的特点就是“直接”,那么他们的“直接”与日本摄影的“直接”又有什么内在联系,该如何解释这种影像的“直接”?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非常深奥,甚至直抵观看与影像之奥秘的核心。我现在也只能就自己目前的认知水准来试着解析一下,但并不代表有了一定的结论。
首先,我以为“直接”应该就是去中介,也就是特定方式的去符号化,比如佛教六祖慧能“以手指月”的那个著名例子——手指是月亮的指示符,而非月亮本身……然而就如符号学所揭示的那样,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作为事物“观相”的符号,我们身处符号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符号的包围之中,又如何可能去除作为中介的符号呢?这其实才是破解问题的关键。



我曾在《童心与性灵》一文中提到一个例子。孩子看见月亮——啊,月亮!看见海——看呀,海!这与成年人看见月亮、看见海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呢?李白看见月亮后,想到的是故乡;苏轼看见月亮后,想到的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而小孩子看见月亮,想到的却是月亮本身,因为月亮本身就足以让他惊喜了。看见海也一样,成年人看见海也许会想到乘邮轮去海外旅游,想到普吉岛、夏威夷,想到“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想到诗与远方,甚至想到永恒……而小孩子想到的可能就是海本身,海本身就足夠新奇,就已经是一个神话了。
现象学家让-吕克·马里翁在《可见者的交错》一书中提出了“充溢现象”的观念,这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对村民影像、儿童摄影乃至某些日本摄影的理解。在这种现象模式中,现象不再以主体为条件,不再被主体构造为对象,而是自我给予、自我显现,现象本身拥有显现的完全自主性;同时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充溢现象的自主显现,并且从中接受自身的规定,从而为现象所构造。马里翁指出,在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原初给予的直观(可见者)是过剩的,进而超越了自我的构造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一组新的现象将会显现出来,这组现象即充溢现象。充溢现象中过剩的原初被给予物(可见者)超越了意向的把握能力,超越了意向根据之前的经验所能进行的理性预测,而成为“意向不能预见的东西”。
在皮尔斯符号学中,符号、对象与解释项构成了一个三元结构。对象决定了符号是与解释项相关联的,而符号又决定了解释项是与对象相关涉的,这就导致对象会通过符号这一中介去决定解释项。皮尔斯对解释项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包括直接解释项、动力解释项与最终解释项。直接解释项有时也被称作“感觉解释项”。“直接”的奥秘或许就在这个“感觉解释项”里——当观看对象作为“充溢现象”而停留于“感觉解释项”时,其“中介”性就被阻断了,从而成为了“意向不能预见的东西”。这里我想讨论一下“视觉逻辑”与“话语逻辑”的问题,“视觉逻辑”是以观看的逻辑为线索的,“话语逻辑”则以概念为线索。在本雅明看来,概念对现象的分类概括是一种割裂和肢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说理念可以完成对现象的拯救……但如果只停留于“视觉逻辑”而不进入会被概念分割的“话语逻辑”呢?村民与儿童的影像,最宝贵的地方大概就在于此。
尼采就曾认为:感性证据是真实的,可信的,只是对它们加工时才塞进了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