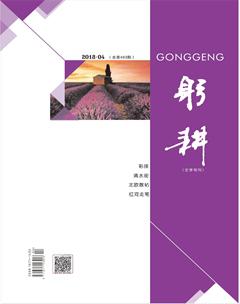命运的写作
韩向阳
在乔老师生命的最后时候,我去看过他。在县医院一个普通病房里的一张普通病床上,他折着身子坐在那里,双手抱紧低垂的脑袋,憔悴的面容痛苦不堪。致命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大脑里,当他意识到我走近时,那只有气无力的手朝我地摆了摆,像是要同我打一下招呼,又像是万分愧疚地告诉我他已经没有说话的力量了……我在他的对面坐了大约半个小时,只是坐着,惶恐而悲哀地看着他——这是我这一生中经历过的最煎熬的时刻——我真的没有再同乔老师说一句话了,我也真的不知道能说些什么……
乔老师患的是喉癌,我不知道那段时间他都经历了怎样的苦痛与折磨。在他治疗期间和他后来回到家里休养治疗的时候,我与他见过多次。那次我到家里去看他,在那间简朴的书房里,他半躺着坐在那张木椅上,手术后他不能像往常那样谈笑风生了,说话的声音微弱喑哑,偶尔起身绕着书房走几步,每隔一会儿就要呷一小口温开水润润嗓子。尽管如此,他仍然面帶微笑,同那些去看望他的老朋友们谈得最多的依然是创作。当时他正在写作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别无选择》。我知道,这多半是作家对人生旅途的最后一次回望了,而且我也感觉得到这沉重而寂寞的回望中充满了宿命的意味。
《别无选择》最初在《南阳日报》连载,后来又在《莽原》发表。或许是编辑们也在那些字里行间看到了宿命的影子,《莽原》发表时改名叫《命运》。这也真的就是一次宿命的写作。我不知道乔老师的这个长篇是何时动意的,是在他得病之前,还是得病之后,作为一个一生都耽于人生思索的作家,这个长篇是否就意味着他已经望见了越走越近的生命彼岸?
有人评论乔老师的写作是凿井式的。这个比喻很是恰当概括了乔老师作品以以小见大以微见著的美学特点和艰难的创作状态。像一个执著而勤勉的农夫,守在一块不大的土地上,一镢一锨地朝下挖掘,直到地层深处石缝里流出他心中期望的那一线泉水。与场面开阔的耕作相比,凿井其实是一种技术难度更高也更加艰苦的劳作。我想起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一个短篇小说《沉重的时刻》,写的是一个作家写作过程中那沉重而艰难的时刻。托马期.曼是在写他自己,也是在写每一个作家。作家的创作似乎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艰苦卓绝的必然阶段,然后才能在某个时刻起身跃入自由宽阔的天地。乔老师一生作品数百万言,可以称之为经典之作的,是他的《汽球》、《乡醉》,是他的《村魂》、《冷惊》,是他的拿了国家级大奖的《满票》,但是在我看来,最能称之为经典的当是他的《别无选择》。在此之前的那些作品是他“创作”出来的,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多数作品,甚至包括那些篇幅不长的短篇,大多时候写得都很艰难,有时候一个小短篇也要构思上几个月乃至几年时间,单是一个小说的开头也要写上几十遍。写了,扔了,再写了,再扔了,否定,再否定,一遍又一遍地在否定的炉火中烧毁自己。我曾经亲眼看到他那张木桌下面扔了一大片揉成纸疙瘩的“小说开头”。而到了《别无选择》,他的抒写之河则完完全全地豁然大开了,我觉得乔老师这个时候才真正进入开宽地阔的自由王国,开始了无拘无束的展翅飞翔。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病魔却突然站在了他的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乔老师的人生是从曲曲折折风风雨雨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写作让他快乐无比,也让他遍体伤痕。这个被称为农民哲学家的作家也更是自己人生的哲学家,他洞悉历史也洞悉自己,十分清楚他是在怎样一个时空中写作的。他的作品总是指向对社会的深刻批判,同时似乎又总是有所顾忌的,因此他此前的作品总以深刻见长却又缺少足够的自由度。我们没有理由去对一个作家说短论长,因为我们都是历史的奴隶。历史别无选择,作家的创作亦别无选择。身处这个时空段,作家们必须面临这样一个共同的困境。
然而,一个真正的作家总是要面对困境,困境给了作家以痛苦和折磨,也给了作家以深刻与超越。
乔老师正是在这个痛苦的时候开始了自己的超越。当病魔开始敲打他的命运之门时,他也迎来了他的解放者。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正是在他面对死神的时候,他那双正在被死神阴影遮蔽的双眼也看到了一片广阔自由的天空。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所顾忌了,可以怎么想就怎么写了。哲学家们说:人类只有面对死亡时才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对于作家们来说,也只有面对死亡时才能产生真正的文学。有时候我甚至在想:若没有这不期而至的病魔,会不会有《别无选择》呢?病魔是在剥夺还是在给予呢?
在死神无情的注视下,乔老师在进行着他最后的写作。自由与死亡,自由与死亡,竟然是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悖论,在迎来解放的同时他又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同样荒诞的荒诞:乔老师在迎来解放者的同时也知道上天留给自己的时间所剩不多了。《命运》真的是一篇命运之作,他以《命运》与命运搏斗,以有限的时间与时间抗争,以《别无选择》进行着自己的最后选择。《别无选择》的许多章节是在病床上写出来的,当病痛使他连拿起笔杆的力量也失去时,他只能躺在那里缓缓口述,请别人代为记录整理。《别无选择》在南阳日报上一篇一篇地连载,我一篇一篇地跟读,阅读的过程中眼前总是不停地浮现着乔老师折身坐在病床上痛苦的身影。这样的阅读带给人的是双倍的煎熬和痛苦:从作品自身中感受到的痛苦和作家痛苦写作带来的痛苦。每次放下报纸后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与茫然。我依然无话可说,甚至不能恩索,只能下意识地祈祷,为乔老师祈祷,祈祷苍天多给他一些时间,让他能够完成他的最后之作,哪怕只有一年时间,而且,我居然也相信,老天一定会答应这个并不过份的甚至是可怜的祈祷的。
然而,苍天没有答应,《别无选择》最终没能完成乔老师便无奈地转身而去……
逝者如斯,如今乔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然而还有一个时间不会消失,这个时间在人们的心中。即使过去了二十年,当人们议论起乔老师时,依然感觉得到他仍像二十年前那样活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那时候县文联的办公地点设在县城深处一个破旧的四合小院里,坐东朝西的那三间上房就是乔老师写作和休息的地方。我记得上房前面是几层砖砌的台阶,走进南头那间小屋时,我看见乔老师正坐在一张老式木桌前的一把老式椅子上。一缕阳光透过一扇同样老式的方格木窗照在一方稿纸上。他摘下老花镜,放下钢笔,起身朝我走过来。“最近又写啥东西没有?”每次见面时他总这样问我,我感觉得到,他的问话中寄托着对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的深深的期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谓的新时期,国门初开,八面来风,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汹涌而至,潮头迭起,作为一个尚且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自己也在满怀激情地追求着那些形形色色的前锋写作。乔老师的创作也在创新中拓进,但同时他又坚守着自己现实批判的写作理念。有一次我拿了一篇名叫《大火》的小说稿子给他看。那是我尝试着写出的一篇所谓荒诞小说。乔老师看过后,两眼笑眯眯地从眼镜上方看着我。“你写这个东西是想说点啥?”我有些结结巴巴地说出了我的想法。他点了点头说:“写小说,一点得有思想……”这是乔老师一贯的观点:一部作品,无论大小长短,一定得告诉人们点什么,一定得让人们思索点什么。后来我还送给乔老师一个短篇稿子《耳巴子》,他看后非常喜欢,动笔写了一封推荐信,寄给了《河北文学》的编辑赵立山。这篇小说很快在《河北文学》发表了,后来还获得了河南省優秀短篇小说奖。
一起交谈时,乔老师有一个习惯性的姿势:斜侧着身体坐在藤椅上,指缝间永远夹着一根香烟,一缕白烟袅袅升起,在他沉思的额前绕来绕去……对于乔老师来说,吸烟早已成了他沉思的方式,香烟弥漫了他作品的字里行间,也弥漫了他的整个人生。那次在他手术后不久我去看他时,他指了指自己手术不久的喉咙,用喑哑的声音说:“都是吸烟吸的……”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他并非不知道吸烟对生命的损耗,但他又不能不沉思。因为无法戒掉沉思,自然也无法戒掉香烟,香烟烧掉了自己也燃烧了一个作家的生命。一个作家的生命有多长,是一根香烟的长度吗?这是作家的又一种宿命。
……如今乔老师一个人躺在一片荒坡上,孤独而安静。陪伴他的是那片他熟悉的故土和那片土地上的庄稼、树木和野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县文联的老院却枯而不荣,永远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水泥钢筋结构的现代建筑,再去那里时,自然也看不到乔老师坐在那把老式椅子上的身影了。
然而,《别无选择》还在,因为,这是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经典之作与时间一样长久,不会死亡……
“就沉沉地睡去一次吧,
就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沉静
可以与外面的风雨无关
空间再狭小将孕育我的生机
……我以简短的感激之辞
感激冥冥中各位天神
多亏生命并非永恒
多亏死者从不苏醒
即使疲惫不堪的河流
也在某地入海安身……”
——这是斯温伯恩的《冥后之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