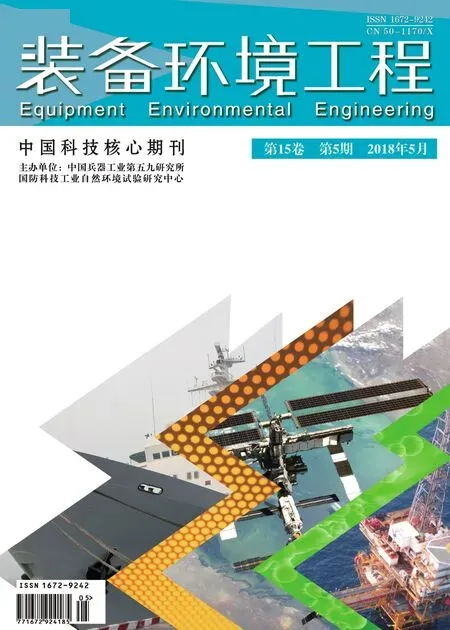铜合金实验室试验与实海挂片结果的比较与分析
周鹏飞,孔小东,苏小红
(海军工程大学 基础部,武汉 430033)
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铜及其合金因具有良好的耐海水腐蚀性能将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各项海洋装备工程。海洋环境对铜合金来说是一种非常严酷的腐蚀环境,铜合金受海水温度、海水含盐度、海洋大气温度、海洋大气湿度、海水流动等因素的影响,腐蚀情况较为复杂。因此,只有充分了解铜合金在海洋环境中的腐蚀特点,并掌握相关腐蚀数据,才能在设计阶段合理用料,使用阶段制定有效防护措施,避免由于腐蚀引起材料结构的过早失效。天然海洋环境腐蚀试验如实海挂片等方法可以获得较为可靠的材料腐蚀数据,但存在试验周期较长、腐蚀因素复杂多变、参数不可控、重现性差等缺点。相比较而言,实验室模拟研究可以调节试验方法和参数,以达到快速获得材料腐蚀数据和腐蚀行为规律的目的[2]。文中选取了B10,H62两种铜合金,对应实际海水温度变化范围,设置一系列温度梯度的3%(质量分数,下同)NaCl溶液浸泡两种试样,用电化学工作站定期进行交流阻抗以及线性极化曲线的测试,同时用三维超景深数码显微镜进行微观形貌拍摄,获得这两种铜合金在模拟海水中的腐蚀数据及腐蚀形貌照片,比较实验室试验结果与实海挂片结果对这两种铜合金腐蚀性能评价的异同之处。
1 实验方法
实验材料选用B10棒材、H62板材,材料均为供货状态,其主要化学成分见表1。

表1 两种铜合金的主要化学成分 %
1.1 试验试样的制备及预处理
H62铜合金板材试样的尺寸为 10 mm×10 mm×10 mm,B10棒材试样的尺寸为φ10 mm×10 mm。试样的表面处理过程为:采用去蒸馏水冲洗试样表面;将试样置于无水乙醇中进行超声清洗,除去试样表面水分;将试板置于丙酮中进行超声清洗除油;将试样吹干,置于干燥箱中24 h备用。在H62试样上下表面(非切割面)的一端焊上导线,在B10试样上下底面的一端焊上导线,与焊接面相对的一面即为工作面。经万用表测试导通后,用环氧树脂将试样密封于PVC管中,待环氧树脂固化后,将工作面经 240#,400#,600#,800#水磨砂纸逐级打磨,并用蒸馏水洗净,吹干后置于干燥箱中备用。
将四个恒温水浴锅分别设置15,20,25,30 ℃四个温度。将试样编号后依次放入盛有3%NaCl溶液的烧杯中,将烧杯分别置于恒温水浴锅中。烧杯加盖,防止溶液水分蒸发对溶液浓度产生影响,每隔 48 h更换烧杯中的NaCl溶液。
1.2 测试方法
采用武汉科思特公司生产的CS310H电化学工作站测试两种铜合金试样浸泡过程中的极化曲线,试样在3%NaCl溶液中浸泡30 min,自腐蚀电位稳定后再进行测试,扫描速率为 0.1667 mV/S,测试范围为±10 mV(vs.开路电位)。测试采用三电极体系,参比电极为饱和甘汞电极,辅助电极为铂电极,铜合金试样为工作电极,介质为3%NaCl溶液。
采用武汉科思特公司生产的CS310H电化学工作站测试两种铜合金试样浸泡过程中的交流阻抗曲线,试样在3%NaCl溶液中浸泡30 min,自腐蚀电位稳定后再进行测试,交流扰动信号为10 mV,频率响应范围为0.01~10 000 Hz。电极体系与线性极化曲线测试相同。
采用基恩士 VHX-5000超景深三维显微镜对两种铜合金试样腐蚀前后表面形貌进行观察。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实海挂片结果
图1为两种合金在不同海域全浸区8年实海挂片平均腐蚀速率结果。图2为B10合金在不同海域的平均点蚀深度以及最大点蚀深度[3-6]。图 1表明,两种铜合金平均腐蚀速率均随实海暴露时间的延长而降低,且在厦门青岛海域,B10的平均腐蚀速率小于H62。B10合金在暴露初期,平均腐蚀速率较大,经过2年左右时间,平均腐蚀速率降低较为明显,暴露中后期平均腐蚀速率较为平稳。H62合金在整个暴露期间平均腐蚀速率降低较为均匀,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与挂片海域无关,说明与两种合金各自的腐蚀机理有关。平均腐蚀速率均匀降低。榆林海域与其他海域相比,海水温度相对较高,合金的平均腐蚀速率均比较高,尤其以B10合金表现更为明显。青岛海域与其他海域相比,海水温度较低,两种合金的平均腐蚀速率均较低,两种合金在不同海域表现出来的规律说明了温度对腐蚀速率的影响。赵月红等的研究也表明了部分铜合金腐蚀速率对温度具有敏感性[7]。通过图 2不难发现,厦门海域B10合金无论是平均点蚀深度还是最大点蚀深度均较大,且随时间呈现增长趋势。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九龙江水注入厦门海域,淡水-淡海水-海水的盐度交替变化加剧了腐蚀[8],且适宜的温度和更低的盐度有利于各种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加剧了局部腐蚀[9]。
2.2 线性极化结果
通过CS Studio5软件对线性极化曲线拟合,得到如图3所示的平均腐蚀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和图4所示的自腐蚀电位随时间变化曲线。两种合金在不同温度下的平均腐蚀速度均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在腐蚀后期呈现出温度越高平均腐蚀速率越大的规律。可以发现,B10的平均腐蚀速率要小于H62的平均腐蚀速率,这一点与除榆林海区外的实海挂片结果有着一致性。B10合金自腐蚀电位随浸泡时间的延长在一个小区间内波动,且在试验期间未表现出与温度有明显关联。H62合金自腐蚀电位随时间的延长逐渐降低,在试验后期表现出温度越高自腐蚀电位越负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模拟海水温度的升高降低了合金的耐蚀性,对腐蚀具有促进作用。两种合金在浸泡前期,平均腐蚀速度波动较大,而在后期,平均腐蚀速度变化趋于稳定,说明在腐蚀初期,腐蚀反应进行最为剧烈。
比较线性极化结果与实海挂片结果,发现线性极化法后期平均腐蚀速度与实海挂片 8年平均腐蚀速度接近,且平均腐蚀速度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线性极化法只能反映试样表面的平均腐蚀状态,对于试样表面的局部腐蚀情况不能有所体现。
2.3 交流阻抗结果
图5和图6分别为B10和H62的交流阻抗谱。通过 ZimpWin软件选择合适的等效电路进行拟合。对于 B10试样,在腐蚀前期采用等效电路 Rs(CPE1(RP0W))进行拟合,待腐蚀后期表面形成膜层后采用等效电路 Rs(CPE1(Rc(CPE2RP0)))进行拟合。对于 H62试样,在腐蚀前期采用等效电路 Rs(CPE1(RP0W))进行拟合,待腐蚀后期表面形成膜层后,采用等效电路Rs(CPE1(Rc(CPE2RP0)))进行拟合,对于出现两个较为明显的容抗弧的阻抗谱,采用Rs((CPE1Rc)(CPE2RP0))进行试样拟合,得到电荷转移电阻RP0的值。图7为两种铜合金在不同温度下电荷转移电阻随时间变化曲线。
在浸泡初期,由于新鲜金属表面与溶液接触,发生的腐蚀反应较为剧烈,且腐蚀反应在试样表面并不是均匀进行,所以在腐蚀初期阻抗谱波动较大。随着腐蚀的进行,形成了稳定的氧化膜,在腐蚀后期阻抗谱逐渐稳定,波动较小。安闻讯等在低合金钢实海腐蚀电化学阻抗谱研究中指出[10],浸泡的第一周腐蚀最为剧烈,1周后变化放缓,且呈波动趋势。这两种铜合金试样的阻抗谱变化同样表现出这种规律,且与线性极化结果具有一致性。交流阻抗结果能够较好反映试样表面成膜的状况,但同样不能反映出试样表面的局部腐蚀状况。
RP0的大小间接反映了腐蚀反应进行的难易程度。对于B10试样,在30 ℃时,腐蚀前期电荷转移电阻迅速增大,说明温度较高时表面氧化膜形成速度较快。随后稳定,最后随着Cl-的渗透电阻略有下降。其余温度下,电荷转移电阻虽有波动,但平稳提高,说明温度较低时氧化膜形成速度相对较慢,这体现了温度对腐蚀的影响。H62试样并未表现出相同的规律,但通过拟合发现,H62存在较大的膜层电阻,结合后期腐蚀形貌观察,推断是由于腐蚀形成的表面突出物造成试样表面不均匀,对交流阻抗谱的测量及拟合存在较大的影响。安讯闻等也指出,表面松散的腐蚀产物构成了金属表面的伪电容。
2.4 腐蚀形貌观察结果
图8和图9分别为B10和H62在不同温度、不同时段下的腐蚀形貌。通过观察可以发现,B10试样在腐蚀后表面逐渐变绿,后期都出现了点蚀现象,在温度较高时形成了带有绿色的突起小泡,有的部分慢慢连接在一起,形成“小疙瘩”。孔小东等的研究表明[11],B10表面形成铜和镍的氧化物膜层,其中镍的氧化物膜层比铜的氧化物膜层更致密,对保护 B10的基体免受腐蚀的效果更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结合图1a可知,B10合金在实海环境中浸泡2年后形成的致密氧化膜使平均腐蚀速率有了明显降低。H62试样在温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能看到腐蚀后红棕色的表面,表面出现少量白色腐蚀产物,符合脱锌腐蚀的基本规律。在温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局部腐蚀更为明显,温度越高点蚀面积越大,出现较大面积的白色腐蚀产物以及绿色腐蚀产物。这种较为疏松的氧化物膜层使基体免受腐蚀的效果较差,也对交流阻抗的测量产生了较大影响和误差。
两种铜合金在实验室通过腐蚀形貌观察都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和时间的延长,点蚀存在加重趋势,这种现象与图2实海挂片点蚀结果所反映的点蚀情况并不一致。说明在实海环境中,温度不是影响点蚀的主要因素,微生物等其他环境因素会对点蚀产生较大影响[12]。
3 结论
1)实验室试验结果和实海挂片结果一致表明,B10耐蚀性优于H62,且温度的升高对铜合金的平均腐蚀具有促进作用。虽然实验室试验周期较短,但平均腐蚀速率同样表现出随浸泡时间的延长而降低,与实海挂片结果一致。
2)实验室试验能对平均腐蚀有较好的反映,但对点蚀情况的反映有限且误差较大。在实验室试验中,B10随温度升高点蚀加重。在实海环境下,温度升高对点蚀未起主要影响,而微生物等其他因素影响更大,这也体现了实验室试验存在的不足。
3)线性极化法和交流阻抗法对于两种合金的腐蚀评价各有优劣,线性极化法更为快捷方便,但只能反映平均腐蚀状态,交流阻抗法对腐蚀的反映更为全面,但是交流阻抗法对于表面产生较多腐蚀产物的H62试样存在较大误差。
参考文献:
[1] 宋诗哲. 腐蚀电化学研究方法[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1988.
[2] 李冬冬, 吴忠良, 许佳宁为, 等. QAl10-4-4、QAl9-4和ZCuAl10Fe3铜合金在模拟海洋环境中的腐蚀行[J]. 腐蚀与防护, 2016, 37(6): 461-466.
[3] 朱相荣, 黄桂桥, 林乐耘, 等. 金属材料长周期海水腐蚀规律研究[J].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 2005(3):142-148.
[4] 赵月红, 林乐耘, 崔大为. 铜及铜合金在我国实海海域暴露 16年局部腐蚀规律[J]. 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2003(5): 266-271.
[5] 夏兰廷, 王录才, 黄桂桥. 我国金属材料的海水腐蚀研究现状[J]. 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 2002(6): 1-4.
[6] 朱小龙, 林乐耘, 徐杰. 铜合金在海水环境中的腐蚀规律及主要影响因素[J].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1998(S1):215-222.
[7] 赵月红, 林乐耘, 崔大为. 铜镍合金在我国实海海域的局部腐蚀[J].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2005(11): 140-148.
[8] 杨博均, 陈翔峰, 姚敬华, 等. 铜及铜合金在淡海水交替自然环境条件下的腐蚀行为研究[J]. 装备环境工程,2017, 14(2): 24-30.
[9] 尹兵. 海洋环境下铜镍合金的微生物附着腐蚀与防护研究[D].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2012.
[10] 安闻迅, 邓春龙, 杜敏, 等. 低合金钢实海腐蚀电化学阻抗谱研究[J]. 装备环境工程, 2009, 6(1): 17-20.
[11] 孔小东, 田志强, 林育峰. 微观组织对铜合金腐蚀性能的影响[J]. 装备环境工程, 2015, 12(6): 1-9.
[12] 杜一立. 两种铜合金微生物腐蚀的比较研究[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