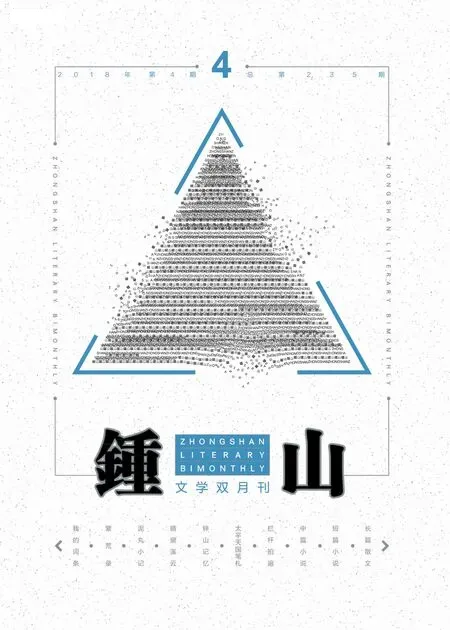罪与罚
——兼及两性问题
李洁非
L I J I E F E I
我们如今所称的“法”,古代一般名之以“刑”。近代以来对“法”的理解,无论层次与精神都更周密、更辨证,古代则比较片面,基本是作为惩罚和镇压工具,假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秩序。所以在古代,“法”大致等于“刑”,或集中体现于“刑”。由于侧重和依赖暴力,古刑比之于今世远为惨刻,目的不但在于让乱法者受惩处,且冀望借助刑的可怖来威吓所有人。但过去我们常有个误解,以为酷刑惟中国为多为甚。其实不能这么说,对酷刑的喜好,旧时代举世皆然。以欧洲为例,起码到十五世纪,那里酷刑就未见得较中国逊色。中国一方面确有不少酷刑,另一方面中国对刑的认识也从来分处两端。一种是嗜虐逞威,另一种则主张慎刑求德。后之代表,即儒家口中的上古圣君尧、舜。据说他们治天下之前,蚩尤“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自谓得法”,这“五虐”之中,包括劓、 、 、黥等肉刑,“而尧、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载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数亦不具于圣人之旨也”,令以刑残民的统治成为过去。尧、舜还主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很了不起,虽距现代“疑罪从无原则”尚存不及,但在远古能持“罪疑惟轻”的认识,已经相当杰出。尽管尧、舜史事尚未从考古上落实,可能是儒家典籍的杜撰,然而作为思想见解,它们存在于中国是不必否认的。
透过法律制度,一来能看到社会的价值取向,比如保护什么、反对什么。二来能看到社会的道德观念,以何为善、以何为恶,法律功能之一就是惩恶扬善。还有,能看到政权的特征乃至权力背后的哲学,比如权力是较有自信还是被焦虑所控制,或权力对人性的看法偏于正面还是负面……这些都会影响法律的面貌,令它宽严相差、刚柔有别。
太平天国官方文件中,未见颁有正式法典,仅有带法律性质的《天条书》和军规一类东西。正式法典究竟有没有,至今存疑。似乎有,张德坚从接受调查的太平军对象那里,听到过“太平刑律”的名称,不过直到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完整的太平天国律书。《贼情汇纂》从大量文书告示中辑录了六十二条,是目前所知太平天国法律条文最全的汇总。这是截至1855年亦即《贼情汇纂》付梓时的条文,法律内容总是会随时变更以适应现实变化,比如广西时期太平天国条例就比较简单,后则“所增禁令日繁”;因此,《贼情汇纂》所辑也只是一个参考,我们姑以此为凭,就太平天国法律情形作一点有限的考察。
先说酷刑。太平天国有些令人色变的野蛮刑罚,如点天灯和五马分尸,是明确载于其文书告示的:
凡我们兄弟如有被妖魔迷懞反草通妖,自有天父下凡指出,即治以点天灯和五马分尸之罪。
故张德坚说:“贼目残忍,专事威 。”不过,仅此不能对我们的认识有何帮助。使用酷刑,绝非太平天国特色。它的敌方清朝,同样有酷刑。让我们从“小说家言”说起,莫言《檀香刑》的主人公,是一位大清刽子手,擅长“檀香刑”。所谓“檀香刑”,就是凌迟。莫言对“檀香刑”极尽渲染,自不免虚构成份,但凌迟重典明载于清律,却是事实。它一直到清朝尾声,于光绪三十一年经沈家本等人奏请,方告废除。《清史稿·刑法二》:
三十一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请删除重法数端,略称:“见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曰凌迟、枭首、戮尸……”
凌迟作为顶级酷刑残忍之极,在它面前,其他酷刑都未免相形见绌。所以我们谈论太平天国酷刑,如果是为证其格外残忍,这个目的恐怕达不到。酷刑的可谈与宜谈,其实在别处,比如说文化含义。人类所有造物,不论美丑,都有文化的意义,就连酷刑这样丑陋的东西,说起来也应划在“文化”范围内。比如中国正统王朝对酷刑之设,是有讲究的,并非怎么野蛮怎么来,怎么狰狞怎么来,而须“传承有序”、“其来有自”,像做文章那样得有出典。史上没有的,不好随便乱创;史上曾有但前朝已废的,也不宜贸然恢复。总之应该循例而设。清朝用凌迟之法,便即如此:
凌迟之刑,唐以前无此名目。《辽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之内。宋自熙宁以后,渐亦沿用。元、明至今,相仍未改。原来,凌迟是契丹始创,宋朝自神宗熙宁年间仿之,而元、明二代沿用。有了这番传承关系,它似乎便正当起来,可以堂而皇之地采用。反观太平天国,耐人寻味的恰也在于,它的酷刑如点天灯、五马分尸、铜锣炙背、火链缠腿、锥刺谷道等,皆非“相仍未改”而来。其中个别的如五马分尸,史上虽有,古名“刑”——商鞅死于“车裂”即此刑——但久已废除。那么,为何偏偏太平天国于酷刑不走“传承有序”路线?这倒正是历史可以品味处。加以体会,我以为或含几点:其一,能力所限,“技艺”达不到。比如凌迟,几被传为绝活,神乎其技,“明杀宦官刘瑾,凌迟三日始死,据云例该三千三百五十刀”,甚是离奇,不知真假,但技术上有相当难度是一定的,太平天国恐怕暂不具备这么高级的专家刽子手。其二,察诸太平天国酷刑,一个共同特点是全都简便易行,人人可为、弗学而能,包括行刑器具亦属俯拾即是一类,还不必挑地点场所,随时随地上手,除了没有技术门槛,不能不说这很适合太平军多数时间处于流动和野战状态的需要。其三,太平天国酷刑,多数带“野刑”味道,不重仪式,比较随兴,宣泄意味浓,与街边田头撒野没啥差别,自“正统王朝”角度会觉得缺乏“明正典刑”的严肃性,但在太平天国,也许反而合它心态;它是一场“革命”,“革命”自不肯循规蹈矩,不痛快淋漓又如何尽显“革命”烈焰熊熊之势?
由此,也谈谈对太平天国酷刑的各种记载的考辨。
除点天灯和五马分尸这两种外,诸记所载的酷刑,在《贼情汇纂》所辑六十二条里都找不到。《贼情汇纂》一书,不出于作者个人之述,全部辑钞自太平天国正式文书和告示,故相当可信。而诸记所载全属见闻,有些来自作者自称的目见,有些却只得诸耳闻。这就带来一个真实性问题。在过去,颇有论者置之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污蔑”,予以了断。这种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然而,同时也就面临另一个不能排除的困难,亦即我们所用到的太平天国史料,多半都属于此类“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撰述,如果“污蔑”的假设在逻辑上成立,就应将它们整体弃用,而没有办法把其中一部分视为“污蔑”、对其余部分却视为可信材料加以采用。因此,借口“污蔑”而搁置诸多太平天国酷刑记载的做法,本身经不住推敲。作为形态有些特殊的政权,“载于明文”未必是甄别太平天国史迹真赝的依据。从至今未见一部成文法典论,刑罚在太平天国,极可能始终就并不采取严谨、正式的法律体系的面貌,反而有很大的随意性、随机性。这里有个例子,沈梓《避寇日记》记述曾见太平军张贴告示于一寺庙,“系南京伪天皇(王)规条,有十诫、十嘱、十除、十斩四十条”,“诫者,诫人犯教中之禁也。嘱者,劝人从其教也。除者,除去恶习,如乌烟、花酒、释道之类。斩者,斩违教者也。 ”这“天王四十条”,别书未见,人不能鉴其真假。直到1950年,江苏金坛县拆除旧墙时发现一份写于黄绫之上的太平军 《邴天福令》,中有“读四十天法,圣心教导精详”之语,适与沈梓“天王四十条”相佐,乃知其虽无考于太平天国官书,但《避寇日记》所述确非虚罔。类乎“天王四十条”那样确实存在而不见载于正式文献的情形,提醒我们太平天国治刑可能有任意、灵活的特点。它的条规可视乎需要随时添改,乃至于握一定权力者可以 “因地制宜”、“便宜行事”、自颁章则。张德坚从缴获材料见到“伪燕王秦日纲所出告示,亦载应斩罪多款”似即为秦日纲法外置法,在所辖范围自搞一套,另张新规。做文章讲“文”“野”之分,其实人类做所有事,都存在“文”“野”之别,刑 也不例外。历来在国法之外,不能尽绝暗中的私刑,比如宗族内部或秘密会社一类死角,私设公堂都司空见惯,所行私刑往往别出心裁、五花八门,以“野”见长。拜上帝会原本就带有浓厚的秘密会社色彩,兼之建都天京后并无向常规国家形态转型的鲜明意识,法度偏“野”少“文”是可想见的,其间若有不见诸史的“野刑”即兴之作,岂足为奇?
李秀成述天京末期:
自九帅兵近城边时,天王即早降严诏,合城不敢违逆,不遵天王旨命,私开敌人之文、通奸引诱,有人报信者,官封王位,之知情不报,与奸同罪,命王次兄拿获,椿砂、剥皮法治。
“椿砂”、“剥皮”这两种酷刑,均未见于张德坚所辑六十二种,此处却经李秀成亲笔述记。同治三年六月,上海《新报》在报道中对两刑曾予描述:

剥皮惨刑古有之,但“椿砂”或“椿臼”则似为太平天国“发明”。《能静居日记》记有一实例,同治三年二月,天京有图谋投诚的头目许连芳,失败后死于该刑:“闻许已监押,后闻于十六日用石臼碓舂死。”借酷刑让人在死亡之外对肉体痛苦极度恐惧,这个效果可以说很好地达到了,以致李秀成冒险对天王表达异见时说:“尔将一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足见对“受刑”的恐惧,远过于处死。用刑过酷的另一证据,是洪仁玕《资政新篇》郑重建议“善待”人犯。他劝洪秀全“恩威并济”,希望他“刑外化之以德,而省于刑”。设若施刑之毒未至惨不忍睹,干王实不必作为一个重大关切在此诚恳提出。
酷刑种类方面,似对火刑情有独钟。上述剥皮之刑,实为火刑一种。点天灯亦为火刑:
用棉絮卷人而绷之浸以油,置巨木倒缚于其上,燃以火名点天灯。
谢介鹤所述几种,俱以用火为主:
越日有出城逃逸者,为贼所获,即前剪发人(太平天国蓄发,剪发意味着投敌),则怒以火烙火锥之,问通妖否……或将手足反接,背置铜锣,用火?之,呼惨之声,不忍入耳。或将衣服脱尽用铁链烧红向胫一盘,但闻油渍铁声,肉皆糜烂,痛叫一声,大半昏绝。或用火箸烧红,刺入股内……
张汝南同样记有 “跪火链”、“烁铁熨背”、“灼锥刺臂股”,以及另一种鞭刑后的火刑:
竹?鞭背,上鹰架,绳缚手足将指而悬之,纸燃烧油滴鞭破处。
太平刑罚之严刻,溯其由来,当是服膺法家思想所致。我们曾介绍了商鞅的“怯民使以刑,必勇”,“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的重典治国路线。然而,商鞅重典治国仍注意刀刃之上的力度,求其轻重有别,真正收威慑作用。太平天国却有些不分轻重缓急,一味从重。虽然酷刑之外,太平天国刑罚也有常规或习见的一面,如斩首、枷号、杖责诸样式,且应说此系主流,酷刑只施诸某些特别严重的罪行和特别危险的罪犯。但终究来说,太平天国对于治罪,总难抑其打破常规、不循常理的任性,所以即便习见的样式,运用上也惊人地表现出轻重失宜、无所顾忌的特色。比如斩首,作为死刑在古代确属普通,然而太平天国用法却极夸张。张德坚注意到,“毛细之过,笞且不足,贼辄律以斩首。 ”亦即通常来讲的轻罪,太平天国往往以问斩伺候。《贼情汇纂》所列六十二条刑律,处以“斩首不留”的居然多达四十二条,庶几无罪不斩。且举数例:“各衙各馆兄弟”如果发生“口角”和“斗架”,将“不问曲直,概斩不留”,亦即只要发生这种事,并不区分谁对谁错,全部斩首;所有兄弟,必须严格呆在本馆,不得“私自过馆”即私自造访别馆,或在彼处“留宿”,“违者斩”;必须熟背“赞美天条”,如“超三个礼拜不能熟记”,“斩首不留”;遇各王及丞相级别官员轿出,必须回避,如果冲撞,“斩首不留”此条应是对丞相以下各官而言;“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斩首不留”;在“朝会敬天父”的场合,如有人喧哗,“斩首不留”;“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因两情相悦而“和奸”,“男女皆斩”;私藏金银和剃刀,就视为“变妖”,“定斩不留”;不准剪发、剃胡须和刮脸,这属于“不脱妖气”,“斩首不留”;吸鸦片必斩,“吸黄烟”的普通烟民,初犯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打一千枷三个礼拜,第三次“斩首不留”;“凡传令讲道理”亦即革命宣传活动,“有无故不到者”,枷七个礼拜打一千,“再犯斩首不留”;军中不能搞文艺创作,凡有“编造歌谣及以凡情歪例编成诗文,迷 兄弟者”,“斩首不留”;如果对挖筑工事等军中事务 “口出怨言”,“斩首不留”;胆敢“辱骂官长者”,“斩首不留”;“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妖书”必须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文娱活动“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凡朝内军中如有兄弟赌博者,斩首”……
以上情形,通常多罪不至死,甚或连处分也够不上,仅予批评教育即可,太平天国则一律视作“活罪难容”。这不特有违常情,考虑到太平天国的信仰,更是大拂基督戒杀之训。《资政新篇》劝说洪秀全慎刑的理由之一,就是基督的教义,“以少符勿杀之圣诫焉”。但遭断然拒绝:“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天法杀人”,就不算“妄杀”。又说:“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味其语意,认为“天妖斗争”尖锐残酷、你死我活,容不得温良恭俭让。总之洪秀全思想里暴力因子突出,认为必须杀杀杀,方能杀出一个新天地。
人的心灵和意念,非凭空而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言行,貌似发乎己身,实则是社会现实、历史文化预先书写的结果。说到嗜杀,中国有此传统无疑,每逢王朝崩解,很少不伴随杀戮甚惨时光。东汉末年、西晋八王之乱后的北方,以及明代尾声等,都曾有杀人如麻的嗜血狂魔。此即为何鲁迅笔下“狂人”,将史书翻来覆去最后只读到“吃人”二字。中国书籍,正史也好演义也罢,里面杀气都很重。洪秀全眼中历史更迭、正邪冲突,离不开砍砍杀杀,显有历史的阴影。之前我们分析,他梦里大战妖魔,“三十三天逐层战下”,活脱脱是《西游记》天兵天将捉拿妖猴之翻版,说明历史文化对他脑子里“成像系统”的作用。进而具体验视太平天国刑罚,像“跪火链”、“烁铁熨背”、“灼锥刺臂股”之类酷刑,严格来讲亦非新发明,在民间因果报应幻说以及所想象的“十八层地狱”景状里,早有类似的描画,太平天国无非是将幻说搬入现实而已。然而事皆有两面。中国历史文化固随处可见毒虐笔触,可是要求克制暴力的思想和声音并不弱。不单儒家要求仁爱治天下,道家也强调“贵生”。故而即便“虎狼之秦”犹有吕不韦一派,主张“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害于生则止”,劝诫君主奉“贵生之术”。北宋时,苏轼曾总结到他那个时候为止的中国历史,说:“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秦、晋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杀不已,故或合而复分,或遂以亡国焉。”这样的道理,在中国也源远流长、代有传人,并不输于对暴力的崇尚,所以中国史能够涌现贤明如汉光武帝、宋仁宗的人主,而不只有石虎、张献忠之类暴虐强人。可见历史文化善恶并现,何去何从,仍视乎自我选择。
洪秀全对于历史不认为应以善制恶,而信以暴抗暴,或许还可推求于个人原因,即精神专家所断言的其人格与心理带有病态倾向,使他更难以积极的目光面对世界、借鉴历史。自他著作来看,他对中国历史几近一笔否定,尚未否定者,仅限于不可鉴知的上古——“坏自少昊时”,少昊以下一团漆黑。这意味着中国历史良善之一面,他都拒不承认了。由此带来一个教训,一味反历史,往往失去择善相从的明智,从而受到毁坏的欲望的掌控。不能不说,太平天国对罪与罚的观念,打上了洪秀全个人心态的烙印。太平刑罚拒不参酌、依循通行的法理和视点,尺度任意,从心所欲,跟洪秀全排拒历史的言谈是相一致的。
人类立法,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犯罪问题加以总结和摸索,提取理性认识,而形成有其规律与沿革的体系。国有兴亡,代有移换,法理精神与认识却体现出恒通性,不随江山易代而弃废。以清朝为例,它作为异族入主中原,在敲订《大清律》时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今法司所遵及故明律令,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
以明朝旧法为基础,结合自身需要,有依有违,有增有损,完成《大清律》撰修。虽然清之于明本是敌国,但考虑法制时却未因此刻意相拗。此盖因法律作为历史结晶,非某朝之私货,是代代延传增损而来。清律所继承的貌似为明律,实际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法制的通识。何止明清之间,我们看今天世界各个国家,虽然意识形态或至相左,但考其法律制度,对罪与罚的认知及绳衡,共性都大于差异性。总之,法律制度愈是接近于“放之四海而皆准”,愈表明其理性意味较强,较能涵盖和反映一般人性尺度;凡是过于别出心裁或另类的情形,不可避免都对法的正确性和正当性有所斫损。
太平天国法制偏于后者,“破”字当头,不肯准古酌今。我们不仅要知其如此,更须探它所以如此的原因。
一来,太平天国有一种情怀,自命为开天辟地,以为将要创造人间前所未有的崭新国度,因而对旧律陈规不屑理会。二来,它不把立法的基点,置于犯罪现象与社会之间利害关系的理性、精细评估,而是先入为主,将拜上帝教教义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很多从社会危害性看通常是轻微罪衍以至非罪的现象,从教义的角度都变为重罪,致其设刑不可理喻。三来,是实用主义倾向过于严重。我们说法律不妨服务于政治现实,但不可为政治捐弃理性观照下的公平正义尺度,太平天国为求政治功用则不惜乱立名目、夸大性质,视法律如政治奴妾,致使法律自身无尊严可言。四来,对法的认识存在根本错误,缺乏辩证观念,一味寡恩、不知市恩。凡属良法都应宽严相济、有张有弛,借此分寸真正收其绳墨社会之效。太平刑律却惟知凶暴、务求刚猛,这种认识不特极为表皮,且根本处在误区。
以上四者,令刑罚在太平天国成为一件乖序失常、怪状奇形之事。典型的如夫妻之间幽会“男女皆斩”,此等罪名与处置,仅出于禁欲戒令和捍卫男女分营制度,罔顾天伦,根本到了逆天的地步。余如口角、打架当斩,劳累有怨言当斩,未能熟记 “赞美天条”当斩,作诗、吟曲、演戏都要斩首……环顾人间,古往今来,法度从未至于如此之滥。有些条文,本意虽好,如禁止劫毁民财民物等,然而概以问斩对待,亦殊为无理。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动辄置之死地,似乎会使治国治军变得容易,但公正全失,归根到底必“得”不偿“失”。法律一旦不讲“理”,无异于自为废纸。失当之法,绝不可能抑制犯罪,只会增加犯罪。太平天国后期,公开无视、逾越律例的行为,从吸烟、饮酒到侵掠民财、“强带外小”,形形色色, 拾即是。表面看是法纪弛涣所致,往深处追究,不得不说那些异于常情、悖乎常理的约束,人们从内心就无法报以敬畏信服。
在此顺而谈谈太平天国与两性有关的问题。
太平军视男女为大防,迄至杨秀清颁 “给配令”,禁家室、禁婚姻、禁私情;设男馆、女馆,男女分营,这种制度似乎直到“给配令”后,仍维持不变。由此造成形形色色犯罪,涉性罪名也因而在刑罚中占有一突出位置。然而两性问题除了造成犯罪,还带来很多复杂的现象或奇特景观,是太平天国时期非常值得关注的侧面。
比如太平军中“娘子军”的存在,颇有人目作“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之类的表征,至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男女平等是它的革命政纲之一”、“是妇女解放思想的第一个实行者,这样广大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真是人类最光荣最先进的运动”。 美誉之丕扬,措辞之热烈,令人咋舌。
其实,太平军并非清一色男性,乃关乎两点。一是“举家团营”政策所致。金田起义动员投营者阖家加入,既基于规避官府迫害,次者也是出于聚拢财力物力和根除家庭羁绊,令会众舍“小家”就“大家”,正如李秀成所说:“将里内之粮谷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山,亦被拿去……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具(俱)要放火烧之”,这是太平军形成拖家带口局面并衍生“娘子军”的真实原因。二则离不开客家风俗这一背景。两广客家,女不缠足甚至光脚,日后江南士民见了彼等每呼“大脚蛮婆”。她们吃苦耐劳,登山涉水、负重挑担、力耕采薪,无不能为、无不能至,数百年来旧俗如此,并非太平军加以“解放”的结果。相反倒应该说,“举家团营”策略成立,系以客家女人独特风貌为前提。设若太平起义不举于两广,而换作中原江南地带,以妇女普遍缠足、三寸金莲移步维艰的景状,即欲“举家团营”,在流徙千里的前途考验面前,也必然难克其成。
故而太平军之有女流,自起因来说,与“妇女解放”八竿子打不着。至于“男女平等”,尤不知从何谈起。那些引吭讴歌的学者,莫非没有读过洪秀全的数百首诗篇?里面歧视女性、男尊女卑的言辞,比比皆是。姑拈数例:
尔为夫主心极真,永配夫主在天庭。尔为夫主心极假,贱莫怨爷莫怨姐。
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大福薄福自家求,各人放醒落力修。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摘不胜摘,引不胜引。
又以所谓“一夫一妻制”,指证“男女平等”。诚然,这种条文可以找见,例如:“一夫一妻,理所宜然。”但引用者往往藏头露尾,孤立地摘出一句,同时对太平天国基本婚配制度避而不谈。婚姻在太平天国断非为“男女平等”而设,实际上它反而是严苛等级关系的产物与体现,妻房数量与爵秩品级挂钩,地位越高,可拥有妻妾配额则愈多,往下递减,及至下层卒众,则减为一夫一妻。众所周知,天王陛下“娘娘”无数。又一证据是1862年左右洪秀全曾颁《多妻诏》,正式公布可依官阶大小享受的妻子数额:
今后均须依照朕谕,妻数应依官阶大小而多少不等。朕诏婚配情况如下:朕长、次兄以及干王、翼王、英王、忠王、赞王、侍王、辅王、章王、豫王,不足六妻者,自行择配,共迎朕之寿辰,届时,望各官员补足其数。
白纸黑字。面对此诏,凡噪呼太平天国行“一夫一妻制”者能不赧颜?诏中还特别补充说:“此诏前已逾所允之数者,朕宽容之。”说明高级干部早就私自过上一夫多妻生活,此诏不过是追认而已。
所谓“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神话,应该散作烟云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妇女“地位”提高。此又如何呢?
论及此点,曲意回护者也很眉飞色舞——理由是太平天国有女官和女官制度。自古,出来做“公家人”、吃“公家饭”、封官晋爵的,没有女流之辈。偶尔出现一个例外,比如大周皇帝武 御前,据说有个“代天子巡方”的女官谢瑶环,当年田汉如获至宝,拿她编了一幕大剧。类似这样的角色,在太平天国却非零星一二,而是成批成群。难道这不是妇女地位空前提高的标志么?
我们仍不急于结论,先把事情弄清。
里头要点有二,一是太平天国为何能有女官?二是太平天国拿她们来做什么?对于第一点,又得提到“大脚蛮婆”的特性。她们在故里及家中,原是顶天立地的模样,很能任事,客家男人亦不觉得让她们独当一面有何不可。这是先决条件。对第二点,太平天国用女官究竟是对她们刮目相看,还是有些事非她们不可?这就要按实详究。在记载中,太平天国女性几乎做过所有事,包括搬砖、砍柴、割麦等各种重体力活。只不过,这些职役近乎苦力,还不能视为妇女“地位”提高的证明。有辨析必要的,应是客家“老姊妹”中间被恩赏了“指挥”、“将军”等职的那群人。她们得职的原由,从史料看似非积军功所致,否则总会有一些女战士陷阵杀敌的突出故事流传,但我们几未见过这样的报道。所以,她们相对高的授职应是出于其他作用的任命。这里“其他作用”,划分一下,盖为三种:一、女营管理;二、女监工;三、女内侍。
男女不得私相授受,分馆而居,它的实施需要大量女营管理人员,且只能由女性充当。这是太平天国庞大“女干部”队伍的第一个由来。《金陵杂记》述之:
每馆定以二十五人,其中立馆长,亦谓之两司马。或十余馆,或数馆,有一贼妇督之,谓之女伪百长,即伪卒长。其上又有女伪军师(应为“军帅”之误)、女伪总制等贼婆,皆广西山洞泼悍大脚妇女为之。
女官名称有“司马”、“百长”或“卒长”、“军帅”、“总制”,与男营相同。
日常另一用得着“女干部”的地方,是监工。太平天国强迫所有女馆居民劳动,从挖沟、运输、伐薪、割麦到纺织等,所有这类场合,皆须人布置、督持、验看,单是女馆两司马显然不够,需要另外委员司事。且不言而喻,凡此辈,亦非得是女性。以织工为例,派设专员如下:
设女锦绣指挥二百四十员,职同指挥,女锦绣将军二百员,职同将军,女锦绣总制一百员,职同总制,女锦绣监军一百六十员,主督各妇女制刺金?冠服的工作。
最后一处大量需求女官的地方,当然是天王宫和诸王府。天王宫除洪氏父子自己,以外概为妇女,甚至护弁亦系裙钗。其所设女官,“宫禁城女检点自左一右二次至三十六,共三十六员。女指挥自左一右二次至七十二,共七十二员。女将军分炎、水、木、金、土正副,共四十员”。又有供奉各种杂务的女侍应,“设有统教、理文、理袍、理靴、理茶等女官,惟员数官阶都不详”。记载中说,天王宫“其凤门以内,皆系贼妇在内,以供洪逆役使”,乃至造屋起殿这种高强度工作,亦由女人承担:“贼妇中并有能造房屋者,去冬洪逆住处失火,烧去楼房数间,传闻旋经贼令木匠将房架造成送入,贼妇即在内盖成房屋。”不但天王宫纯用女官,诸王府亦然。韦昌辉北王府:“其中妇女亦不下数百人,门内除韦逆外,别无男人。”翼王府“其中妇女亦有数百,时常骑马出入”。秦日纲燕王府“选服侍妇女多人,类皆广西大脚者多”。诸王府女官设职比照天王宫,员额品级相应减降。例如:“天朝内掌门,东殿、西殿内贵使,都职同检点。东殿、西殿内掌门,南殿、北殿内贵使,都职同指挥。南殿、北殿内掌门,翼殿内贵使,都职同将军。翼殿内掌门,燕第内贵使,都职同总制。 ”
由这三种主要用途,终于生成了太平天国极具规模的女官群。《贼情汇纂》卷十一,列有太平天国各类女官的详细数目,其中“伪女卒长一千人”,与谢介鹤所述接近;而“伪女管长”亦即“两司马”之职为“四千人”;再加上其他各官,太平天国女官总数为“六千五百八十四人”。这是截止于1855年的记录。
综上可知,太平天国大量使用女官且形成制度,殊非有意提高妇女“地位”,实出乎不得己。倘若不搞“女性干部队伍建设”,“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就没法实施。好在机缘凑巧,客家女人不裹脚、能任事的特质,刚好很堪驱驰。
话题未完,还要继续深挖——大量需要女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秘密。我们已经知道,天王宫中以及权贵府邸,乃女官充职之一大去处。有些野史涉笔及此,故弄玄虚,导人淫邪之思。然而,天京深宫高墙之内性别比例的巨大悬殊,与所谓欲壑难填基本无关。实际上,它关乎一个难言之隐。
那就是:对宦官苦不能致。
汪堃《盾鼻随闻录》,两次出现太平军阉不得法记录。卷五提到杨秀清曾“阉割幼童,十难活一”,复于卷八又说:“贼取十三四岁幼童六千余人,尽行阉割,连肾囊剜去,得活者仅五百余人。”如果私家笔记不足凭信,那么再看《贼情汇纂》的记载:
癸丑八月杨逆下令选各馆所掳幼孩十二岁以下、六岁以上者二百余人阉割之,欲充伪宦官,因不如法,无一生者。杨逆知不可为,又诡称天父下凡指示,再迟三年举行,以掩群下耳目。
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即1853年,南京太平军入城半年后。有年龄范围,即十二岁以下、六岁以上未成年男童。还有被用于阉割试验的具体人数:二百余人。以此验诸《盾鼻随闻录》,知其确有讹失之处——将试阉对象说成六千人,过于夸大;又说存活者十能有一,岂非犹有成功之例?至《贼情汇纂》明指“无一生者”,始与理相合。我们多次讲过,《贼情汇纂》是应曾国藩之命结撰的调研报告,注重情报价值,没有必要捏造事实,所涉内容悉有文书、采访为凭,故敢称“事务求实,不尚粉饰”。 此书既将试造太监未果之事写入,就可以断定并非谣传。
事情的可信度,亦能于反方向求证。天王及以下各王,对于有宦官在宫府供役的需求,极为强烈。癸丑年1853正月二十八日,由武昌兵发南京途中,洪秀全发下诏旨,专申宫禁之严:
咨尔臣工,当别男女,男理外事,内非所宜闻;女理内事,外非所宜闻。朕故特诏,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内言永不准出。今凡后宫,臣下宜谨慎,总称娘娘。后宫姓名位次永不准臣称及谈及,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各名位次者斩不赦也。后宫而(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不赦也。后宫声永不准臣下传,臣下女官有敢传后宫言语出外者斩不赦也。臣下话永不准传入,臣下话有敢传入者传递人斩不赦,某臣下斩不赦也。朕实情诏尔等:后宫为治化之原,宫城为风俗之本,朕非好为严别,诚体天父天兄圣旨,斩邪留正,有偶不如此,亦断断不得也。自今朕既诏明,不独眼前臣下宜遵,天朝天国万万年,子子孙孙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语也。内宫与外臣,一般的敬避之规虽属必要,但如此忮刻,以至于言及姓名位次即死、瞄一眼即死之类,真可谓匪夷所思。我们以清宫为例。清宫有“垂帘仪”:“凡召见、引见,仍升座训政,设纱屏以障焉。”即,外臣可以抬头、与后妃照面,二者间纱屏相隔,以增朦胧。对比之下,洪氏忌褊之心未免世所罕见。
透过这道诏旨,足可想见思求宦官之渴,也足可想见使能握得阉割之术,将何等欢欣鼓舞。问题又回到了一个相似之点,前面讲到凌迟不见诸太平极刑与人才和技术有关;此刻,拿二百余名男童做实验竟“无一生者”,正好两相辉映。明末,沈德符从南方赴京,一过河间、任邱以北,时于“败垣”之中得见自腐之辈,他心惊肉跳写道:“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之侧,他日将有隐忧。”可知首善之区周边,连民间都已掌握了阉割之法。只是“帝都”几百年独特历史的氤氲造化,别处不能望其项背。杨秀清试阉全败,证明至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从两广到长江流域这一带,阉割术仍是没有破解的秘密。
中国正史都有“志”的板块,其中一项内容曰“职官”,而“职官”必讲到宦官。 《清史稿》里,这个部分称“内务府”,列于卷一百十八志九十三职官五。假设今人援古例为太平天国修史,则相应部分的组成人员,便是天王宫及各王府里那些女流之辈。她们除开“内掌门”、“内贵使”等官衔与历代有别,功能及角色可以说一模一样、不分轩轾。易言之,她们无非就是清朝内廷的敬事房、御膳房、掌礼司、尚衣监以及总管、副总管之类,抑或明代“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以及提督、掌印、秉笔太监之类。惟一不同,是明清此类机构人员由阉后男宦充任,太平天国因不能阉腐,不得已由女人充任。
注释:
(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二刑考一,页4838。
(2)同上,页 4837。
(3)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页 227。
(4)同上。
(5)同上,页 229。
(6)同上,页 227。
(7)《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页4199。
(8)同上。
(9)《中国历史大辞典》“凌迟”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页 2502。
(10)沈梓《避寇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八)》,页 57。
(11)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上海出版公司,1952。
(1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页227。
(13)《李秀成亲供手迹》,排印文,页 41。
(14)转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页1181。
(15)赵烈文《能静居日记》,页 739。
(16)《李秀成亲供手迹》,排印文,页 37。
(17)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 537-539。
(18)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页716。
(19)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同上书,页662。
(20)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同上书,页716。
(2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页227。
(22)同上,页 228-232。
(23)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 538。
(24)同上。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 538。
(2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18。
(26)《吕氏春秋集释》, 中华书局,2013,页38。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中华书局,2012,页 5。
(28)《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二,志一百十七,页4182。
(29)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1,页186。
(30)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三联书店,1955,页 318。
(31)同上,页 340。
(32)《李秀成亲供手迹》,岳麓书社,2014,排印文,页01-02。
(33)《天父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页 436。
(34)同上。
(35)同上,页 438。
(36)《国宗提督军务韦石革除污俗禁娼妓鸦片黄烟诲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90。
(37)《多妻诏》,《洪秀全集》,页 206。
(38)同上。
(39)涤浮道人《金陵杂记附续记》,同上书,页622。
(40)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卷二十八,页1024-1025。
(41)同上,页 1024。
(42)同上,页 1025。
(43)涤浮道人《金陵杂记附续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页627。
(44)同上,页 628-629。
(45)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卷二十八,页1024。
(46)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页309。
(47)汪堃《盾鼻随闻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页 398。
(48)同上,页 424。
(49)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页326。
(50)张德坚《贼情汇纂》凡例,同上书,页34。
(51)《天命诏旨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页 69。
(52)《清史稿》卷八十八,志六十三,页2619-2620。
(5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六,中华书局,1997,页 178-179。
(54)《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中华书局,2013,页 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