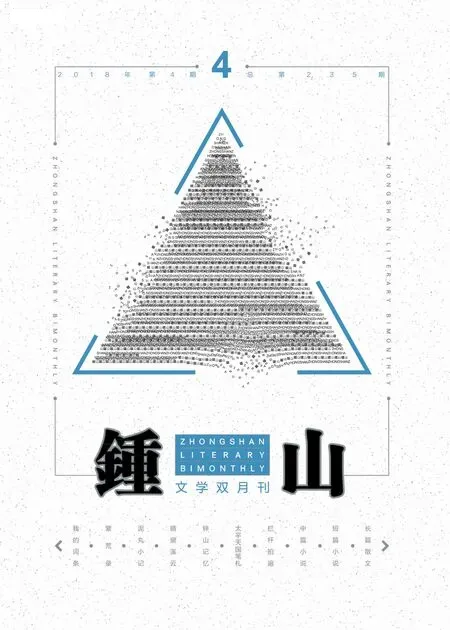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
王彬彬
WANGBINBIN
一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清末的变法维新运动中,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在《钟山》2018年第2期发表的 《陈宝箴的喉骨》一文,对此有所评介。但陈宝箴还是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中医,能够为人处方看病。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字琢如)是乡间名医,陈宝箴继承了父亲在医学方面的志趣。而陈宝箴对中医的兴趣也为儿子陈三立所承袭。陈三立同样具有为人看病开药的本领。所以,义宁陈氏,其实是中医世家。陈三立之子陈寅恪,从小耳濡目染,对中医也了解甚深。对中医,陈寅恪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清末政坛有轰轰烈烈的表现,也与其时政坛上清浊两类人物都多有瓜葛。陈寅恪晚年,曾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记述和评说清末政坛状况及祖父和父亲在清末政坛的所作所为。据陈寅恪门人蒋天枢说,此稿作于1965年夏至1966年春,是陈寅恪最后之作。这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目录如下:
弁言
(一)吾家先世中医之学
(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
(三)孝钦后最恶清流(佚)
(四)吾家与丰润之关系(佚)
(五)自光绪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间清室中央政治之腐败(佚)
(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
(七)关于寅恪之婚姻(佚)
正文原有七个部分,三、四、五、七四个部分都在混乱中散失了。现存者是经蒋天枢整理的残稿。在《弁言》中,陈寅恪说:“今既届暮年,若不于此时成之,则恐无及。因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证诸史料,参以平生耳目见闻,以阐明之。并附载文艺琐事,以供谈助,庶几不贤者识小之义。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知我罪我,任之则已。 ”又说:“清代季年,士大夫实有清流浊流之分。寅恪本人或以世交之谊,或以姻娅之亲,于此清浊两党,皆有关联,故能通知两党之情状并其所以分合错综之原委。因草此文,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他日读者倘能详考而审察之,当信鄙言之非谬也。”陈寅恪要以乃祖乃父的事迹为中心,对晚清政坛清浊两党做一评说,并且自信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立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然而,这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却首先说的是自家的“家学”:“中医之学”。曾祖、祖父、父亲三代俱习中医,俱能处方治病,实在与清末政治没有什么关系。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中医知识,与他们的政治作为、与清季政坛之清浊,也实在看不出有何牵扯。陈寅恪首先述说“吾家先世中医之学”,岂非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但陈寅恪何许人,岂会犯博士买驴的错误?此中或有深意存焉。此一层,最后再说。
第一部分“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一开头写道:
吾家素寒贱,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逃虚所谓读书种子者。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曾撰三国志中印度故事、崔浩与寇谦之及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法曲篇等文,略申鄙见,兹不赘论。小戴记曲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曾祖至先君,实为三世。然则寅恪不敢以中医治人病,岂不异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女流求,虽业医,但所学者为西医。是孟子之言信矣。
又说:
中医之学乃吾家学,今转不信之,世所称不肖之子孙,岂寅恪之谓耶?
这里主要表达了三种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自家虽然自曾祖至父亲,三代俱通中医,自己也读过不少中医古籍,然而,自己却并不相信中医。中医固然有见效之药,但却无法用科学理论进行解释。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区,不得已而用中医,自然是可以的,但如果把中医矜夸为“国粹”,让中医凌驾于西医之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第二层意思是,自己虽然读过不少中医古籍,但却不敢像曾祖、祖父和父亲那样为人看病开药。虽然是中医世家,但自己的长女流求却学的是西医,所以,自己是家学的背叛者,是不肖子孙。第三层意思尤为重要,那就是所谓中医,也并非完全是中土的产物,在理论和方药两方面,都颇有域外传入者。换句话说,所谓中医,也并非纯粹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
二郭嵩焘是陈宝箴挚友。当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锐意革新时,郭嵩焘多有赞助。郭嵩焘曾为陈宝箴父亲陈伟琳撰墓碑铭,其中写道:
江以西有隐君子,曰陈琢如。先生讳伟琳,系出江州,世所称义门陈氏者也。先世有仕闽者,遂为闽人。祖鲲池,由闽迁江西之义宁州,再传而生先生。考克绳,以孝义,生子四人,先生其季也。始六七岁,授章句,已能通晓圣贤大旨。端重简默,有成人之风。及长,得阳明王氏书读之,开发警敏,穷探默证,有如夙契,曰:“为学当如是矣!奔驰夫富贵,泛滥夫词章,今人之学者,皆贼其心者也。惟阳明氏有发聋振瞆之功。”于是刮去一切功名利达之见,抗心古贤者,追而蹑之。久之,充然有以自得于心。一试有司,不应选,决然舍去,务以德化其乡人,尤相奖以孝友。其事父母, 力壹心,承顺颜色,不言而曲尽其意。母谢太淑人病亟,夜驰二十里,祷于神。比反,太淑人寐方觉,言神饵我以药,疾以霍然。先生以太淑人体羸多病,究心医家言,穷极《灵枢》、《素问》之精蕴,遂以能医名。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诊无倦。自言:“无功德于乡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尽也。”
这让我们明白,陈家先前便是江西江州人,后来因为有人在福建做官,一度徙家福建。到了陈伟琳的祖父一代,又从福建迁回江西。陈伟琳的父亲名克绳,生子四人,伟琳是最小的儿子。伟琳之所以研习起医学,是因为母亲体羸多病。为治母病而学医,卒成地方名医,以至于“病者踵门求治”。
伟琳的中医之学,传给了儿子宝箴。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记述了几件祖父在中医上的表现。翁同騄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正月二十日”条云:
晚访陈右铭,未见。灯后右铭来辞行,长谈。为余诊云,肝旺而虚,命肾皆不足,牛精汁白术皆补脾要药,可常服。(自注:脉以表上十五杪得十九至,为平。余脉十八至,故知是虚。)宝箴字右铭。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这一年,是宝箴春风得意的一年。1893年,宝箴被任命为直隶布政使,并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宝箴被任命为东征湘军的粮台,驻守天津。此时,宝箴已准“专折奏事”。1895年秋天,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为翁同騄把脉疗疾时,应该尚在粮台任上。正月二十这天,太阳落山时分,翁同騄拜访陈宝箴,未遇。掌灯后,宝箴回访兼辞行,二人长谈。长谈中,宝箴大概看出翁同騄气色不佳,于是主动提出为其把脉。翁同 曾任帝师,此时是军机大臣。陈宝箴敢于为其把脉开药,可见他对自己的医学是很自信的。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又说:
犹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先祖擢任直隶布政使,先君侍先祖母留寓武昌,……一日忽见佣工携鱼翅一?,酒一瓮并纸一封,启先祖母曰,此礼物皆谭抚台所赠者。纸封内有银票伍百两,请查收。先祖母曰,银票万不敢收,鱼翅与酒可以敬领也。佣工从命而去。谭抚台者,谭复生嗣同丈之父继洵,时任湖北巡抚。曾患疾甚剧,服用先祖所处方药,病遂痊愈。谭公夙知吾家境不丰,先祖又远任保定,恐有必需,特馈以重金。寅恪侍先祖母侧,时方五六岁,颇讶为人治病,尚得如此酬报。在童稚心中,固为前所未知,遂至今不忘也。
这说的是陈宝箴为时任湖北巡抚的谭继洵 (谭嗣同之父)治病之事。陈宝箴任直隶布政使,在光绪十九年,陈寅恪记忆略有误。北上任职前,陈宝箴是湖北布政使,居家武昌。北上时,家眷未随行,仍留居武昌。陈宝箴治好了谭继洵的重病,于是谭继洵差人送上鱼翅、美酒和重金。陈寅恪时方五六岁,颇惊异于为人治病竟获如此厚报。
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还说了这样一件事:
又光绪二十五年先祖寓南昌,一日诸孙侍侧,闲话旧事,略言昔年自京师返义宁乡居,先曾祖母告之曰,前患咳嗽,适门外有以人参求售者,购服之即痊。先祖诧曰,吾家素贫,人参价贵,售者肯以贱价出卖,此必非真人参,乃荠絇也。盖荠絇似人参,而能治咳嗽之病。本草所载甚明(见本草纲目壹贰“荠絇”条)。特世人未注意及之耳。寅恪自是始知有本草之书,时先母多卧疾,案头常置本草纲目节本一部,取便翻阅。寅恪即检荠絇一药,果与先祖之言符应。是后见有旧刻医药诸书,皆略加批阅,但一知半解,不以此等书中所言为人处方治病,唯藉作考证古史之资料,如论胡臭与狐臭一文,即是其例也。
戊戌政变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被朝廷革职。1898年11月,陈宝箴携眷定居于南昌。这里说的,便是陈宝箴闲居南昌时对诸孙回忆旧事。荠絇似人参而能治咳嗽之病,是《本草纲目》上写明了的,但“世人未注意及之”。而宝箴一听母亲以贱价购得人参并且果然治愈咳嗽之症,便知此必非真人参而实为荠絇,可见其中医素养超乎流俗。陈寅恪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此时年方九岁,但已知有《本草纲目》一书。九岁的寅恪,听了祖父对于荠絇的介绍后,居然想到查阅《本草纲目》以验证祖父之言,宜乎日后成为学术大家。而且,从此以后,见到旧刻医学书籍,都要看一看。虽然寅恪自谦曰一知半解,但以他的资质,读了许多中医古籍,对中医的知解决非很粗浅。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没有提及父亲陈三立为外人处方治病事,但说到了他常给儿子看病开药:
寅恪少时多病,大抵服用先祖先君所处方药。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移家江宁,始得延西医治病。自后吾家渐不用中医。盖时势使然也。
寅恪儿时生病,都由祖父和父亲以中医诊治。可见父亲三立也是能开药方的。1900年,陈三立携眷移居南京。自此家中有人生病,便请西医治疗。1900年便能放弃中医而信任西医,是不容易的,而作为中医世家,能断然舍中医而就西医,就更是难能可贵了。陈三立在父亲主导的湖南新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非偶然。
三陈寅恪虽然自幼便读中医古籍,读了许多,具备丰富的中医知识,但却并不以此为人疗疾,只是把中医知识用于历史研究。应该说,中医方面的学养,帮助陈寅恪弄明白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方面的广博知识,又让陈寅恪对中医发展史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下面,对陈寅恪涉及中医的几篇文章略作介绍。
(一)《狐臭与胡臭》
此文颇短小,才一千多字,原刊1937年6月出版的 《语言与文学》,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的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
《狐臭与胡臭》一开始写道:“中古华夏民族曾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近世学人考证之者,颇亦翔实矣。寅恪则疑吾国中古医书中有所谓腋气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或与此端有关。”陈寅恪在中古医书中发现“腋气”病名,又称“狐臭”。他想到中古时期华夏民族曾与“西胡”混血,便疑“狐臭”之病,源自“西胡”,而本来称“胡臭”,后来才衍变成“狐臭”。
陈寅恪首先纠正了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和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关于“狐臭”(“胡臭”)叙说的错误。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狐臭”条云:“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而此气能染,易著于人。小儿多是乳养之人先有此病,染著小儿。”这种关于“狐臭”的描述,基本是胡说了。陈寅恪指出,巢元方认为患腋气者“腋下有如野狐之气”,所以又称“狐臭”,这在字面上虽然说得通,但其实是在望文生义。欧美之人,当盛年时,大抵有腋气,与血气不和也没有关系。至于说“狐臭”具有传染性,也是谬误。孙思邈《千金要方》论“胡臭”:“有天生胡臭者,为人所染胡臭者。天生臭者难治,为人所染者易治。”“胡臭”都是天生,没有后天染上者。孙思邈所说也颇谬。
陈寅恪指出,南宋杨士瀛所撰《仁斋直指》中有“腋下胡气”条目,并为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沿用。 “胡臭”之“胡”,自然是“胡人”之“胡”。古代“胡”“狐”二字虽可通用,但在《千金要方》《仁斋直指》《本草纲目》编撰之时,却不可认为“胡”乃“狐”之同音假借;诸书都写作“胡”而不写作“狐”,也不可认为是音近而讹写。实际上,在古代,所谓腋气一病,尚有“胡臭”与“狐臭”两种称谓并行。
陈寅恪又举了两个古籍所载身有“胡臭”而有“胡人”血统者的例子。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断定有“胡臭”者就必定有“胡人”血统。陈寅恪说:
……证据之不充足如此,而欲依之以求结论,其不可能,自不待言。但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又可考者,恐不易多得。即以前述二人而论,则不得谓腋气与西胡无关。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而且正确欤?
借助中医旧籍中关于腋气的介绍,陈寅恪指出腋气本来是“西胡”人种独有,所以,有“胡臭”之名行世。后来,当华人与“西胡”混血之后,后代便也有人体有腋气,再称之为“胡臭”便不合适了,又因为腋气之症颇似野狐之骚,便改“胡臭”为“狐臭”了。
(二)《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此文原刊《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的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
这篇文章,指出《三国志》中作为真实事迹介绍的曹冲和华佗的故事,有的其实是来自于佛教读物,是把佛教读物中的神话故事,嫁接到曹冲、华佗身上而已。文章一开始说:
陈承祚著三国志,下笔谨严。裴世期为之注,颇采小说故事以补之,转失原书去取之意,后人多议之者。实则三国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特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者耳。陈寿(承祚)著《三国志》,以态度谨严为人称道。裴松之(世期)注《三国志》,常常援引小说故事来补充本文叙述,也因此时常遭到后人的讥嘲。因为小说故事往往出自想象虚构,不能视作历史事实。然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三国志》本文中叙述的故事,有些也正是来自于佛教的神话传说。
《三国志·魏志》说曹操之子曹冲从小便异常聪慧,有成人之智。有一次,孙权送来一头大象,曹操想知道其重量,遍询诸人,无人能想出称量的办法。曹冲说,置大象于大船之上,在吃水线上刻下印痕,然后称物入船,便能得知大象的重量了。曹操大喜,即依法而行。这就是著名的曹冲称象的故事。后人往往信以为真。陈寅恪指出,这故事其实出自北魏时期译出的《杂宝藏经》。《杂宝藏经》云:
天神又问,此大白象有几斤?而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天神。
陈寅恪指出,《杂宝藏经》虽然到北魏时期才译出,但此书原本杂采诸经而成,其中所载故事,别见于中国先后译出之佛典中。所以以船称象的故事,完全可能先于《杂宝藏经》而传入中国。如果找不到先于《杂宝藏经》传入中国而载有此故事之佛典,那也不能证明此故事绝对没有先期传入,因为载有此故事之书完全可能已经亡逸而无可查考。并且:“或虽未译出,而此故事仅凭口述,亦得辗转流传至于中土,遂附会为仓舒(引按曹冲字仓舒)之事,以见其智。但象为南方之兽,非曹氏境内所能有,不得不取其事与孙权贡献混成一谈,以文饰之,此比较民俗文学之通例也。”
那时的人们为了夸饰曹冲之智,遂把佛经中的故事粘贴到曹冲身上。又因为曹操统治的地域,不可能有大象,便拉扯上南方的孙权,说大象是孙权赠送。《三国志》有“华佗传”,其中关于华佗行状的叙述,很多也来自佛教典籍,并“华佗”这个名称,也源自天竺语(梵文)。《三国志·华佗传》中说,华佗字元化,深谐“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其年已过百,但仍是壮年之态。华佗精通医术,为人治病,往往药到病除。华佗还擅长“外科手术”。如果病“结积在内”,针灸、服药俱无用,必须“刳割”(开刀),便先让病人服下“麻沸散”(麻醉药),病人立即便如醉死一般,失去知觉。于是华佗便“破取”,也就是切开身体。如果是肠子有病,便把有病的那段剪下来“湔洗”,然后再缝上去。病人不醒不痛,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一个月后伤口便恢复如初。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人患咽喉堵塞病,食物不得下咽。家人用车子载着欲往就医。华佗听见呻吟声,停车往视,对那人说:“刚才路过的地方,有一卖饼家有蒜泥姜汁大醋调和的佐料,你去弄得三升饮下,病便好了。”那人依言而行,“立吐蛇一枚”。他把蛇挂在车边。华佗尚未走远。此人赶上华佗,却见华佗车内挂着此种蛇十多条。又有一个士大夫身体不适,华佗说:“你的病已经很严重,必须破腹除病。但你的寿命也只剩十年。此病不足以让你丧命,你忍病十载,也就免得受破腹之苦。”此人痛痒难耐,必欲除之,华佗于是为其破腹治病。病虽然立即好了,但此人也在十年后死了。广陵太守患病,胸中烦闷,面色赤红、食欲减退。华佗诊脉后说:“你胃中有虫数升,快要形成内疽,是吃多了腥物的原因。”于是煎了二升汤药,先让病人服一升,过一会儿把剩下的服完。不一会,吐出虫儿三升左右。虫儿皆赤头,身子蠕动,半身是生鱼丝。病也立即好了。曹操听说了华佗的神技,便把他召到身边。曹操患有头风病,深以为苦。每次发病,心乱目眩。华佗针扎曹操胸膈,病痛立愈。华佗离家日久,十分想家,便说收到家信,要请假回家一趟。回家后又一再以妻子生病为由续假。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华佗回来,又命地方官赶紧把华佗送回。但华佗自恃身怀绝技,不愿在曹操身边受驱使,迟迟不上道。曹操大怒,派人到华佗家查看。如果其妻果然患病,便赏赐小豆四十斛,延长其假期,但限定回来的日子。如果华佗是说谎,便将其捕押到许昌。华佗被押解到许昌,经审讯拷问,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曹操便把华佗杀了。华佗死了,而曹操头风病仍在。曹操说:“华佗能治愈此病。但这个小人故意不治愈,想以此自重。我就是不杀他,他也不会为我断此病根。”后来,曹操爱子曹冲病重,曹操哀叹说:“我后悔杀了华佗,让这个儿子活活死掉。 ”
陈寅恪指出,华佗为历史上真实人物,这没有疑义。但《三国志》中叙述的那些神技,却让人无法相信。断肠破腹、数日即愈,在当时决无可能,只能是一种神话。梵文中“药”,发音为“阿伽佗”,后来省去“阿”,犹如“阿罗汉”只剩“罗汉”。元化固然本姓华,但本名却并非“佗”。“当时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为‘华佗’,实以‘药神’目之。”

……总而言之,三国志曹冲华佗二传,皆有佛教故事,辗转因袭杂糅附会于其间,然巨象非中原当日之兽,华佗为五天外国之音,其变迁之迹象犹未尽亡,故得以推寻史料之源本。夫三国志之成书,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时,犹不甚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遂致以承祚之精诚,犹不能别择其伪,而并笔之于书。则又治史者所当注意之事,固不独与此二传有关而已。
陈寿撰《三国志》时,佛教传入中国尚不久,而其神话故事却已传播如此之广,在民间社会之影响已经如此之深,以至于以陈寿的严谨、精诚,都不能识别其为来自印度的神话,难怪陈寅恪要大发感慨了。
(三)《崔浩与寇谦之》
本文原刊《岭南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之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
文章首先强调崔浩与寇谦之之关系,是北朝史中一大公案。寇谦之是著名的道教人物。道教虽然一开始是中国本土产物,但后来渐渐接受模仿外来之学术和技艺,变易演进,便成为一庞大复杂之混合体。综观二千年来道教的发展变化,每一次变革,必与一种外来学说的影响有关,而影响道教最深最巨者,当推佛教。佛教影响道教的方式,是医药和天算。借助医药和天算,佛教从精神上征服道教人士,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佛教的学说、思想。陈寅恪进而说:
……自来宗教之传播,多假医药天算之学以为工具,与明末至近世西洋之传教师所为者,正复相类,可为明证。吾国旧时医学,所受佛教之影响极深……
以医药与天算为传播手段,是宗教传播的通例。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亦复如此。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大大借助了医药。佛教的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进入中医系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医的理念与方法。所以,从佛教传入之日起,中医便不能认作纯是中国本土产物。

耆域者,天竺人也。晋惠之末,至于洛阳,时衡阳太守南阳滕永文在洛,寄住满水寺,得病,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因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枝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时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树数十株枯死。域问永文:此树死来几时?永文曰:积年矣。域即向树咒,如咒永文法,树寻荑发,扶疏荣茂。尚方署中有一人病症将死,域以应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咒愿数千言,即有臭气薰彻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举布,应器中有若淤泥者数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阳兵乱,辞还天竺,既还西域,不知所终。
耆域不但能治人之病,还能令死了多年的树起死回生。《高僧传》本是为佛教高僧来游中国者立传,传主当是真实人物。而耆域原本是印度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却与真实人物同列僧传。陈寅恪指出:“事虽可笑,其实此正可暗示六朝佛教徒输入天竺之医方明之一段因缘也。”又说:“至道教徒之采用外国输入之技术及学说,当不自六朝始,观吾国旧时医学之基本经典,如内经者,即托之于黄帝与天师问对之言可知。 ”
四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中,论白居易《法曲》时,指出白居易等人认为是“华声”的音乐,其实不过是先前输入之“胡乐”。例如“霓裳羽衣曲”,“实原本胡乐,又何华声之可言?”进而指出:
夫琵琶之为胡乐而非华声,不待辩证。而法曲有其器,则法曲之与胡声有关可知也。然则元白诸公之所谓华夷之分,实不过今古之别,但认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耳。今世侈谈国医者,其无文化学术史之常识,适与相类,可慨也。20)陈寅恪认为,元白诸人在音乐上强行进行“华夷之分”,是十分可笑的。他们所谓的“华声”,不过是较早输入中国之“夷音”。陈寅恪又把话题转到医学上。今天那些侈谈“国医”、认定所谓“中医”是“国粹”者,其可笑正与元白相同。今天人们熟知、信奉的种种中医理念、方法,或许正是先前输入的外国货。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意在揭示祖父和父亲与清末政坛的关系,尤其是要说明祖父和父亲在戊戌变法中所起的作用。但一开始却写的是自家先前三代与中医的因缘,并且发表了一通对中医的看法。这看似偏离主旨,其实恐怕意在借中医演变,表达对清末思想界中西之争的看法。中医的许多理论方法被视作“国学”“国粹”,但其实不过是较早输入之外来东西。同样,在许多方面,清末守旧者认作是“传统”“国粹”的东西,也不过是早些时候从外国输入的洋货,而被守旧者视作是洪水猛兽、与传统观念冰炭难容的思想,只因是新近输入,便有如此遭遇。
陈寅恪让我们知道,至迟从元稹、白居易的时候开始,所谓中西之争、华夷之别,实不过是古今之争、早迟之别而已。
2018年4月30日
注释:
(1)(2)(3)(4)(5)(7)(9)(10)(11)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版,第163页,第165—166页,第167页,第168页,第169页,第169页,第169页,第169—170页,第169页。
(6)郭嵩焘:《陈府君墓碑铭》,见《郭嵩焘全集》第十五,岳麓书社2012年12月版,第574页。
(8)刘梦溪:《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故宫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1—22页。
(12)陈寅恪:《狐臭与胡臭》,见《寒柳堂集》第140—142页。
(13)(14)(15)(16)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见《寒柳堂集》第157页,第157—158页,第158—159页,第160—161页。
(17)(18)(19)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113页,第114页,第114页。
(20)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144页。
- 钟山的其它文章
- 影印伤
- 罪与罚
——兼及两性问题